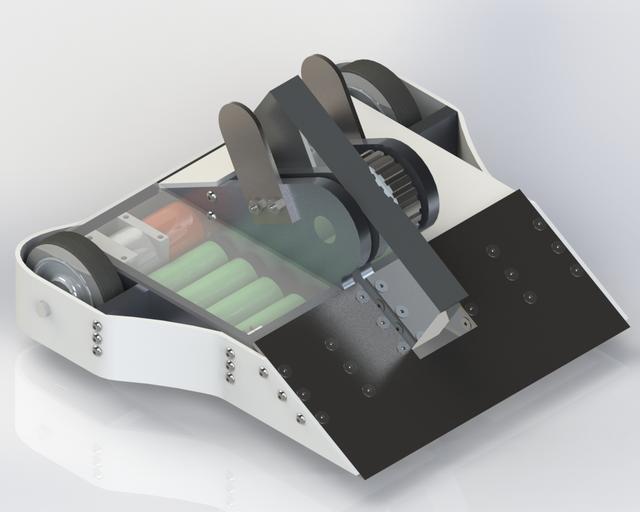不眠的硅谷
◇ 摘自《电脑报》
要 点: 科技的飞速发展、持续创新,超越时空的国际市场竞争,不断促使我们要快马加鞭地前进,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硅谷尚且如此拼搏,我们该怎么办?落后就要挨打,企业要生存,只有靠踏踏实实的埋头苦干、艰苦奋斗,才能迎来希望的明天。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你很难看到有人在外面闲逛;也很难看到有人在午夜之前就上床睡觉。当然,我们不是在谈论夜间活动的“吸血鬼”,而是在说硅谷自己的“夜游神”。这些编程人员、软件开发人员、企业家及项目经理坚守“睡着了,你就会失败”的信条。凭着远大的理想,借助大杯大杯的咖啡,他们会坐在发出融融光线的显示屏前一直工作到凌晨四、五点钟,有时甚至到六点,而不是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这就是参与超越时区的国际市场的代价:每天都有新的起点,不断狂热地开发着“因特网”技术。
睡觉是一种奢侈
安德列·拉莫思常常工作到五点钟,六点开始睡觉。早晨八点左右被来自东海岸或欧洲的电话吵醒。如果晚上休息充足,他会在四点起床;或者当感到身体舒适时,他就在床上辗转反侧,也许一点也不想睡。拉莫思今年二十八岁,家在米尔蒂珀斯,经营一家游戏制作公司。他说他感到身体比以前痛得更厉害。有好几个早上都昏昏欲睡。但是,他依然艰难执行部分是由高科技工业决定的工作日程。这个工业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睡觉也成为一种奢侈。睡觉是无产出的时间耗费,是科技向未来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令人厌烦的驿站。对于越来越多的象拉莫思这样的“凡人”来说,抵抗睡意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尽管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继承了八十年代的工人为免遭解雇而日夜工作的方式。并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人说这是一种病态,但是,正是这样的工作方式建立了今日的硅谷。
“一旦我们为那个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事物进行竞争时,我们都完全失去了控制”。拉莫思说,“我们这一代将体现出为信息时代所需付出的身体和心理的代价。”拉莫思象个极其投入的举重运动员一样,会工作到深夜,直到他需要休息时。
“睡得太久,就会有人抢先得到专利、升职、项目资金或市场份额。”正是这条座右铭驱使着睡眼朦胧的硅谷人彻夜工作。不要在意寒冷、偶尔的胡言乱语和昏昏沉沉地开车回家时的危险,这就是参与超越时空的国际市场所需付出的代价。每天都有发疯似的人耕耘着最新因特网技术,电子函件、ISDN专线和万维网(WWW)已经使家成了工作的延伸地。
由于人们都努力赶超同类产品,使得产品周期变短。“产品开发的速度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太平洋研究中心经理莱尼·西格尔说,该中心是在了望山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十年前,你只要更新产品就可以了。”他还说,“但是现在,在你还没有完成一个产品之前就必须开发新的产品。”
人们减少睡眠,除了竞争激烈的这个原因外,也是受到具有强大压力的计算机精神的影响。这种精神存在于因其经常更新记录和违反常规而引人注目的计算机工业中。在闪闪荧光下,凭着肾上腺激素和咖啡的支持,一个个大项目和大公司不断诞生。
“我从来都不理解为什么需要睡觉。”三十二岁的戴维·费洛说。他是雅虎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与在九五年四月份上市之前一样,他努力工作,克制自己的睡意。现在,从帐面上看,他已是拥有几千万的大富翁了。费洛很少有每晚睡四个小时的时候,有时你可以在桌子底下发现他。他说:“我常常想找一种方法来避免睡觉。我认为人在生理上并不需要睡眠,睡觉只是精神上的事。”
夜间工作也非常适合技术人员的思维方式。不受打扰的一整段空余时间对这种方式是十分重要的,这时可以免受来自白天诸如电话之类的干扰。“在这个行业中,你找不到太多的人,因为人是有政治倾向的动物,他们喜欢闲谈,喜欢开会。”三十岁的迈克尔·拉萨姆说。他是海格软件公司工作小组组长,他在红杉城办公室的灯每天都亮到凌晨二点。拉萨姆很少睡上四个小时,他称之为“永远的生活选择”——或者永远工作到他身体所允许的时候。“当我死后,他们可以给我挂上一块金牌”,他说。
公司大院像大学校园
由于夜间工作的适合性和激烈的竞争性产生了这种独特的硅谷生活方式,在深夜,公司内淡淡地漂散着大学校院气息——穿着体恤的青壮年吃着烤馅饼,光着脚丫在踢足球。但是,这并不能够掩盖他们的斗志,而这正是工作着的人们的特点。很少有人会抱怨说太累了。“我们必须给智力提供赶超极限的机会。”二十七岁的拜伦·雷基策斯说,“这就是我们为实现人类丰功伟绩所付出的代价。”他是网络应用公司(在了望山的一个文件服务公司)的编程员。对于雷基策斯来说,去年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当时他陷入了“一个情感危机”。他认为每天工作到凌晨四点的计划是引起这种“危机”的部分原因。那时,即使睡了足够的时间,雷基策斯还是感到腰酸背疼。当他开车上班时,机器指令总会闯进他的脑海。雷基策斯在三月份回到公司,现在,他称自己为“康复了的夜猫子”,又开始试着在凌晨五点离开办公室。当采访结束时,雷基策斯依然坐在他的终端前,忙于写他的长篇报告。他计划今年下半年开始减少工作时间。
如果有人谈论说他很累,那常常是一种自夸方式进行的。“跟运动员比腿上的伤疤一样,我们比谁睡得最少。”雷基策斯说,正如体育运动一样,高科技领域主要是年轻人的天下,这取决于人衰老过程的极限。据统计,在这个工业中,三十五岁以下的单身男子占绝大多数。他能感受到,有些人在趁他们还未变老之前,在拼命地尽可能从自己身上多榨出些产品(同时从公司领到报酬)。过去的目标常常是在四十岁以前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圣·克拉拉生产集团公司(一个高科技贸易协会)总裁加里·柏克说:“现在好象已经下降到二十岁了。”
这种抱负已经扩展到今日硅谷更广阔的技术敏感性领域。“现在解决硅谷的问题已经不够了。”圣何瑟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切克·达拉说,“现在,我们希望所做的一切成为全世界的楷模。如果你离开这条高速公司哪怕十亿分之一秒钟,你也会失去机会。”
因此,睡眠必然成为一种灾难。“在竞争和科技处于领先地位时,你会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莉莉·普拉特·金说。她是一个职业咨询员,与斯坦福商学院毕业生一起工作。“忘了轻松愉快的加利福尼亚式的生活方式吧,”她说,“硅谷中的人们都已经养成了惜时如金的性格——那就是绝不让时间流走。这种性格变得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成了我在西海岸和中西部看到的最坏的事。”工作到深夜几乎是今日硅谷中大约二十万高科技劳动大军统一的生活方式,那些按照传统日程工作的人们每天有两个交替的时段,而在高科技工业园的停车场里,可能在凌晨三点还依然拥挤不堪。而许多把黑夜当作白天的人们会在夜里把家中的计算机联到办公室的网络上。
凌晨二点发出的电子邮件
布赖恩·厄曼雷德,三十三岁,某网络应用公司系统工程部经理,他经常在晚上八点离开办公室,然后在家中工作到凌晨二点。厄曼雷德努力睡上五个小时,但是如果忽然有了一个新主意,他就会起床并通过电子邮件把这个想法传给同事。“我在凌晨二点发出一个电子邮件。在四点又因想到了另一个主意而醒来,发现二点发出的邮件已经得到了回复”,他说。当软件发布日来临时,塞格软件公司的员工就睡在附近的大号汽车旅馆里,费用由公司支付。Netscape通讯有限公司的员工过去常睡在铺有褥垫的指定的房间中,但是,公司已经撤消了这种房间以鼓励员工停止工作回家去。
习惯一旦养成,很难改掉
“员工们总是要求重新开设铺有褥垫的房间。”塞思黛·霍尔说。霍尔是一个专业的Netscape编程员。她是一个“夜猫子”,带上装有衣服、卫生用具和照明灯的运动包。她把自己称作一个“雅皮士式的乞丐”。
员工们往往被分成小组。一旦发布日或装运期临近时,深夜就成了十分重要的工作时间。在互相合作的环境中,没有消瘦下去是令人担忧的,因为那意味着你没有拼命地工作。“我们在最后期限的压迫下工作。不会有人希望自己到时被迫说‘这是我的错’”霍尔说,当员工拥有公司股票时,这种压力会更大,而员工拥有公司股票是非常普遍的。
曼罗公园未来研究所的保尔·塞福说,计算机生产小组就象军队中的“排”一样。“在战争时期,没有人是为国家而牺牲的。”他说,“他们的死是因为在一大群人面前,每一个人都不是胆小鬼。当你在产品开发小组中,你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赛福把今日的硅谷描绘成为“智力上的武装竞争”。
机器本身也体现出它们的“残暴”,工程师和编程员都描绘了他们如何不能感受到时间的流失;当检查问题时,仿佛只花了几秒钟,但最后却发现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昨天晚上,我在编一段程序,可老是不能完成。”普林斯顿一家软件咨询公司的老板黛博拉·库雷塔说,“不过,我总能从计算机那里得到正确的反馈信息,这是相当令人心醉的,于是我继续工作下去,直到我疲惫不堪。”这时已是凌晨四点,我稍稍打了一会儿盹,早晨七点半起床,打点好两个女儿,送她们去上学。
在家庭和睡眠上作出选择
在从事高科技工作的父母中,库雷塔的工作计划是相当流行的:从睡眠中借点时间来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需要。在他三岁的儿子安德鲁还未出生之前,Adobe系统公司图像与动画工程部经理格雷戈·吉莱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回家。现在,他六点回家,吃完饭,给安德鲁洗浴,送他上床,最后花一点时间陪陪他的妻子凯伦。十点,他回到了望山的公司,并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回家。
深夜,在他的办公室里,吉莱一边吃着糕点一边说“我们不得不在家庭和睡眠之间作出取舍”。
吉莱脸色苍白、头发凌乱,看起来好象在生病。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从不锻炼也不去看医生。凯伦十分为他担心。他计划在这个产品周期结束后好好休息一下,“我常常在这样的强度下连续工作四个月,之后会感到相当的累。”他说,当问他这样干了多久时,他摇摇头说:“八个月了”。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二十七岁的旋风工作室(3DO的子公司,从事游戏制作)经理海尔马特·科勃勒将去渡三年来的第一个假。在一个深夜,他坐在狭小的办公室说:“把十足的夜游神吸引到这个行业里来说明了这个行业确实具有吸引力。但是,几年以后,它就失去了其魅力,现在,我宁愿呆在床上。”科勃勒承认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对自己说:“每天晚上,一喝到坎贝尔汤(一种用来提神的汤液),我就恶心。我必须培养其它兴趣,我赞同变革。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变得平淡无奇,于是我又想去征服世界。”

不眠的硅谷
◇ 摘自《电脑报》
要 点: 科技的飞速发展、持续创新,超越时空的国际市场竞争,不断促使我们要快马加鞭地前进,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硅谷尚且如此拼搏,我们该怎么办?落后就要挨打,企业要生存,只有靠踏踏实实的埋头苦干、艰苦奋斗,才能迎来希望的明天。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你很难看到有人在外面闲逛;也很难看到有人在午夜之前就上床睡觉。当然,我们不是在谈论夜间活动的“吸血鬼”,而是在说硅谷自己的“夜游神”。这些编程人员、软件开发人员、企业家及项目经理坚守“睡着了,你就会失败”的信条。凭着远大的理想,借助大杯大杯的咖啡,他们会坐在发出融融光线的显示屏前一直工作到凌晨四、五点钟,有时甚至到六点,而不是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这就是参与超越时区的国际市场的代价:每天都有新的起点,不断狂热地开发着“因特网”技术。
睡觉是一种奢侈
安德列·拉莫思常常工作到五点钟,六点开始睡觉。早晨八点左右被来自东海岸或欧洲的电话吵醒。如果晚上休息充足,他会在四点起床;或者当感到身体舒适时,他就在床上辗转反侧,也许一点也不想睡。拉莫思今年二十八岁,家在米尔蒂珀斯,经营一家游戏制作公司。他说他感到身体比以前痛得更厉害。有好几个早上都昏昏欲睡。但是,他依然艰难执行部分是由高科技工业决定的工作日程。这个工业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睡觉也成为一种奢侈。睡觉是无产出的时间耗费,是科技向未来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令人厌烦的驿站。对于越来越多的象拉莫思这样的“凡人”来说,抵抗睡意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尽管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继承了八十年代的工人为免遭解雇而日夜工作的方式。并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人说这是一种病态,但是,正是这样的工作方式建立了今日的硅谷。
“一旦我们为那个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事物进行竞争时,我们都完全失去了控制”。拉莫思说,“我们这一代将体现出为信息时代所需付出的身体和心理的代价。”拉莫思象个极其投入的举重运动员一样,会工作到深夜,直到他需要休息时。
“睡得太久,就会有人抢先得到专利、升职、项目资金或市场份额。”正是这条座右铭驱使着睡眼朦胧的硅谷人彻夜工作。不要在意寒冷、偶尔的胡言乱语和昏昏沉沉地开车回家时的危险,这就是参与超越时空的国际市场所需付出的代价。每天都有发疯似的人耕耘着最新因特网技术,电子函件、ISDN专线和万维网(WWW)已经使家成了工作的延伸地。
由于人们都努力赶超同类产品,使得产品周期变短。“产品开发的速度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太平洋研究中心经理莱尼·西格尔说,该中心是在了望山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十年前,你只要更新产品就可以了。”他还说,“但是现在,在你还没有完成一个产品之前就必须开发新的产品。”
人们减少睡眠,除了竞争激烈的这个原因外,也是受到具有强大压力的计算机精神的影响。这种精神存在于因其经常更新记录和违反常规而引人注目的计算机工业中。在闪闪荧光下,凭着肾上腺激素和咖啡的支持,一个个大项目和大公司不断诞生。
“我从来都不理解为什么需要睡觉。”三十二岁的戴维·费洛说。他是雅虎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与在九五年四月份上市之前一样,他努力工作,克制自己的睡意。现在,从帐面上看,他已是拥有几千万的大富翁了。费洛很少有每晚睡四个小时的时候,有时你可以在桌子底下发现他。他说:“我常常想找一种方法来避免睡觉。我认为人在生理上并不需要睡眠,睡觉只是精神上的事。”
夜间工作也非常适合技术人员的思维方式。不受打扰的一整段空余时间对这种方式是十分重要的,这时可以免受来自白天诸如电话之类的干扰。“在这个行业中,你找不到太多的人,因为人是有政治倾向的动物,他们喜欢闲谈,喜欢开会。”三十岁的迈克尔·拉萨姆说。他是海格软件公司工作小组组长,他在红杉城办公室的灯每天都亮到凌晨二点。拉萨姆很少睡上四个小时,他称之为“永远的生活选择”——或者永远工作到他身体所允许的时候。“当我死后,他们可以给我挂上一块金牌”,他说。
公司大院像大学校园
由于夜间工作的适合性和激烈的竞争性产生了这种独特的硅谷生活方式,在深夜,公司内淡淡地漂散着大学校院气息——穿着体恤的青壮年吃着烤馅饼,光着脚丫在踢足球。但是,这并不能够掩盖他们的斗志,而这正是工作着的人们的特点。很少有人会抱怨说太累了。“我们必须给智力提供赶超极限的机会。”二十七岁的拜伦·雷基策斯说,“这就是我们为实现人类丰功伟绩所付出的代价。”他是网络应用公司(在了望山的一个文件服务公司)的编程员。对于雷基策斯来说,去年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当时他陷入了“一个情感危机”。他认为每天工作到凌晨四点的计划是引起这种“危机”的部分原因。那时,即使睡了足够的时间,雷基策斯还是感到腰酸背疼。当他开车上班时,机器指令总会闯进他的脑海。雷基策斯在三月份回到公司,现在,他称自己为“康复了的夜猫子”,又开始试着在凌晨五点离开办公室。当采访结束时,雷基策斯依然坐在他的终端前,忙于写他的长篇报告。他计划今年下半年开始减少工作时间。
如果有人谈论说他很累,那常常是一种自夸方式进行的。“跟运动员比腿上的伤疤一样,我们比谁睡得最少。”雷基策斯说,正如体育运动一样,高科技领域主要是年轻人的天下,这取决于人衰老过程的极限。据统计,在这个工业中,三十五岁以下的单身男子占绝大多数。他能感受到,有些人在趁他们还未变老之前,在拼命地尽可能从自己身上多榨出些产品(同时从公司领到报酬)。过去的目标常常是在四十岁以前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圣·克拉拉生产集团公司(一个高科技贸易协会)总裁加里·柏克说:“现在好象已经下降到二十岁了。”
这种抱负已经扩展到今日硅谷更广阔的技术敏感性领域。“现在解决硅谷的问题已经不够了。”圣何瑟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切克·达拉说,“现在,我们希望所做的一切成为全世界的楷模。如果你离开这条高速公司哪怕十亿分之一秒钟,你也会失去机会。”
因此,睡眠必然成为一种灾难。“在竞争和科技处于领先地位时,你会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莉莉·普拉特·金说。她是一个职业咨询员,与斯坦福商学院毕业生一起工作。“忘了轻松愉快的加利福尼亚式的生活方式吧,”她说,“硅谷中的人们都已经养成了惜时如金的性格——那就是绝不让时间流走。这种性格变得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成了我在西海岸和中西部看到的最坏的事。”工作到深夜几乎是今日硅谷中大约二十万高科技劳动大军统一的生活方式,那些按照传统日程工作的人们每天有两个交替的时段,而在高科技工业园的停车场里,可能在凌晨三点还依然拥挤不堪。而许多把黑夜当作白天的人们会在夜里把家中的计算机联到办公室的网络上。
凌晨二点发出的电子邮件
布赖恩·厄曼雷德,三十三岁,某网络应用公司系统工程部经理,他经常在晚上八点离开办公室,然后在家中工作到凌晨二点。厄曼雷德努力睡上五个小时,但是如果忽然有了一个新主意,他就会起床并通过电子邮件把这个想法传给同事。“我在凌晨二点发出一个电子邮件。在四点又因想到了另一个主意而醒来,发现二点发出的邮件已经得到了回复”,他说。当软件发布日来临时,塞格软件公司的员工就睡在附近的大号汽车旅馆里,费用由公司支付。Netscape通讯有限公司的员工过去常睡在铺有褥垫的指定的房间中,但是,公司已经撤消了这种房间以鼓励员工停止工作回家去。
习惯一旦养成,很难改掉
“员工们总是要求重新开设铺有褥垫的房间。”塞思黛·霍尔说。霍尔是一个专业的Netscape编程员。她是一个“夜猫子”,带上装有衣服、卫生用具和照明灯的运动包。她把自己称作一个“雅皮士式的乞丐”。
员工们往往被分成小组。一旦发布日或装运期临近时,深夜就成了十分重要的工作时间。在互相合作的环境中,没有消瘦下去是令人担忧的,因为那意味着你没有拼命地工作。“我们在最后期限的压迫下工作。不会有人希望自己到时被迫说‘这是我的错’”霍尔说,当员工拥有公司股票时,这种压力会更大,而员工拥有公司股票是非常普遍的。
曼罗公园未来研究所的保尔·塞福说,计算机生产小组就象军队中的“排”一样。“在战争时期,没有人是为国家而牺牲的。”他说,“他们的死是因为在一大群人面前,每一个人都不是胆小鬼。当你在产品开发小组中,你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赛福把今日的硅谷描绘成为“智力上的武装竞争”。
机器本身也体现出它们的“残暴”,工程师和编程员都描绘了他们如何不能感受到时间的流失;当检查问题时,仿佛只花了几秒钟,但最后却发现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昨天晚上,我在编一段程序,可老是不能完成。”普林斯顿一家软件咨询公司的老板黛博拉·库雷塔说,“不过,我总能从计算机那里得到正确的反馈信息,这是相当令人心醉的,于是我继续工作下去,直到我疲惫不堪。”这时已是凌晨四点,我稍稍打了一会儿盹,早晨七点半起床,打点好两个女儿,送她们去上学。
在家庭和睡眠上作出选择
在从事高科技工作的父母中,库雷塔的工作计划是相当流行的:从睡眠中借点时间来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需要。在他三岁的儿子安德鲁还未出生之前,Adobe系统公司图像与动画工程部经理格雷戈·吉莱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回家。现在,他六点回家,吃完饭,给安德鲁洗浴,送他上床,最后花一点时间陪陪他的妻子凯伦。十点,他回到了望山的公司,并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回家。
深夜,在他的办公室里,吉莱一边吃着糕点一边说“我们不得不在家庭和睡眠之间作出取舍”。
吉莱脸色苍白、头发凌乱,看起来好象在生病。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从不锻炼也不去看医生。凯伦十分为他担心。他计划在这个产品周期结束后好好休息一下,“我常常在这样的强度下连续工作四个月,之后会感到相当的累。”他说,当问他这样干了多久时,他摇摇头说:“八个月了”。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二十七岁的旋风工作室(3DO的子公司,从事游戏制作)经理海尔马特·科勃勒将去渡三年来的第一个假。在一个深夜,他坐在狭小的办公室说:“把十足的夜游神吸引到这个行业里来说明了这个行业确实具有吸引力。但是,几年以后,它就失去了其魅力,现在,我宁愿呆在床上。”科勃勒承认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对自己说:“每天晚上,一喝到坎贝尔汤(一种用来提神的汤液),我就恶心。我必须培养其它兴趣,我赞同变革。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变得平淡无奇,于是我又想去征服世界。”

不眠的硅谷,总算明白了国内996的起源啦
◇ 摘自《电脑报》
要 点: 科技的飞速发展、持续创新,超越时空的国际市场竞争,不断促使我们要快马加鞭地前进,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硅谷尚且如此拼搏,我们该怎么办?落后就要挨打,企业要生存,只有靠踏踏实实的埋头苦干、艰苦奋斗,才能迎来希望的明天。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你很难看到有人在外面闲逛;也很难看到有人在午夜之前就上床睡觉。当然,我们不是在谈论夜间活动的“吸血鬼”,而是在说硅谷自己的“夜游神”。这些编程人员、软件开发人员、企业家及项目经理坚守“睡着了,你就会失败”的信条。凭着远大的理想,借助大杯大杯的咖啡,他们会坐在发出融融光线的显示屏前一直工作到凌晨四、五点钟,有时甚至到六点,而不是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这就是参与超越时区的国际市场的代价:每天都有新的起点,不断狂热地开发着“因特网”技术。
睡觉是一种奢侈
安德列·拉莫思常常工作到五点钟,六点开始睡觉。早晨八点左右被来自东海岸或欧洲的电话吵醒。如果晚上休息充足,他会在四点起床;或者当感到身体舒适时,他就在床上辗转反侧,也许一点也不想睡。拉莫思今年二十八岁,家在米尔蒂珀斯,经营一家游戏制作公司。他说他感到身体比以前痛得更厉害。有好几个早上都昏昏欲睡。但是,他依然艰难执行部分是由高科技工业决定的工作日程。这个工业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睡觉也成为一种奢侈。睡觉是无产出的时间耗费,是科技向未来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令人厌烦的驿站。对于越来越多的象拉莫思这样的“凡人”来说,抵抗睡意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方式,尽管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继承了八十年代的工人为免遭解雇而日夜工作的方式。并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人说这是一种病态,但是,正是这样的工作方式建立了今日的硅谷。
“一旦我们为那个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事物进行竞争时,我们都完全失去了控制”。拉莫思说,“我们这一代将体现出为信息时代所需付出的身体和心理的代价。”拉莫思象个极其投入的举重运动员一样,会工作到深夜,直到他需要休息时。
“睡得太久,就会有人抢先得到专利、升职、项目资金或市场份额。”正是这条座右铭驱使着睡眼朦胧的硅谷人彻夜工作。不要在意寒冷、偶尔的胡言乱语和昏昏沉沉地开车回家时的危险,这就是参与超越时空的国际市场所需付出的代价。每天都有发疯似的人耕耘着最新因特网技术,电子函件、ISDN专线和万维网(WWW)已经使家成了工作的延伸地。
由于人们都努力赶超同类产品,使得产品周期变短。“产品开发的速度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太平洋研究中心经理莱尼·西格尔说,该中心是在了望山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十年前,你只要更新产品就可以了。”他还说,“但是现在,在你还没有完成一个产品之前就必须开发新的产品。”
人们减少睡眠,除了竞争激烈的这个原因外,也是受到具有强大压力的计算机精神的影响。这种精神存在于因其经常更新记录和违反常规而引人注目的计算机工业中。在闪闪荧光下,凭着肾上腺激素和咖啡的支持,一个个大项目和大公司不断诞生。
“我从来都不理解为什么需要睡觉。”三十二岁的戴维·费洛说。他是雅虎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与在九五年四月份上市之前一样,他努力工作,克制自己的睡意。现在,从帐面上看,他已是拥有几千万的大富翁了。费洛很少有每晚睡四个小时的时候,有时你可以在桌子底下发现他。他说:“我常常想找一种方法来避免睡觉。我认为人在生理上并不需要睡眠,睡觉只是精神上的事。”
夜间工作也非常适合技术人员的思维方式。不受打扰的一整段空余时间对这种方式是十分重要的,这时可以免受来自白天诸如电话之类的干扰。“在这个行业中,你找不到太多的人,因为人是有政治倾向的动物,他们喜欢闲谈,喜欢开会。”三十岁的迈克尔·拉萨姆说。他是海格软件公司工作小组组长,他在红杉城办公室的灯每天都亮到凌晨二点。拉萨姆很少睡上四个小时,他称之为“永远的生活选择”——或者永远工作到他身体所允许的时候。“当我死后,他们可以给我挂上一块金牌”,他说。
公司大院像大学校园
由于夜间工作的适合性和激烈的竞争性产生了这种独特的硅谷生活方式,在深夜,公司内淡淡地漂散着大学校院气息——穿着体恤的青壮年吃着烤馅饼,光着脚丫在踢足球。但是,这并不能够掩盖他们的斗志,而这正是工作着的人们的特点。很少有人会抱怨说太累了。“我们必须给智力提供赶超极限的机会。”二十七岁的拜伦·雷基策斯说,“这就是我们为实现人类丰功伟绩所付出的代价。”他是网络应用公司(在了望山的一个文件服务公司)的编程员。对于雷基策斯来说,去年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当时他陷入了“一个情感危机”。他认为每天工作到凌晨四点的计划是引起这种“危机”的部分原因。那时,即使睡了足够的时间,雷基策斯还是感到腰酸背疼。当他开车上班时,机器指令总会闯进他的脑海。雷基策斯在三月份回到公司,现在,他称自己为“康复了的夜猫子”,又开始试着在凌晨五点离开办公室。当采访结束时,雷基策斯依然坐在他的终端前,忙于写他的长篇报告。他计划今年下半年开始减少工作时间。
如果有人谈论说他很累,那常常是一种自夸方式进行的。“跟运动员比腿上的伤疤一样,我们比谁睡得最少。”雷基策斯说,正如体育运动一样,高科技领域主要是年轻人的天下,这取决于人衰老过程的极限。据统计,在这个工业中,三十五岁以下的单身男子占绝大多数。他能感受到,有些人在趁他们还未变老之前,在拼命地尽可能从自己身上多榨出些产品(同时从公司领到报酬)。过去的目标常常是在四十岁以前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圣·克拉拉生产集团公司(一个高科技贸易协会)总裁加里·柏克说:“现在好象已经下降到二十岁了。”
这种抱负已经扩展到今日硅谷更广阔的技术敏感性领域。“现在解决硅谷的问题已经不够了。”圣何瑟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切克·达拉说,“现在,我们希望所做的一切成为全世界的楷模。如果你离开这条高速公司哪怕十亿分之一秒钟,你也会失去机会。”
因此,睡眠必然成为一种灾难。“在竞争和科技处于领先地位时,你会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莉莉·普拉特·金说。她是一个职业咨询员,与斯坦福商学院毕业生一起工作。“忘了轻松愉快的加利福尼亚式的生活方式吧,”她说,“硅谷中的人们都已经养成了惜时如金的性格——那就是绝不让时间流走。这种性格变得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成了我在西海岸和中西部看到的最坏的事。”工作到深夜几乎是今日硅谷中大约二十万高科技劳动大军统一的生活方式,那些按照传统日程工作的人们每天有两个交替的时段,而在高科技工业园的停车场里,可能在凌晨三点还依然拥挤不堪。而许多把黑夜当作白天的人们会在夜里把家中的计算机联到办公室的网络上。
凌晨二点发出的电子邮件
布赖恩·厄曼雷德,三十三岁,某网络应用公司系统工程部经理,他经常在晚上八点离开办公室,然后在家中工作到凌晨二点。厄曼雷德努力睡上五个小时,但是如果忽然有了一个新主意,他就会起床并通过电子邮件把这个想法传给同事。“我在凌晨二点发出一个电子邮件。在四点又因想到了另一个主意而醒来,发现二点发出的邮件已经得到了回复”,他说。当软件发布日来临时,塞格软件公司的员工就睡在附近的大号汽车旅馆里,费用由公司支付。Netscape通讯有限公司的员工过去常睡在铺有褥垫的指定的房间中,但是,公司已经撤消了这种房间以鼓励员工停止工作回家去。
习惯一旦养成,很难改掉
“员工们总是要求重新开设铺有褥垫的房间。”塞思黛·霍尔说。霍尔是一个专业的Netscape编程员。她是一个“夜猫子”,带上装有衣服、卫生用具和照明灯的运动包。她把自己称作一个“雅皮士式的乞丐”。
员工们往往被分成小组。一旦发布日或装运期临近时,深夜就成了十分重要的工作时间。在互相合作的环境中,没有消瘦下去是令人担忧的,因为那意味着你没有拼命地工作。“我们在最后期限的压迫下工作。不会有人希望自己到时被迫说‘这是我的错’”霍尔说,当员工拥有公司股票时,这种压力会更大,而员工拥有公司股票是非常普遍的。
曼罗公园未来研究所的保尔·塞福说,计算机生产小组就象军队中的“排”一样。“在战争时期,没有人是为国家而牺牲的。”他说,“他们的死是因为在一大群人面前,每一个人都不是胆小鬼。当你在产品开发小组中,你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赛福把今日的硅谷描绘成为“智力上的武装竞争”。
机器本身也体现出它们的“残暴”,工程师和编程员都描绘了他们如何不能感受到时间的流失;当检查问题时,仿佛只花了几秒钟,但最后却发现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昨天晚上,我在编一段程序,可老是不能完成。”普林斯顿一家软件咨询公司的老板黛博拉·库雷塔说,“不过,我总能从计算机那里得到正确的反馈信息,这是相当令人心醉的,于是我继续工作下去,直到我疲惫不堪。”这时已是凌晨四点,我稍稍打了一会儿盹,早晨七点半起床,打点好两个女儿,送她们去上学。
在家庭和睡眠上作出选择
在从事高科技工作的父母中,库雷塔的工作计划是相当流行的:从睡眠中借点时间来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需要。在他三岁的儿子安德鲁还未出生之前,Adobe系统公司图像与动画工程部经理格雷戈·吉莱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回家。现在,他六点回家,吃完饭,给安德鲁洗浴,送他上床,最后花一点时间陪陪他的妻子凯伦。十点,他回到了望山的公司,并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回家。
深夜,在他的办公室里,吉莱一边吃着糕点一边说“我们不得不在家庭和睡眠之间作出取舍”。
吉莱脸色苍白、头发凌乱,看起来好象在生病。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从不锻炼也不去看医生。凯伦十分为他担心。他计划在这个产品周期结束后好好休息一下,“我常常在这样的强度下连续工作四个月,之后会感到相当的累。”他说,当问他这样干了多久时,他摇摇头说:“八个月了”。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二十七岁的旋风工作室(3DO的子公司,从事游戏制作)经理海尔马特·科勃勒将去渡三年来的第一个假。在一个深夜,他坐在狭小的办公室说:“把十足的夜游神吸引到这个行业里来说明了这个行业确实具有吸引力。但是,几年以后,它就失去了其魅力,现在,我宁愿呆在床上。”科勃勒承认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我对自己说:“每天晚上,一喝到坎贝尔汤(一种用来提神的汤液),我就恶心。我必须培养其它兴趣,我赞同变革。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变得平淡无奇,于是我又想去征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