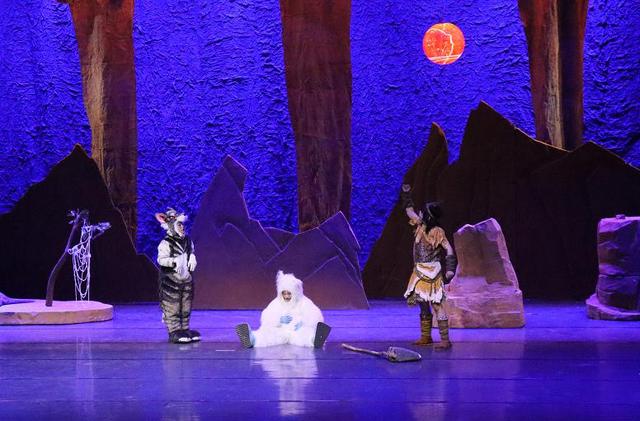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俺们高架子大队,除了唱戏、放电影,就属炸爆米花那儿有吸引力。

由于俺们山村男女劳力是在队长的吆喝下集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炸爆米花的人总选择在晚上开始。炉火在风箱吹动下,温馨地一闪一闪地撕扯夜幕。
大人扎堆聊天并不时照看着自己的玉米,当前面的倒入锅内,马上就会把自己的往前挪动一个位置。我们这些顽童就着炉火玩老鹰捉小鸡。
那时,不知是为了给家里节省煤油还是老师很少布置家庭作业,我印象中晚上总有成群的孩子疯玩。可不管玩的多入迷,当“嘣”声响动,就会拼命向爆米花机这儿挤,以便能多拣到几颗从锅口蹦出来的爆米花。
当风箱前后抽送时炉火亮堂,可以在布满尘土的地上马上分辨出雪白的爆米花;风箱停顿时,就在地上凭运气乱摸一气。
也不是说想吃爆米花,只能靠拾,有时也会有大人端着刚炸好的爆米花,碰巧这个人是你家处得很好的邻居或是近亲,他就会抓一把,不过这是有来往的。如自家炸了一锅,本人就会像过年一样高兴,每天上学前就会从密封的塑料袋里抓一小把以便路上像吃水果糖似的边走边吃,这样会觉得二里路真近,像是学校就在自家院墙的拐角处。
俺父亲时常炸一锅,并且是大米花。这是因父母都是教师,有工资收入,肯定要比那些靠工分生活的村民优渥的多,再有我们家五口都是非农业户口,有白面和大米的供给,可我们弟兄三人也不能随意或放量吃。
提到“非农业”,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在周营街剃头,剃头的师傅在随意的询问下,知道了我是“非农业”,立即转脸兴奋地告诉旁边的一个中年妇女,这个快嘴的女人马上向剃头铺门口的几个熟人喊:快来看,这儿有一个“非农业”小孩……
有一年的冬季,我边走边向嘴巴里一颗颗送大米花,看到正倚在向阳墙脚取暖的老老爷(比我大三辈),我赶紧礼貌地打招呼。他戏谑说:亚民,你吃的是大米花吧,能让我尝尝?我赶紧捂口袋。
他一看说:你这孩子,我60多岁的人能抢你的东西吃,我小时就经常吃,并且是用芝麻杆烧火炸成的江米花。那时,你老太太(他母亲)每天早上给我冲两个鸡蛋,再从写着“营养米”的牛皮纸袋子里捧两捧江米花,还滴上两滴香油……
他的话我在父亲那儿得到证实——他家原来四面有高墙四角设炮楼大门上的铜钉有碗口大,是名符其实的“地主”,只是在他不到十岁时,他的父亲就把地败光了——
关于爆米花的琐碎记忆还有很多,我很庆幸随时间的推移,周围环境、人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水平日新月异了许多,也庆幸手摇式爆米花机依然如故,给我延续着记忆,让我的记忆能够膨胀炸开并轻盈地飘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