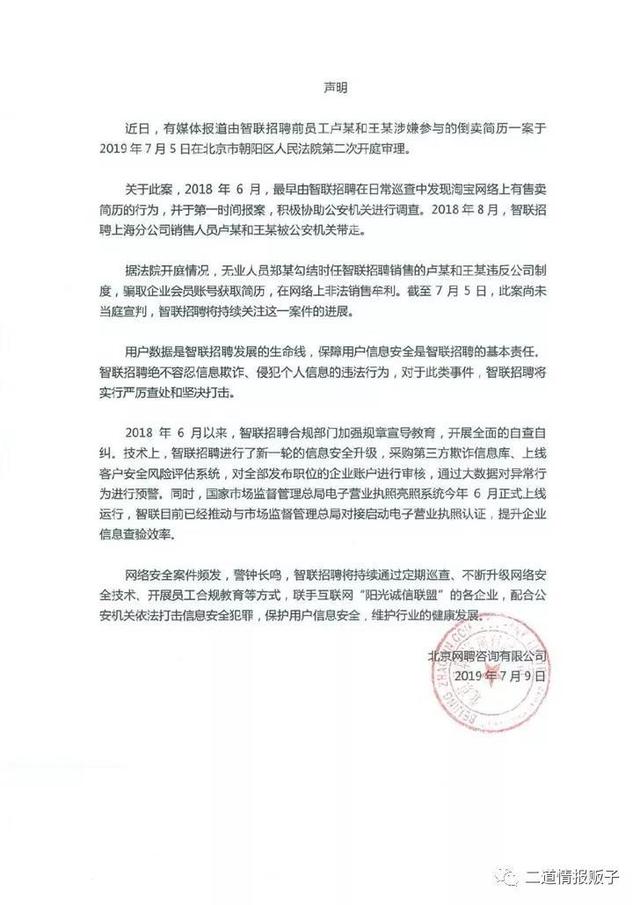读过许多诗之后,虽然我仍然没有学会写诗,但对诗这个物事却也有了一些感悟和看法。下面试着说说,算是姑妄言之。文中的排序只是我作文时随机的思绪,与内容的重要性无关。
一、诗有何用?“ 世间何事好?最好莫过诗。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始拟归山去,林泉道在兹。”这是一位姓杜的老先生写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这位老先生对诗的执著的爱,在生天天都作诗,一天不拉下,要他不作诗,除非他死了。这种精神着实令人钦佩。那么诗有何用?如此令人着迷?关于诗的功用,说法甚多:能咏物,能言志,能抒情,作武器,作号角,作鼓舞,等等等等。都对,但我认为还有一样没有说,能养气。养什么气?文人之气,雅士之气。只要你喜欢上了诗,无论是喜欢读还是喜欢写,你便不可避免地沾上了文人雅士之气,久而久之,你的言行举止以及形象思维便会受到改变,逐渐向文人雅士靠拢,这种改变是渐进的、无声的、不知不觉的,也许你终其一生也成不了文人雅士,但却一生都在向其靠拢,正所谓潜移默化就是这样。心浮气躁的粗俗之徒和打街骂巷的市井流氓绝对是与诗无缘的,即便偶然扯上关系,也决不会有好的造诣,我不说成就与建树,因为这样的人根本不配与这两个词并列,人品差太多了,诗品自然就谈不上。
三、 诗当晓畅。说到诗,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是晦涩与晓畅的问题。有一种误识,认为写旧体就一定要尽量写得古奥难懂,这才显得有水平,象古诗,其实错了,许多经典古诗几乎就是白话,“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臥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太多太多,不胜枚举,这些诗多么的明白晓畅。反之,如果写得拐弯抹角诘屈聱牙,人们就不大喜欢读,更不容易被记住。试看一下下面这两首同样为《村居》的诗:
“鸡号四邻起,结束赴中原。戒妇预为黍,呼儿随掩门。犁锄带晨景,道路笑更喧。宿潦濯芒屦,野芳簪髻根。霁色披窅霭,春空正鲜繁。辛夷茂横阜,锦雉娇空园。少壮已云趋,伶俜尚鸱蹲。蟹黄经雨润,野马从风奔。村落次第集,隔塍致寒喧。眷言月占好,努力竟晨昏。”诗中描写的农村中活动场景生动具体,非常之好,但读来总有晦涩之感。另一首《村居》就明白晓畅得多: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臥剥莲蓬。”
前一首的作者是秦少游,后一首的作者是辛弃疾,俩人都是著名的大词家,两首词都把乡居生活描写得栩栩如生。然而人们更为喜爱更愿背诵也更能记得的是哪首呢?无疑是辛弃疾的这首。把这两首同题材的作品放在一起来比较,就更能看出“文”与“白”的不同效果了。我说在旧体诗词创作中顺其自然,“白”点亦无妨。但这“白”与“俗”是有区别的。不必刻意求“文”、求“古”,但也不应刻意求“白”、求“俗”,进而发展到多用俚语村言或流行新词的口语化的地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否则又是一个误区。“白”也应有诗味,否则便是白话的排列;“白”也应是用的规范化的语言,否则“白”虽“白”矣,恐很快便会沦为比“文”更难懂的文字。例如我们写“坑爹吐槽草泥马,驴友逗逼键盘侠”,或“小三插足没神马,宅女Q群有帅锅”,当今的人肯定觉得再明白不过了,然而时移事易、百载千年之后呢?其绝对会成为最难懂的文字,那时就需要由学者去考证和注释了。为什么?就因为它不是规范化的语言。规范的语言很稳定,而俚语髦词的一大特点就是流行得快,消亡得也快。
让我们来读读这首《品令》:“幸自得,一分索强,教人难吃。好好地恶了十来日。忔而今教些不?须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须肐织!衡倚赖脸儿得人惜,放软顽道不得。”什么意思?如坠五里雾吧?这词就是口语化的。是用宋朝某个时段的杨州方言写的,在当时当地是最“白”不过了,然而我们现在去读,除了进行研究的学者外,估计多数人是读不懂的了。上述问题我曾在《浅谈旧体诗词创作中的“文”与“白”》一文中简要说过(见《贵阳诗词》2016年第一期)虽然意犹未尽,曾有意深入展开再谈,但不拟在这篇文章中重说了 。

四、义重于形。这个题义不是只要内容不要形式,如果这样认识,就是曲解了我的意思。所谓义重于形,前提是诗,是在遵循诗的规则的大框架下。否则写一句口号岂不更直接了当?形式与内容到底孰重孰轻孰主孰次?问题这样提出,多数人会说:当然是内容为主嘛,还用问吗?然而当这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处理它时却又是另一态度,换成了形式为重了,经常会为了形式而改变内容,编辑为了刊物的声誉,要改;作者为了不被讥嘲和得以认可,要改。两者都很无奈,都知道内容应重于形式,但也都要改,即使有时违心也不能免。当然,认为形式重于内容者也有,极少罢了。这一改,往往便有些好句好词好字甚至好意思好意境被改掉了,相信许多诗友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诗词,形式上无懈可击,诗句却乏善可陈,象这样只有诗的躯壳而缺少诗的灵魂的所谓诗,没有也罢。
格律这东西是古人为了声律更谐音韵更美而创造出来的,但他们对格律的遵从却比我们要灵活得多,平仄上有拗救,韵脚上有通押,有的甚至只求诗意通达而罔顾平仄,最典型的莫过于崔颢的《黄鹤楼》诗,“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一句比“孤平”还孤平,后一句则是三平尾,这些都犯了大忌,是不允许的,还有“黄鹤”、“黄鹤”反复出现,按现在观点也是犯了大忌。崔颢是盛唐时人,那时格律早成。然而大诗人李白看了这诗后,并没有指斥其“绿”了,更没有义愤填膺地讥其不懂格律不守规矩,反而由衷地钦佩对方说你这诗写得太好了,有你这样好的诗在此,我也不必再写了。沈约所标诗之“八病”,曰: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韻、小韻、正纽、旁纽,我看了之后,感觉若全依他的,虽然于声律美上确有彰益,但写诗这档子事恐将更其小众化,非博学鸿儒不能为。
仅以“蜂腰”、“鹤膝”来说,何谓“蜂腰”?首尾浊音夹中间一清音是也,如“邂逅承际会”。反之即为“鹤膝”,如“微音冠青云”。到后来连“滾滾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作者杨慎也看不下去了,鄙夷地说“休文(沈约字)八病,甚为拘滞,正与古体相反......未免商君之酷,不足道也”。沤心沥血焚膏继晷地研究出来的成果(或者说钻出来的牛角尖),却被别人一句“不足道也”弃若弊履,何苦来着。为了音韵之美达于极致,唐律还曾对颔、颈两联要求双声叠韻,“律诗中联,双声叠韻。即律诗起结及绝句用对体者,便须用此法。但起结及绝句,可对可不对。”(范况《中国诗学通论》)何谓双声叠韻?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韻,谓之叠韻。杜诗:“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燕语太丁宁”,“造次”为双声,“丁宁”即叠韻。李白诗:“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翡翠”叠韻,“鸳鸯”双声。这些精益求精之法,因太过琐细,缚人手脚,故自宋以后遂渐被弃用,“旧法殆尽,几成绝学”。(范况语)词律则更严,不仅要求平仄,还要求上去入的区分,“盖诗文分平侧,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李清照《词论》)。现在则除了少数特别要求的词如《满江红》要押入声外,大多都只要该用仄声的地方用仄声就行,而不需分上去入了。
以上种种,说明了从古至今,在雕章琢句韵律修饰上走的一直是一条由繁到简、由严及宽的路。虽然这些都是由古人创造并推向极致的,但也是由他们开启回归之路的。以后还将简化下去,这是一种趋势,无人能挡。不解的是至今仍有人认识不到这点,死抠格律,一丝不苟。若在正式出版物上也还罢了,甚至在平时聊天的急就章中也不容瑕疵,誓死捍卫传统美学,时常弄得人人噤声,大煞风景,这就有点过了。子路在战场上刀光剑影之中,忽然帽子掉了,他坚守“君子死,冠不免”的礼制,宁愿不要命也要把帽子捡起戴上,于是被人砍掉了头颅剁成了肉酱。宋伯姬面对房屋失火,因不符礼制决不离开,于是被大火烧死。这都是太过拘泥不知变通迂腐至极的典型事例。
不过我可不敢笑他们,因我有时在对旧体诗词规制上的拘泥与上述两位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虽事体有异,而本质亦同。少年时曾听一位老先生说过六韵通转,后来在《中国诗学通论》等书中也读到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也有权威说不能通转。老早以前曾有过借韵,但也有一些限制,如只在首句,只限邻韵等。而在实际运用中也似乎不能,如大家常用的诗词检测软件,你把有拗救、通押的诗放上去试试,拗救一定标为出律,通押一定标为不押韵。且用红字标出。看到这些红字,会感觉有一种威压,于是不想改也得改。软件确实也好用,提供了一个较方便的工具,但需要把拗救和通押的内容补上去,如此,则更为完善。近人范况在《论指摘》中有一段话,虽为失粘而言,但亦可推而广之:“盛唐诸家,出奇变化,往往不缚于律,故其时之诗,多失粘者。虽失粘而不害为好诗。后人竭力避之则拘;有心效之亦过矣。”末两句确为中肯之论,竭力规避则拘谨呆滞,着力效仿则不足为法。要之,形式服务于内容,附丽于内容,从属于内容。“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王安石《上人书》)这些见解都很正确,惜乎我们常未能理解。买双新鞋,不合脚了,怎么办?拿出刀来,将顶鞋之处的皮肉切去以符鞋码,行吗?任意询人,其必曰:傻瓜才会这样做?不幸的是有许多聪明人却常在做着这样的事而不自知,或自知而仍要削。不仅削自己的脚,有的还喜欢削别人的脚,真是无法可想。我这人胆小,而且手艺差,所以从不敢去削别人的脚,但却经常削自己的。最近一例,前两天在家午睡,适大雷雨,煮饭半途停电,致饭夹生。戏得长短数句:“骤雨庭前消暑,鼾声室内惊魂。抛却身前身后名,且喜六根清静。 傍晚忽然停电,锅中米饭犹生。聊将老酒邀寒星,举杯无月对影。”前阙借辛词“赢得身前身后名”句,反其意而用之。后阙用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典。全词清新自然,暗含两典,略怀文蕴,首联对仗亦工。正小有自得。然而比对规则,却于制不符。奈何只得削足,改成这样:“骤雨庭前消暑,鼾声室内雷鸣。远抛身后眼前名,且喜六根清静。 傍晚忽然停电,黄梁釜里犹生。聊将老酒对疏星,却恨冰轮无影。”虽符了格律,却觉不如初稿,凿痕明显,且违了原意。
诗词刊物,讲究规制,坚守阵地,这是必须的。但倡导新风是不是也为应有之义呢?我想建议能否每期拿出两页,辟一个园地,取一个恰当的专栏名称,专登虽有出律,但词义均佳的诗词,开一个先河呢?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望岳》、王维的《鹿柴》、孟浩然的《春晓》、柳宗元的《江雪》不是都很好吗?

五、关于重词重字。诗词中出现重词重字,要不要改?愚意以为不能一概而论,须看诗作而言。无重未必就好,有重未必就孬。有时重字重词还会收到意料之外的好效果。如前面所举《黄鹤楼》诗就是一例。翻开古诗,类作甚多,如“江水漾西风,江花脱晚红”(王安石《江山》)、“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王安石《北陂杏花》)等。李白还特意模仿崔颢的黄鹤楼诗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红楼梦》中有首《秋窗风雨夕》更是把这种笔法发挥到了极致:“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哪堪风雨助凄凉。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续,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挑泪烛......”。重词重字在楹联中被广泛使用,对这点人们倒是没有异议,所以籍重词重字而得新意妙意之联句不少,如“以教人者教己;于劳力处劳心”、“新知长相知知心知意知冷暖;老伴永作伴伴读伴游伴春秋。”、“不大地方可国可家可天下;平常人物为将为相为名臣”等等不胜枚举。还有一联更妙,须仔细参详才能读懂它:“好读书不好读书;好读书不好读书。” 从这些例子看,重词重字只要用得好,不仅可以,而且能收奇效。
六、关于古风。什么是古风?有人以为凡是没有按格律写的文言或半文言诗,就可以叫作古风,于是把自己不合律的诗都心安理得地标作古风,这种取巧其实是不对的。能称作古风的诗,也有软硬两方面的要求。软的方面,要求格调高古。何为高古?这很难用文字给予准确而明晰的界定,只能在阅读时去心领神会。硬的方面,诗句多为拗句,一大特点是二、四字同声,比如“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间、壶”、“杯、明”就是这样的句子。对三字脚也有要求,只有仄平仄、平仄平、仄仄仄、平平平四种格式,“无相亲”、“邀明月”、“成三人”可不是随便写的,而是作者有意为之。而入律的古风则不仅要求用律句,还要求有粘对,要换韵,且是平韵仄韵交替着换。知道了这些,也就明白不是随便什么诗都可以称作古风的了。
七、诗当出新。别人见月仄而伤心,我便观花谢而落泪,别人长呼大江东去,我便慨叹逝者如斯,别人夸梅花清高,我也赞梅枝傲骨,人云亦云,了无新意。无新意,便不可取,这样的诗,不写也罢。出新,说着容易,行则甚难。一轮月,一湾水,一座山,一树梅,古人写到今人,写了几千年,什么不被写尽了,要想出新,谈何容易!虽如此,也并非不可为。就算不能为,也须作为努力的方向。如何出新?我以为首在立意,立意新了,新句才能出来,若无新意,则索尽枯肠也难有新句。“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张籍《秋思》)旅人在外日久,季节变换,秋凉了,想家人了,写封家书回去探问一下,本极平凡的事,开篇也是平铺直叙。但到末了话锋一转:送信的人都要走了,等等,回来,恐怕我有些话还没有说周到,让我再打开信来看看!牵肠挂肚的情绪跃然纸上,新意出来了。“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李峤《中秋夜》)同是吟月却不落圆缺感伤的窠臼。
八、关于韵脚。在诗词韵文中,于特定的句子之末用发音相近的字,以使诗文读起来谐律上口,于是产生了韵脚。我国从来地广人多,口音大异而又文化相同,总不能在相同的文化下却各说各话,各押各韵,于是有了统一的需要。已知的最早韵书为一千五百多年前隋人陆法言编的《切韵》(据说此前尚有三国时人李登编的《声类》,但该书按宫、商、角、徵、羽五声而不是按韵部编排,且早已失传,故对后世韵书影响不大),收字一万一千五百,分一百九十三部,为学界及官方公认。唐初以《切韵》为蓝本编了《唐韵》,至北宋增订为《大宋重修广韵》,南宋重编为《平水新刊韵略》,再至清初的《佩文韵府》,再至民国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国语新诗韵》,再到前些年的《中华新韵》及去年的《中华今韵》。为什么一本韵书要反反复复改来改去,原因很简单,因为语言总是在变,“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陈第《毛诗古音考》),为了适应,必须得与时俱进。那么经过了这么多之后,是否就已经完善了呢?我认为还没有。不信且看,无论是《佩文诗韵》还是较宽的《词林正韵》甚至更宽的《中华新韵》,在同一个韵部里都能捡出许多我们读着并不押韵的字来。比如:支、吹、皮;元、村、反。
不知别人如何,我是读不出它们的韵来,然而前三字同在四支,后三字同在十三元。如果用支、吹、皮或元、村、反做一首诗的韵脚,读来一定相当别扭。而与此相反的情况竟也有,如袁、闲、黔、严,我们读来很押韵吧,按普通话其韵母也完全相同,但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首诗里做韵脚却又大错特错了,因为它们竟然分属不同的四个韵部:十三元、十五删、十四盐、十五咸。翻开韵书,此类情况腑拾即是,我想说《佩文韵府》可以休矣,但只敢小声地说,怕被胶柱鼓瑟的先生们听见,那样我可死定了,非被千夫所指不可。须知“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后果是很严重的。平水韵如此,那么《中华新韵》又如何呢?比较起来,后者要好很多,但也还是有同样的问题,比如曾、冰、封,同在十一庚,梭、格、浊同在二波。这是差异较大的;还有一些同一韵部的字虽差异较小,但读来也觉不太押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 是《中华新韵》也许还受到古谱一定的影响。二是说明我们今天的读音与古时区别是很大的,还有地域的不同,发音的差异,我的父母是湖南人,他们的口语里就有楚音,有许多字在他们的嘴里说出来就是合韵的。还有一次在电视上看中华诗词大赛,有位福建选手说他感觉用闽南话读古诗有时音律更谐,于是朗诵了一首,诗名我忘了,闽南话我也听不懂,但听他朗诵起来确实感到非常的协韵,很舒服。国家推广普通话几十年了,成就甚大,现在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能说普通话,虽然标准程度尚有参差,但最差的也能互相交流。至于听懂,就更没问题了。更重要的是越是年青人、孩子们,普通话越说得好。我想,应该彻底摒弃以前的韵谱,完全依据普通话编定新的韵谱了。最近读到一篇发表在中华诗词论坛上的文章,题目叫《声韵的起源、改革与发展》,文中批评用现代语言去套宋朝的语音,诗写出来却不能用平水韵去读,就好似哑巴英语,是“秦时服饰现时穿”岂非不合时宜么?
结束语:题外的话。中国人既聪明又勤劳,本可以在人类文明与科技进步上有更大的贡献,惜乎咱们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把几乎所有的聪明才智和精力时间都用在了咬文嚼字上,实用科技则留给了工匠,而工匠们又没有文化,不能在理论上升华,从而再用升华了的理论来提高技艺,致使这方面一直停滞在工匠的水平。当大家都在这水平上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甚至还为工匠们木雕石刻的精良技艺津津乐道沾沾自喜。而西方的知识分子们在殚精竭虑地研究自然科学并取得巨大成就后,我们的落后便显出来了,于是鸦片战争、甲午风云、七七事变、八国联军等等百年耻辱便降临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头上。瓦特对着开水壶格物,格出了蒸汽机,引发了欧洲的工业革命;牛顿对着苹果树格物,格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籍此科技获得了许多重大成就;王阳明对着竹子格物,格出了唯心主义的心学,虽然也算在哲学上有所建树,但于国计民生却没有什么作用。若说文房四宝能挡得住真枪实弹,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现代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大多数都去钻研实用科技甚至基础研究去了,虽然感觉于旧体诗词一道有点后继乏人,但对国家民族的兴盛却是最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