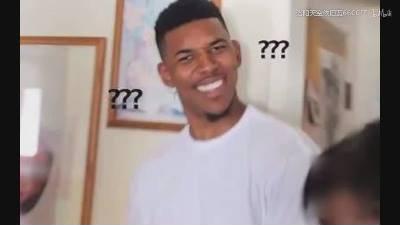大花草(图片来源: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花,或许也是最臭的花;它让无数人为之惊叹,也让科学家琢磨不透。在过去的200年里,大花草始终是世人的焦点;而未来,它却可能在我们的注视中走向灭绝。
1818年,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阿诺德(Joseph Arnold)在跟随新上任的斯坦福德·拉弗尔斯(Stamford Raffles)中尉远征时,在苏门答腊岛的英属明古莲地区(今明古鲁省)发现了一朵奇异的巨型花朵。“说实话,如果周围没有旁观者,我可能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这朵花的大小远远超过任何我此前见过或者听说过的花朵……”阿诺德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它足足有1码(约92厘米)宽;它的红色花瓣从根部到顶端有12英寸(约30厘米)长。”
植物学家的本能使得阿诺德迅速把这朵花剪下,并将其制作成标本。不幸的是,在这不久后,阿诺德就因发热而逝世。随后这份标本及其相应的图鉴被送回了英国,交由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进行研究。为纪念拉弗尔斯和阿诺德,布朗将这种植物命名为阿诺德大花草(Rafflesia arnoldii)。
在之后的岁月里,人们又陆续发现了其他物种的大花草,它们在外形、气味、生长周期上都非常相似。如今,这种神奇植物集荣誉与恶名于一身。在印度尼西亚,大花草被奉为3大国花之一;对普通人而言,它们更广为人知的头衔或许是“最大的花”、“最臭的花”;而在遗传学家眼里,它们是不折不扣的“花中窃贼”,其基因组中蕴含的谜团,直至今日也尚未被完全解开。
罕见之花1993年,阿诺德大花草和美丽蝴蝶兰(Phalaenopsis amabilis)、茉莉花(Jasminum sambac)共同被选为印度尼西亚三大国花。后两者均是由于美丽的外表而获此殊荣,但阿诺德大花草入选则是因为其稀有性。苏门答腊岛的明古鲁省是阿诺德大花草的主要生长地,此外,少数阿诺德大花草还分布在加里曼丹岛上。
除了有限的分布范围,大花草转瞬即逝的花期也让这种花朵更为罕见。在大花草长达数年的生命周期中,5~7天的花期只能算是它漫长岁月中留下的惊鸿一瞥。在开花之前,大花草已经在宿主植物体内“潜伏”了2~3年。在有条不紊地完成播种和受精后,大花草这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然后再经历1~2年的花苞期和花被期,约1%~18%的大花草能够存活下来并开出花朵。仿佛睡醒了一般,大花草会在1~2天内倏然绽放,而后花朵会在一周内迅速凋谢。1个月内,花朵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雌性大花草的花柱,孑然等待着新生命的诞生。6~8个月后,大花草果实成熟,默然等待与蓦然绽放的生命图景将再一次上演。

阿诺德大花草开花过程的不同阶段(图片来源:SUSATYA A. Biodiversitas Journal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2020, 21(2).)
奇特之花或许因为沉寂太久,大花草铆足了劲,一举开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花。目前有记录的最大的花朵来自阿诺德大花草,其直径可达到106.7厘米,重约11千克,花朵中央甚至能放下一个婴儿。“我很难描述第一次看见大花草的场景,因为相比我们熟悉的花,大花草的花朵实在是太大了。”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查尔斯·戴维斯(Charles Davis)表示。戴维斯在加里曼丹岛北部研究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时第一次看到了大花草,如今他研究大花草已将近15年。他补充道:“大花草的颜色也非常奇怪,大概处在红色和棕色之间,花瓣上覆满了白色小点。这完全不符合大多数人对花的想象。”
更奇怪的是,大花草没有根茎叶等植物常见器官。这并不是因为大花草将所有的营养都用在了花的发育上,而是与它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大花草是一类典型的寄生生物,其营养都来自宿主植物,因此不需要额外的器官来合成和运输营养物质。在宿主选择上,大花草可是相当挑剔,绝大多数大花草科植物都将葡萄科的崖爬藤属植物作为唯一的宿主。“如果你曾经被困在树林中,你就会知道最好的水源之一就是植物的藤蔓……这可能也是大花草选择崖爬藤属植物作为宿主的原因之一。”戴维斯表示。事实上,水是大花草硕大花朵的主要成分。也正是因为大量的水被运输到大花草中,它们才能在花朵发育的最终阶段迅速生长。
但让大花草闻名世界的,不仅仅是其怪兽般的尺寸和奇特的外形,还有它们所散发出的类似腐肉的诡异气味——“腐尸花”的别名也由此而来。戴维斯曾用真空泵捕获了大花草散发出的气体分子,并将其送往康奈尔大学进行检测。质谱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气体分子的化学特征与腐肉所散发出的气体分子匹配度非常高。
这种气味在大花草开花期的第三四天的中午最为明显,这也正是大花草传粉的最佳时期。对于人类来说,这种味道可谓臭气熏天,但食尸类蝇虫却对此趋之若鹜——它们是大花草精心挑选的传粉者,单次飞行距离最远可达到19~22千米。为了吸引这些小蝇虫,大花草煞费苦心:它们会提高自身的代谢水平,从而散发出热量以加速臭味分子传播;适宜的温度也能帮助蝇虫在造访大花草时,减少热量消耗。当这些蝇虫离开大花草时,它们的背上会携带非常粘稠的含有花粉的液体。这些液体能在体外保持活性长达数周,直到蝇虫将它们带给雌性大花草。戴维斯进行的田野调查表明,大花草很少开花,因此传粉和受精的成功概率也很低。“但是一旦成功,”戴维斯说,“就像是中了一样,因为雌花产生的果实中孕育着成百上千颗种子。”

大花草(图片来源:Jeremy Holden)
但这些种子是如何进入宿主体内的?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有科学家认为这些种子可能会被树鼩吃掉,再经树鼩排出后黏附在大象的脚上进行传播。也有科学家认为蚂蚁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蚂蚁或许咬开了崖爬藤属植物的藤蔓或者被渗出糖水的藤蔓缺口所吸引,使得自身携带的大花草种子能够从这些植物“伤口”处侵染宿主从而实现寄生。
基因窃贼从形态到气味再到生存方式,大花草身上隐藏着众多未解之谜。但对科学家而言,大花草最能吸引他们的是隐藏在其基因组中的秘密。
2014年,美国长岛大学布鲁克林分校的生物学家让迈尔·莫利纳(Jeanmaire Molina)决定研究大花草的基因。她想要知道的是,大花草的种种奇特之处是否在基因层面也有所体现。在对大花草的基因组测序后,莫利纳惊讶地发现他们无法检测到叶绿体基因组或者其他色素体基因组的存在。对植物学家来说,这是一项难以置信的发现,因为色素体介导的光合作用是植物的标志特征之一,在大约15亿年前原生生物就通过吞食蓝藻获得了进行光合作用的能力。“即使是疟原虫也含有色素体基因组,而它们在数亿年前就已经与进行光合作用的祖先分离了。”莫利纳表示。事实上,大花草是第一个未检测到色素体基因组的植物。
但这项发现只是个开始。今年,戴维斯及其团队发现大花草科的寄生花(Sapria himalayana)不仅不含有色素体基因组,而且它们丢失了近一半的在植物中广泛存在的保守基因。“我们知道它们肯定存在基因丢失的情况,”戴维斯表示,“但是我们没想到丢失比例会高达44%。”这项今年3月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杂志上的研究指出,寄生花中分解代谢相关基因的丢失率最高,达到了81%,并且许多基因中不编码蛋白质的内含子区域也被删除了。你或许会认为这是为了让基因组尽可能小,以减少不必要的代谢负担。但事实上,寄生花的基因组大小约为32亿~35亿个碱基,几乎和人的基因组一样大。那么,这些多余的基因从何而来呢?

寄生花(图片来源:phichak)
当戴维斯及其团队分析寄生花的基因组时,他们发现了问题的线索:寄生花的基因组中充斥着许多其他生物的基因。他们估计,其基因组中大约1.2%的基因都来自其他生物。这个比例看上去或许微不足道,但对于植物而言,就算是1%也相当令人惊讶。因为基因在不同物种间的转移并非由性交配介导,而是由一种被称为水平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的现象介导。细菌等原核生物水平转移发生的频率较高,可以达到10%~20%。但在真核生物中,水平转移发生频率较低。即使在相对简单的单细胞真核生物的基因组中,其他生物的基因占比也低于1%。
可是1.2%的外来基因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大花草会有如此庞大的基因组。哈佛大学信息小组(FAS Informatics Group)生物信息部主任蒂姆·萨克顿(Tim Sackton)在这项研究中帮助戴维斯及其团队分析测序结果。他表示:“90%的寄生花的基因都是由大量重复片段构成的。”并且,其中大约60%的重复片段都是一种可以自由移动的DNA片段,这种元件被称作转座子。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寄生花基因组中会含有如此多的转座子。
长期以来,转座子都被认为是一类“自私”元件,对于宿主没有益处,而且“要使这些元件保持沉默,生物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唐纳德·丹福思植物科学中心的植物学家塞马·沙希德(Saima Shahid)表示。她认为这些元件或许可以帮助寄生花获取一些必要的基因:“它们或许能够携带一些基因片段,并把这些片段插入寄生花的基因组中。”而萨克顿则认为,这些元件的大量存在是因为寄生花没有办法阻止它四处移动并进行复制,因为部分元件来自宿主植物,寄生花或许无法识别并沉默这些元件。“它们就像是入侵生物一样。”萨克顿表示。
要解开这个谜题,需要对基因组展开更详细的分析,例如分析转座元件与基因组其它特征元件之间的联系。但也正是由于这些重复片段的存在,解析大花草的基因组绝非易事。事实上,戴维斯及其团队在过去的15年中都在尝试解开大花草的基因之谜,但是大花草高度重复的基因片段使得基因组组装十分困难。“这就像是在完成一幅拼图,图中是蓝色的天空,而每一片拼图又都是同样的形状和颜色。”萨克顿比喻道。直到最近十年,新一代测序技术的出现,才让对更长的DNA片段测序成为可能,从而走出了重复片段的梦魇。但即便如此,据戴维斯及其团队估计,他们也只解析出了寄生花基因组的40%,其余60%的基因组片段仍然隐藏在重复序列的迷雾之中。
大花草的危机无论如何,留给戴维斯和其他科学家的时间或许不多了。漫长的生长周期、短暂的花期、人类的活动以及当地居民和科学家的采集,都让大花草科植物在灭绝的边缘摇摇欲坠。例如,大花草属的惊奇大花草(Rafflesia magnifica)自2008年起就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目前该物种数目仍在继续下降。而作为首个正式命名的大花草,阿诺德大花草的生存状况同样不容乐观。印度尼西亚明古鲁大学的保护生物学家阿古斯·苏萨蒂亚(Agus Susatya)曾在2003年走访过位于明古鲁省的三个阿诺德大花草生长地。但到2014年时,这三个生长地中却已经全然不见阿诺德大花草的踪迹。
莫利纳如今正和美国植物园合作,努力实现对大花草的人工培育。她希望有朝一日,在植物园中盛开的大花草,或许会以其独特魅力惊艳世人。人们在驻足欣赏它的美丽时,或许也会想到它身上承载的科学之谜,以及它面临的生存危机。
撰文:洪艺瑞 审校:吴非
论文链接:
Cai, L., Arnold, B. J., Xi, Z., Khost, D. E., Patel, N., Hartmann, C. B., ... & Davis, C. C. (2021). Current Biology, 31(5), 1002-1011.
Molina, J., Hazzouri, K. M., Nickrent, D., Geisler, M., Meyer, R. S., Pentony, M. M., ... & Purugganan, M. D. (2014).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31(4), 793-803.
参考文章: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dna-of-giant-corpse-flower-parasite-surprises-biologists-20210421/
https://www.harvardmagazine.com/2017/03/colossal-blossom#217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