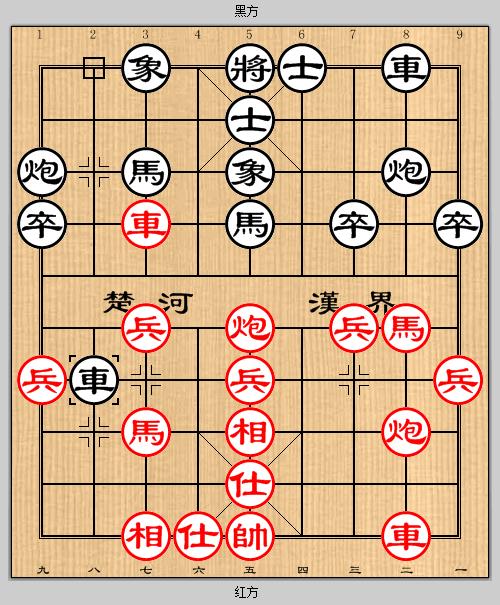编者按:2020年1月12日,吴光先生以75岁高龄不远千里、不畏严寒远赴湖南汨罗屈子书院讲学,以其温柔敦厚的儒者风采感染了现场200多名观众与在线45.8万粉丝。吴教授讲学有感而作记曰:“己亥岁腊月十七日,余赴宁波作阳明讲座,当日乘高铁行五千余里至湖南汨罗屈子文化园,次日上午参观屈子祠,下午在屈子书院讲‘儒学与中华家文化’,由凤凰网湖南频道作现场直播,据说在线听众约五十万,可谓盛矣。故撰此联,以资纪念。屈子者流放汨罗,行吟江畔,泣赋离骚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也。延陵苗裔、青溪逸民吴光谨记。”并撰对联一幅:
追溯两千年,屈子风采争日月,忧国忧君忧民困;
奔波数万里,布衣学问播华夏,弘道弘德弘人文。
在即将回程之际,我于屈子文化园卜居客栈对吴光先生进行了访谈,再次领略了先生博学多才,诲人不倦,传道不息的精神。《论语》所言:“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大概描绘的就是吴光先生的这种境界吧。
该访谈以《布衣学问播华夏,弘道弘德弘人文——著名学者吴光教授访谈录》发表于《衡水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为便于阅读,现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以“求学经历与研究兴趣”“弘道弘德弘人文”“对传统文化热的看法”为标题予以推送,以飨读者。
著名学者吴光教授访谈录:上篇
王琦: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的?在您求学的过程中,什么人或事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
吴光:我怎么走上研究的道路呢?我出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不算是书香门弟,家里没什么书,但是我国学启蒙是从父亲与兄长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的。我们村当时一个秀才叫吴顺理,是我的叔叔辈。他是章太炎先生创办的“苏州国学讲习会”的亲炙弟子。章太炎对王充的《论衡》评价很高。
我这位叔叔听了章太炎的国学讲习后,发奋要注《论衡》。但因为太用功,书还未注成,便得肺结核去世了。我经常到他们家去玩,他们家人看见我喜欢读书,就将王充的《论衡》送给了我。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就反复地读《论衡》,虽然看得不太懂,但是还是感受到这本书思想深刻,知识面广。应该说我从王充的《论衡》开始对中国的思想史有所了解。
我们当时读高中时语文课本里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其中的《原君》《原臣》对我触动很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是从新安江移民到浙江淳安的,正好碰上共产风,家庭非常困难。当时在农村也看到了很多问题,比如那个时候干部的命令与官僚作风等。因此在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时,开始对社会有所认识与思考。

王琦教授于卜居客栈采访吴光教授
进入大学后开始比较系统地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但是真正全面了解传统文化还是在进入研究生以后。因为我从初中开始读王充的《论衡》,所以在大学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论王充的思想》,是针对在文化大革命批儒评法的背景下,将王充视为批评儒家的法家而发的。文章批驳了当时将王充作为法家的杨荣国,认为王充是儒、道、佛、法家等思想都兼而有之。这文章在文革时是发表不出来的。
1978年我准备报考考研究生。因为我大学所就读的历史档案系,偏重历史,所以就想报考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专业的研究生。我就给侯外庐先生写信,由于自己手头没有中国思想通史的资料,因此希望侯先生赠送点给我。同时将自己写的王充的论文寄了过去。庐先生看完后,认为我是个可造之材,就叫他的秘书给我寄一套《中国思想通史》。但由于寄得晚,所以直到报名截止时,我还没有收到书,因此我第一志愿就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当时与历史系还没分开),第二志愿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史专业。所以人家都觉得很奇怪:你第一志愿是人民大学清史所,怎么第二志愿就跨到思想史呢?我说我本来就是想考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但因没有条件,所以报考人大清史所了。
当时人大招生的是戴逸先生与尚钺先生。复试时,戴逸先生看到我论王充的文章,对我也比较感兴趣。就问我:“如果将你招进来,您对历史更有兴趣,还是对清史更有兴趣?我说:“我对历史思想史感兴趣,如果分开的话,最好能进历史系。”
后来他们就尊重我的意愿,将我分到历史系(人大中国哲学专业是从1979年开始招生)。在读期间,戴逸先生一直很很关心我。后来他做国家清史项目时,因我对黄宗羲有一定的研究,所以就让我做浙东学派与黄宗羲,这样我就进入了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

吴光教授在汨罗屈子书院讲学
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写的道家黄老之学。最初,我导师郑昌淦教授看到这个题目时有些疑虑,觉得黄老学资料太少太杂,前人语焉不详。我说:“正因前人语焉不详,我欲语焉详之。”于是说服了导师。等我论文做出来之后,导师很高兴,认为我取得一大成就,说我不仅能搞思想理论梳理,而且还能够做考证。北大过去看不起人民大学,因为北大重考据,而人民大学光讲理论,所以他认为我黄老之学的论文,兼具考据与理论之长。我导师对我的要求比较严格,寄寓的期望也比较大,当时请了六位教授组建了答辩委员会,分别是人大哲学系石峻、北大张岱年、中国社科院邱汉生、李学勤(评审委员)、历史系郑昌淦、曾宪楷六大教授。这在当时都是很少见的。
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比较成功,李学勤先生评价我在黄老之学的研究上是“独辟蹊径”;张岱年先生认为是“迄今为止道家黄老学研究中水平最高的一篇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石峻先生的书面评语是“较之前人有所突破”。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很快就写成一本书叫《黄老之学通论》。出书时请邱汉生先生写序,他在序中写道此书是“蓬勃的理论勇气和严密的考证相结合。”
在《黄老之学通论》中,我对道家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将黄老之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老学阶段,包括老子和他的弟子(如关尹、列子);第二个阶段是新老学阶段,包括以庄子为代表的楚国庄子学派与稷下道家学派;第三个阶段是黄老学。我在黄老之学的研究上做出了一些新意,树立了黄老之学的评价标杆,即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论道家之言:“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那么,吸收儒、墨、名、法、阴阳的思想是不是老子的呢?老子是反对儒家的,他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的学说与儒家是不相容的,也即司马迁所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思想,既不是老子,也不是庄子的,而是黄老之学的。所以我以此就确立了评价黄老之学的标准,由此展开去衡量秦汉之际一些著作,如《黄老帛书》、《吕氏春秋》、《鹃冠子》、《淮南子》,我都把他们列入黄老的系统去研究,这对后来道家的研究很多启发。
我这部著作较之前人,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梳理了道家发展的历史;第二是确立了黄老学说的评价标准。因此我批判了郭沫若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认为稷下道家学派不符合黄老学派的标准,它充其量只是吸收了儒、墨的思想,既没有因阴阳之大顺,也没有撮名法之要,所以稷下道家不属于黄老学派。当时,很多人既吸收了我关于黄老之学的标准,同时又接受了稷下黄老学派。比如湘潭大学的余明光先生研究《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其实《黄帝四经》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黄帝四经》是马王堆出土的四篇文章,其中只有《十六经》一篇是讲黄帝的,另外三篇没有讲黄帝。如《称经》是各种语录汇编,既没有皇帝之言,也没有皇帝君臣之言。还有《经法》与《道原经》,也没有讲黄帝。《十六经》,有些人说是《十大经》,我当时请教李学勤先生,后来订定名《十六经》。我就确定的黄老之学的标准,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里面所提出的道家的标准,那个道家不是老、庄,而是黄老的标准。第三,是扩展了黄老之学的研究视野,所以我的书叫《黄老之学通论》,后来研究道家的人一般都要读我这本书。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光明日报》《文汇报》等13家杂志与报刊发表了肯定性的书评。

王琦教授与吴光教授在汨罗屈子书院讲坛现场
王琦:您最初做的是道家研究,请问为什么会转向儒学研究?
吴光:后来我怎么转到儒家的呢?读研究生期间,我通读了《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左传》《国语》。那个时候特别想读书,每一天晚上都搞得很晚,我熬夜的习惯就是那个时候养成。这时的广泛阅读,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的学术研究是从王充的《论衡》开始的,然后到董仲舒。当时导师想让我做董仲舒,我认为研究一个人不如研究一个学派,所以就说服了导师,做了黄老学派。黄老学派不仅是一股思潮,而且是一个学派,其中牵涉到了诸子百家中阴阳、五行、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六家,都要需要去认真了解。因此打下了诸子学、儒学研究的基础。
后来因缘际会,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了浙江去,点校了《黄宗羲全集》标点本、《王阳明全集》,还开了一个黄宗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因此受到了香港的刘绍先先生的推荐,到新加坡的东亚哲学研究所去做研究。新加坡的东亚哲学所是以儒家为主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儒家哲学做为自己的研究题目,从1988年4月到1990年1月,我将近做了两年,最后提交了《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的研究成果。我是第一个在学术界把儒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的学者。我的这个思想是继承新儒家思想而来,比如说新儒家的牟宗三着重突出了儒家的道德主体性、道德理想主义,而新儒家的另一走向则是将儒学概括为中华人文主义。我认为儒家既是道德的,也是人文的,所以我就提出了道德人文主义这个说法。
在新加坡的两年,我在儒学研究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当时所有新儒家的著作在大陆还没解禁,但在新加坡已经比较齐全与丰富了,所以就选择了这个题目,写成了这本书。从此以后,我学术研究重点就主要放在了儒学领域。
来源:“屈子书院”公众号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