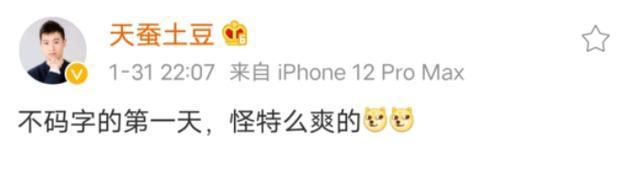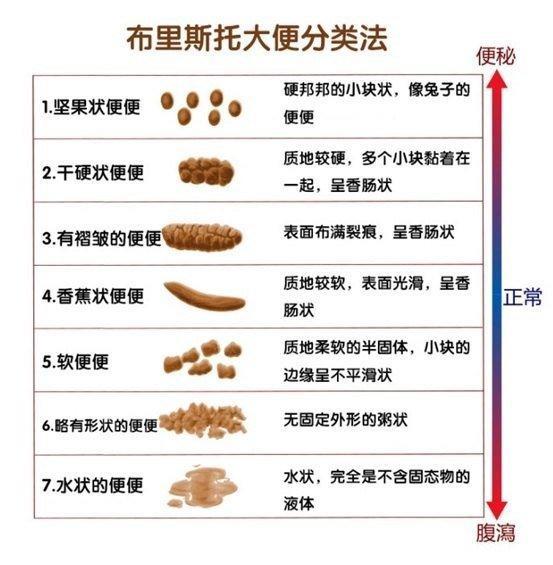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张飞刚戾好杀、暴而无恩,人所共知。
值得注意之处、是刘备“未见飞将,即知飞死”。此事不仅见于文学演绎作品,也在《三国志》中言之凿凿。
历来观点,大抵将此事看作刘备兄弟情深、甚至怀疑陈寿穿凿附会;其实并无玄机。
关键词即张飞信使的身份,是飞“营都督”。
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飞营都督表报先主。--《蜀书六 张飞传》
“营都督”即军主的护卫长,负责保护军事首脑的人身安全。彼时张飞远在阆中,而其营督却星夜奔成都、求见刘备。所为何事,不言自明。
安保负责人不在前线保护张飞的安全,却连夜狂奔到后方、连跨数级求见刘备,潜台词就是“张飞的人身安全出了大问题”。
备与飞相知多年、对其刚戾暴虐心知肚明;张飞的安全若出了问题,必是“身死军破”之事。因而有那句流传千古的“噫!飞死矣”。
先主闻飞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飞死矣。”--《蜀书六 张飞传》
此事无关乎心灵感应、而是理所当然罢了。
本文共 4900 字,阅读需 10 分钟
张飞的早年履历孤微发迹,使张飞对出身极为自卑。这是其成年后“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现实来由。
张飞行伍出身,粗猛擅斗,与关羽并称“万人之敌、熊虎之将”。
虽然后世文学作品攀缘附会、对张飞的早年经历多有演绎,其实皆不实之词。
常见的演绎,有“猪屠出身、家富于财”;又有“面白如玉、擅长书法”,甚至南朝陶弘景在《刀剑录》中还有“凿山铸铁、炼作神兵”等等。以上皆谬。
张飞的早年履历不详,出身亦不详。卢弼《集解》包揽群书,对张飞发迹前诸事、完全不见记载。可见东晋南朝时,学者对张飞之事已不甚了了。
如陶氏《刀剑录》成书于张飞死后三百年,已经舛谬频出。称其刀铭为“蜀新亭侯刀”。
“蜀”是魏吴的蔑称,“汉”才是刘备集团的自称。若铸刀之事属实、刀铭当作“汉西乡侯刀”云云。
张飞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炼赤朱山铁为一刀,铭曰新亭侯蜀大将也。--《古今刀剑录》
张飞命匠炼赤朱山铁为一刀
至于所谓的“杀猪佬儿”、“白面郎君”、“书法家”等穿凿衍文,更是令人发笑,不值一驳。
张飞的真实出身,从刘巴与诸葛亮的对话记载中,可略加窥见。
刘巴骂张飞为“兵子”(一种侮辱性称谓),而诸葛亮也承认“飞实武人”。
巴曰:“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零陵先贤传》
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零陵先贤传》
可见张飞出身寻常、发迹行伍,是彼时人所共知的事实。
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原生烙印、往往会伴随一生。登高者自卑、涉远者自逊,不外如是。
与关羽相异,张飞虽然出身寻常,却特别热衷“攀龙附凤”之事。
魏晋时代军人地位低下,“武人”、“士息”、“兵子”等皆侮辱性称呼。比如荆州刺史琅琊王睿,便因孙坚“出身武人”,言语侵凌,为坚所杀。
叡先与坚共击零(陵)、桂(阳)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吴录》
又如张昭侄子张奋投身行伍,被张昭讥笑,称其“自降身份”云云。
(张)奋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车,为步骘所荐。昭不愿曰:“汝年尚少,何为自委于军旅乎?”--《吴书七 张昭传-附传》
在“贵文贱武”的背景下,便衍生出许多可笑之事。
比如(兖州)山阳豪强李典,麾下奴客三千,宗族万余,却“好学问、敬贤士大夫”,被冠以“长者”的称号。
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军中称其长者。--《魏书十八 李典传》
须知,李典死时不过三十六岁。所谓的“长者”,不过是士族利用舆论塑造“好榜样”罢了。
另有东吴凌统、两代将门,亦爱敬乡贤、对长吏极尽礼数。得到时人的交口称赞。
(凌统)过本县,步入寺门,见长吏怀三版,恭敬尽礼,亲旧故人,恩意益隆。--《吴书十 凌统传》
在此背景下,张飞也潜移默化地沾染了“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恶习。
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蜀书六 张飞传》
君子与小人,非人品含义,而是隐喻出身和地位。说得再明白一些,张飞喜欢攀附上位者、出身高贵者;却鄙视下位者、出身卑贱者。
比如上文提到的零陵刘巴,世代高门,巴父刘祥还是益州牧刘焉的“仕途举主”。因此,虽然刘巴被刘备“宿昔所怨恨”,张飞却卑躬屈膝,拜谒刘巴,结果吃了个大闭门羹,狼狈而去。
张飞尝就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零陵先贤传》
与“爱敬君子”相反,张飞对待武人或下级,却极尽侮辱之能事。
比如镇守徐州时(196),张飞便与中郎将许耽与军司马章诳构衅,又侵凌曹豹。最终下邳暴乱,吕布趁虚而入,坐城放火,大破飞军,揍得张飞星夜亡奔石亭。
备中郎将丹杨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吕)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英雄记》
再比如江州之战(213),张飞生擒守将严颜,不知抚慰,居然喝骂“何不降而敢据战”。见严颜不为所屈,竟要“牵去斫头”。
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蜀书六 张飞传》
严颜不降,飞怒,令左右牵去斫头
虽然此事最终和平解决,但张飞“鄙视武人”却可见一斑。否则“义释严颜”也便没有大书特书的必要了。
可想而知,以往落到张飞手中的“小人”(武夫、出身卑贱者),大概率就是“立毙刀斧”。
如果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张飞的婚姻问题,可能也是“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现实映射。
张飞虽然生年无载,但“少从先主周旋”,可知二人年龄相若。彼时(178-184)刘备在涿县“合义兵”,不过二十出头年纪,可知飞亦如是。
张飞二女先后嫁刘禅为皇后,可知飞女与备子年龄亦相若。问题在于,刘禅是刘备四十六岁所生,可知张飞生女,亦极晚。
后主敬哀皇后,车骑将军张飞长女也。--《蜀书四 二主妃子传》
飞妻是夏侯渊侄女儿,在本郡“出行樵采、为飞所得”。谯沛夏侯氏是西汉开国滕公夏侯婴后裔,属高门之后,因此“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
建安五年,时(夏侯)霸从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魏略》
至于往日被张飞“抄掠所得”的女眷,如果出身寻常,下场如何,也便不难想象了。
张飞其人的价值观、可见一斑。
暴而无恩张飞之暴虐,史不绝书;且专以“凌下为务”,更为可憎。
张飞“暴而无恩、刚戾多杀”人所共知。类似的武夫颇为常见,比如甘宁“粗猛好杀”,于禁“肆其杀心”皆如此类。
(于禁)肆其好杀之心,以戾众人之议。--裴松之
甘宁粗暴好杀,既尝失(吕)蒙意,又时违(孙)权令。--《吴书九 吕蒙传》
但张飞好杀,与诸人相异。
张飞的“刑杀过甚”(刘备语),是源自其“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扭曲心理。
换言之,对待刘巴一类的高士,即使受尽侮辱,张飞也能矫情忍性;但对待地位低下的军士,张飞便逞其滥杀之能。
刘备与张飞相交四十载,对飞之“暴虐凌下”目见耳闻,心有戚戚。经常会善意提醒,让其“克制刑杀”,但飞“听而不改”。
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飞犹不悛。--《蜀书六 张飞传》
张飞又有虐待士卒的恶习。
试想,严颜贵为巴郡太守,尚且被张飞“牵去斫头”;许耽、曹豹、章诳身负戍卫重任,结果被张飞或打或杀。对待中下级军官尚且如此,对待白身士卒,又会如何?
按刘备所言,飞似有恶癖,日夜鞭挞军健,肆其淫威。刘备孤微发迹、喜怒内敛,有识人之明,屡诫三弟。结果张飞不仅不听,还把受过鞭笞的士卒,置于左右,以逞其能。
(飞)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蜀书六 张飞传》
刘备见状,长叹“此取祸之道也”。
飞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
刘备僭位汉中王时,曾授关张二人“假节”。
关羽好理解,身边另有监军(糜芳、士仁),假节以增其威重。
张飞的假节,可能另有深意。即刘备刻意限制张飞的滥杀恶习。
主君授予臣下节钺,大抵有三级。最高级是“使持节”,可擅杀二千石以下高官;次级是“持节”,可杀白身无官位者;最次级是“假节”,只能杀触犯军令者。
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宋书 百官志》
关羽假节,以糜芳士仁运粮误期,便可威胁“触犯军令”而杀之;假节是增其权位。张飞假节,却并非如此。
按假节只能杀“犯军令之人”,张飞的辖区(阆中)又不在前线,下属犯军令的概率相对较低。故刘备“假节”张飞,很可能是刻意限制,免得给了更高权限,导致张飞愈发滥杀无度。
问题是,三爷平日杀人、几曾遵循过法度?在张飞帐下,怕不是咳嗽一声、便是断头的罪过。张飞未得假节之前,已是恶习缠身;给了假节,更助长了嚣张气焰。
张飞之死善骑者坠于马、善水者溺于水、善饮者醉于酒、善战者殁于杀。
杀害张飞的凶手,范强、张达二人,身份非常有趣。这是解释张飞之死的关键所在。
范、张二人,是张飞“帐下将”,与“营都督”应属同一系统,即“护卫张飞安全”的亲随武官。
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蜀书六 张飞传》
这也能解释,为何在“护卫昼夜绕帐环立”的制度下(参见《典韦传》),张飞居然能被斩首。
(韦)性忠至谨重,常昼立侍终日,夜宿帐左右;稀归私寝。--《魏书十八 典韦传》
因为张飞死前,“帐下将”已皆有叛心,范、张不过是领头人。至于其余护卫,恐怕亦多有串谋,至少是保持中立,乐见张飞被杀。
一言蔽之,张飞死前,已是人心尽丧。真应了刘备那句“卿鞭挞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的预言。
“营都督”飞报刘备时,备闻听是张飞的“安保负责人”跨级求见,便已知晓张飞身死。
“刑杀过甚”之人,不出事儿就是没事儿,出了事儿必是大事儿。
“营都督”因为职责特殊,一贯是被主将宠赖有加的“腹心之人”。
比如关羽败走麦城时(219),身边跟随的大将是(儿子)关平、与(营都督)赵累。最终三人被吴将马忠击斩,未见变节。
(潘)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吴书十 潘璋传》
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
再比如孟达率部降魏时(220),其营都督郤揖,便放弃质于成都的家小(郤正),跟随主将叛变。
(郤)揖为将军孟达营都督,随达降魏,为中书令史。--《蜀书十二 郤正传》
张飞的营都督,眼见“帐下将”变节叛逃,甚至谋害主帅,却一无所为。纪律竟败坏到这个地步。
其实也不能全怪营都督,就张飞这种“日夜鞭挞、刑杀无度”的狂徒,他连刘备的话都不听,难道会听营都督的话?
“不恤小人”的张飞,平日里如何对待下属,路人皆知。张飞的营都督,名为卫戍、不过备位充数而已。
小结张飞之死,咎由自取。
“爱敬君子者”有之,凌统、李典皆为表率。
“不恤小人者”亦有之,甘宁、于禁实为翘楚。
问题在于,凌统、李典口头上爱敬君子,行为上却也颇为儒雅,有“贤士令名”。张飞却日夜殴打士卒,肆其淫威。
甘宁、于禁虽然不恤小人,但懂得“斩草除根、不留遗祸”的道理。
甘宁曾虐待厨子,捉回后立刻射杀。于禁刑戮过甚,从来不留活口,乃至身败名裂后,竟被上谥号“厉”。按谥法,杀戮无辜曰厉。
宁厨下儿曾有过,走投吕蒙……宁许蒙不杀。斯须还船,缚(厨下儿)置桑树,自挽弓射杀之。--《吴书十 甘宁传》
谥(于)禁曰厉侯。--《魏书十七 于禁传》
张飞一方面“爱敬君子”,另一方面“不恤小人”。从根源上说,这是对出身的自卑,因此攀龙附凤,自抬身价。另一方面看,张飞凌虐士卒,又令在左右,乃至刘备劝诫而犹不悔改,亦可见其自恃武勇,骄悍难驭。
这与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表面相异,内核相同。皆是“自负才武、傲慢骄矜”的表现。
因此,关羽虽号称“善待卒伍”,但荆州之败,士卒尽叛。按孟达所言“荆人变节、百不存一”。
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吴书九 吕蒙传》
张飞虽号称“爱敬君子”,实际真正的名士刘巴,连话都懒得和张飞说,直接给了个闭门羹。
张飞尝就巴宿,巴不与语。--《零陵先贤传》
可见,关张二人,无论其口中爱憎如何,不过都是“自恃勇力、轻慢他人”的表现罢了。他们既不爱君子,也不爱小人,只在乎自身利益与刘备情分而已。
“爱敬君子”的凌统与李典,“不恤小人”的甘宁与于禁,大抵得其令终(于禁例外);但“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的张飞,却横遇飞祸,身首异处。
究其原因,恃才而骄、名实相悖耳。
陈寿所谓“以短取败、理数之常”,可谓精洽。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Thanks for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