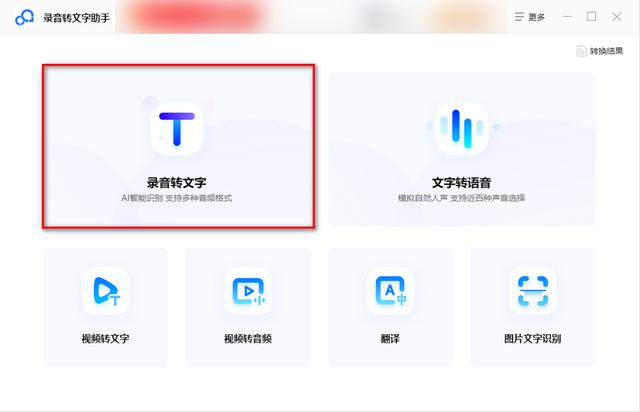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父亲母亲是一对极为普通的农民,父亲13岁丧父(我的祖父去世)虚岁14岁上就去学木工手艺,经常清早挑工具出村,为邻村村民做房子,打家具,修农具等在顾主家吃过晚饭又摸黑回来他没有上过学,但是认得好多字特别是关于木工活的相应术语,每个工程的所需材料他都记得清楚,计算得准确无误比如瓦樑,桷子,屋脊挑檐,横竖上下,前后左右,东南西北,长短尺寸等等都能熟记于心这是在师傅的教导下学识的,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母亲是一对极为普通的农民,父亲13岁丧父(我的祖父去世)虚岁14岁上就去学木工手艺,经常清早挑工具出村,为邻村村民做房子,打家具,修农具等。在顾主家吃过晚饭又摸黑回来。他没有上过学,但是认得好多字。特别是关于木工活的相应术语,每个工程的所需材料他都记得清楚,计算得准确无误。比如瓦樑,桷子,屋脊挑檐,横竖上下,前后左右,东南西北,长短尺寸等等都能熟记于心。这是在师傅的教导下学识的。
他的师傅是本村人,父亲的堂叔,我们叫柏爷爷,他是当年县城以北有的建筑木工,做民房做祠堂样样精通。上世纪二十年代,他还积极参于共产党组织的农民协会,帮助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参加过第一次土地革命,当过村苏维埃主席。红军大转移〈长征)后,师傅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捕,被迫暗中举家搬迁到另一村生活,从此低调谋生,暗中还协助党组织做好各种工作。父亲受到师傅的影响,也能讲出许多革命道理。
小时候父亲在家时,在夏天的月光下,家门口的草坪上,放上竹床乘凉,我们拿小板凳坐在父亲傍边听父亲讲故事,常娥奔月,七仙女下凡…他还吭得一些京剧和采茶调,他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讲秋收起义,南昌起义,毛主席率领红军上井冈山,共产党率领红军发动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讲三国,讲水浒里的英雄人物,中国四大名著里的有关故事都能讲得头头是道。〈他可能也是听评书丶说书佬和瞎子戏里学来的)反正我听得津津有味。他对人谦和有礼,重情义,忠厚老实。做事一丝不苟。在县城以北十里八乡稍有名气,与城头刘厚万刘厚铭刘坑乡黄伯良等齐名。也可能是名师出高徒的原因吧。
父亲长年四季大部分时间在外做木匠活,家里分得的水田旱地基本上由母亲一人打理。
母亲年轻时人高馬大,约17o㎝高,五官端正,身体粗壮,象个男子汉。此前她是邻村女子,经媒婆介绍嫁给我父亲。她娘家也是贫苦农民出身,外公外婆生二男一女,外公早年去世,大舅舅去当红军,参加过一至五次反围剿,长征后一直查无音信。二舅舅三年困难时期因病去世,二舅妈改嫁,二舅舅的女儿抱养给县城一家富户做童养媳。母亲成婚后,外婆孤身一人生活,思儿念女又担心孙女,常年暗自流泪,以致双目失明。虽然享受烈属优抚,日常生活还是靠堂舅舅舅妈照应。(堂舅舅的儿子过继到了红军舅舅的名下)。
一九五几年互助组合作社之时,我家分得的土地主要在雪竹坑,过龙背,狗嘴底(大塘尾水库用地)大部分是不向阳的冷浆田。有县颁发的土地证,盖有县政府公章,县长宛华的公用章。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才把土地统统入社,由集体统一耕种。(农户每户按人口分得少量自留地)
互助组合作社(单干)时期,农忙时父亲负责犁耙载插,后面田间管理(耘禾锄草施肥)主要靠母亲。把小孩放到奶奶家里,自己一人去田园忙前忙后。大姐二姐读到小学毕业就被迫停学,要帮助做农活,大哥考上中学读到一年,学校寄宿,生活艰苦,吃不了苦就回家种田了。
父母生我们兄弟姐妹八个四男四女(有一女孩小时夭折)两个姐十七岁左右就许配了人家。我四兄弟加一个小妹,大哥与父母一起参加生产队劳挣工分,我和两弟一妹还在读小学初中,在上世纪50,60,70年代,父母亲为了子女上学,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早出晚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父亲外出做木工要交生产队积累〈现金)出去一天交1元记10分工分。母亲在队里劳动一天记6点5分,早上不出工(在家煮饭)中午下午出工,按o点8天计算得5分2厘工分。哥是年轻人,一天可挣9分5厘。按当年的工分值一天10分工分能得8角9角就不错了。大哥赚了几年工分,到二十三岁上就经人介绍结婚成家立业,第二年就另起炉灶分开过了。那时我还在读初中,两弟一妹还在读小学。
父母亲对子女的文化教育问题,在当年的农村来说还是算很重视旳。二个姐有小学文凭。(一九五几年)哥读了初中,而我和弟弟妹妹可以凭自己的本事读到高中大学都可以。我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优秀,年年都是班上前三名,考虑到家庭负担重,父母亲挣工分难,要让两个弟一个妹读书,所以主动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班主任老师对我两次要填报上高中的志愿,我很感谢老师并对他讲了家里的实际情况,他说那你填共大分校也好啊,我勉强填了共大分校(半工半读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话问题)可是后还是没录取。据说是因为社会关系问题。也好,我反正也没打算再去上学。就这样回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建设了。
父母亲为了锻炼我们兄弟治家理财的能力,谁快到成家立业的年会就谁来管家,谋划一年的经济收入,购买生产队分配的粮油物资,弟妹读书费用,全家人的衣着穿戴,人情世故红白喜事,伤风感冒等开支。不够就想法增加收入。比如多养肉猪,养母猪卖猪仔,多养鸡鸭鹅等增加家庭副业收入。承包生产队鱼塘增加工分收入。
当然所谓管家是以父母占主导,儿子积极参与商讨决策,现金收支还是由母亲掌握。谁结婚成家后,第二年新谷出来,秋后就分家另外过。兄弟每人都有一次在家长指导下实习管家的机会。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道理未结婚前就已经体会到。
由于父母的精心策划和安排,我们兄弟每个人结婚成家都不要向他人借钱借粮。办好喜事还略有节余。父母为子女操心一辈子,而当他们年老时,我们只给老人分耕责任田,约定每户给大人一点零花生话费。也可凭自己的良心和对大人的尊重态度多给一点钱,另给父母买些鞋袜衣帽。平时有人客到不忘请父母一起聚聚。他们虽已6o,70岁,还坚持自已种菜,养少量家禽,父亲还种了几年药材红花卖。当然有时间也一样照看孙子女。当他们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时,做子女的还时没有经常嘘寒问暖,至今仍非常惭愧。
父母年事已高,加上积劳成疾,于1990年代先后仙逝,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里路。
现在我们兄弟姐妹个个都称得上三代同堂的老年人了。每每想起父母亲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宠爱都会深切怀念,感激涕零,暗然泪下…
二0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