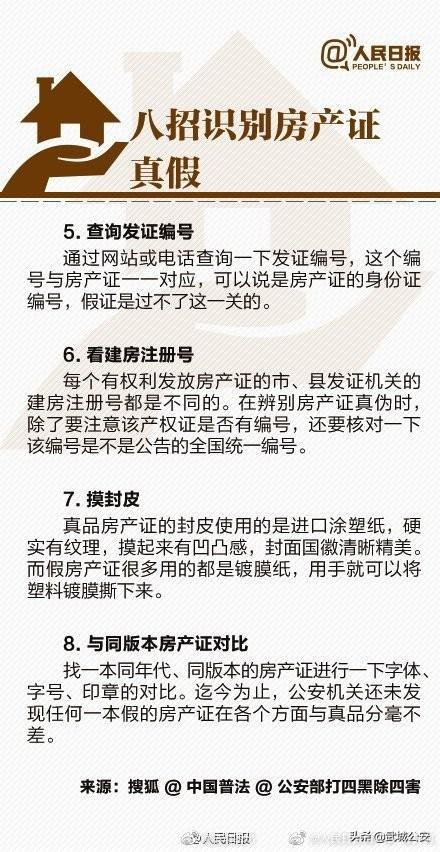百鸟朝凤,经典的唢呐电视,经典的唢呐曲。但是在我心里却无法排的上第一唢呐曲,只因我从小就在我父亲的唢呐声中长大。
父亲的唢呐声远没有《百年朝凤》这么肝肠寸断,也不会一响上云霄,在我听来有的只是一顿胡吹乱吹,一顿嘈杂声,谈不上任何音乐的美感,嘴里还念着我永远听不懂的曲调"工车上工车上工车上,火死火工车上…"
也不知道这些我记得对不对。我们那个生产大队有个典子队,父亲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唢呐手。父亲参与其中的目的不为音乐,也不是子承父业,只是为了能吃个饱饭。
父亲出生在1955年,那是个吃不保穿不暖的年代。他是屋里的长子,而爷爷体弱多病。为了支撑这个家,父亲以半天读书半天回家带弟弟下地干活的方式在读完五年级后彻底离开了课堂。为了能多个挣钱的门路也许父亲就学习了唢呐,加入了红庙典子队。在别人家有丧事时送葬,这样能得一条毛巾和其他的物质,以此补贴家用。
在我小时候,父亲的唢呐是他的宝贝,从来不让我碰,怕我把他的唢呐摔坏。他用的吹嘴是用芦苇杆做的,先把一根直径约8mm的芦苇杆放在开水里面煮一煮,然后再把一头压扁,然后中间用铜丝围起来。每次把吹嘴做好以后就会放在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也不允许我去拿。这种吹嘴简单实用,但寿命不长,往往用了几次就坏掉。
那时候的父亲精力还比较充沛,夏天的晚上他会吃完饭以后将几个碗一次性摆开,然后一只手拿着一只筷子,一边敲打着碗嘴里一边念叨着他的曲谱,对着繁星点点的夜晚,总要敲上个把小时才过瘾,说是为了以后"演奏"时能合得上别人敲的鼓。
冬天的晚上,父亲在房里会练习唢呐,母亲总会觉得吵,于是他就去客厅吹,灯也不开,黑乎乎要吹老一会。常年的吹唢呐,父亲早就练得一颗肺活量巨大的肺,小时候的我和别人在水下比憋气,只遇到过一个对手,而他的父亲也在红庙典子队吹唢呐,也许这都是遗传了父亲的习惯。
后来的父亲开发了一项新的技能,那就是在搞"坐吹",有人结婚的时候他们就坐在主人家大门口迎宾,来一个客人吹一会。还自讽为"看门狗"来个人吠一声。
搞"坐吹"的待遇比做丧事要好的多,好吃好喝招待着还能拿到不少喜糖。小时候最希望父亲能去搞"坐吹",这样晚上我就能有不少糖或者饼干等零食吃。
为了搞好"坐吹"父亲还学习了其他乐器,笛子、箫等,偶尔还能看到他敲个鼓啥的。也许是年纪大了,也许是常年劳作的原因,父亲吹的唢呐声音被人觉得不那么动听,搞"坐吹"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等到去年回家我发现父亲已经在用他的第5杆唢呐了,而用的吹嘴也不再是自己用芦苇杆编制的,而是买的那种塑料管做的,轻便干净,寿命更长,吹起来声音也更加细长悦耳。
父亲的唢呐声永远无法达到《百鸟朝凤》的高度,也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父亲的唢呐声与音乐无关,有的是对生活的坚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支撑一个家庭而做出的不懈努力。那也是从小伴随着我长大,为我的童年带来不少零食的唢呐声,在我心里那嘈杂的唢呐声永远是第一味的唢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