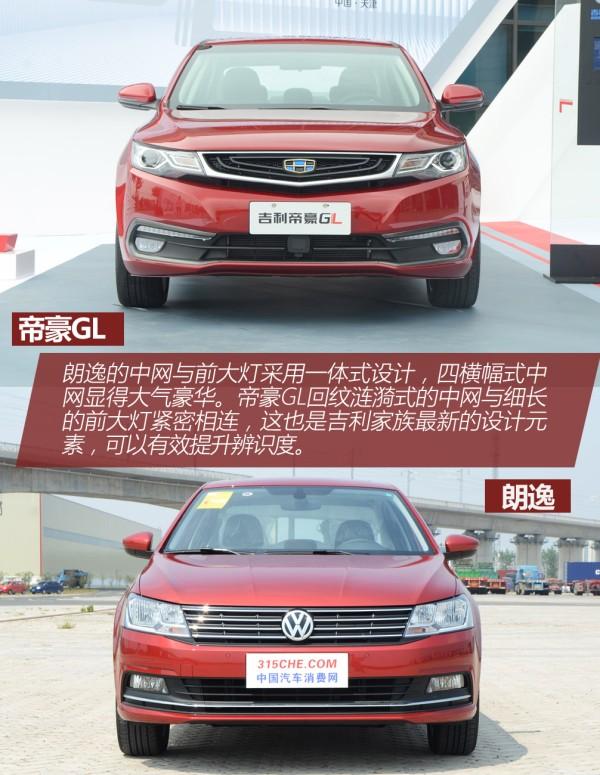杨绛振华上学记
十年之中,几次北上,去拜访杨绛。每次去看她,最多的话题,是当年她所读书的“振华”,振华是我们苏州十中的前身,那是一所女校,开始是小学,后来又办中学,再办师范。杨绛在那儿待了六年。她对这里有着太多的记忆,早年她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事业》,几乎是以在“振华”读书的经历为素材写下的,我曾当年问过她:是不是?她微笑、点头。那是在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那是2005年12月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与北京“振华校友会”的几个老人,一起去看望她,这些老人都是很有建树的人了,可是在杨绛面前,都是小妹妹,她们小心翼翼地敲门,小心翼翼地说话。杨绛那年95岁,身体硬朗,典型的江南女子的气质与风度,开门、让座、端茶,温文尔雅,吴侬软语。
杨绛说,振华有一股味儿。这股味儿,影响了她一生。坐在她家书房,几张沙发、一张写字台、几张书橱,曾是钱钟书书房,钱钟书去世之后,杨绛就在这里读书、写作,也在此接待亲朋好友。她执意让我们坐在沙发里,自己放一张木凳子在两张沙发的中间,处于墙角,她就坐在那儿。就像一个慈祥的祖母或外婆,我们对她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我们也小声开口,小口喝茶,也变得斯文有风度。杨绛说往事、说她的王校长季玉先生,交谈间,不时发出笑声。

我为杨绛拍了这张相片
杨绛说,我在“振华”的时候,还不在今天的织造署旧址,是在严衙前那个老振华校舍。一个大的、私人的宅子。外面门房,进来轿厅、大厅,后头几进是住房。在轿厅与大厅的上用木板与洋铁皮,搭成很简陋的六个教室。现在,我闭着眼睛也想得出来,哪是校长办公、教员办公室。后面楼底下的大厅,就是大课堂。早上朝会,就在这个大课堂里。教室四面漏气,很蹩脚。英文是请外国先生来教的,有一个长得很美,在隔壁上课,我们就常凑到板壁上的窟窿前去偷看。化学实验室,就在我们隔壁。有一次,试验的是做硫化氢。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味儿?隔壁做实验,我们就怀疑是谁泄了气。曾冤枉过一胖一瘦两个妹,大家笑,下了课才知道是化学实验室里冒出来的臭味儿。
王校长季玉先生,特别认真,又特别随和。我与她在一起那么多年,每天早上第一课就是训话。就是朝会,就是训话。她总说,伲(苏州话)振华,实事求是。她说话有点儿卷舌头,我们学不像,就问她了,你干嘛要卷舌头呀?她说小时候父母在外做官(父亲王颂蔚,在清廷军机处做章京),保姆是外省人,所以说话也有点儿卷舌头。大事小事,都从‘实事求是’说起。小事情也要讲,如,家里带来了菜,不要一个人单吃、不给别人吃,我们大家要过好集体生活等。我们是跟季玉先生一桌吃饭的,老师都与学生一桌吃。所以,我们的伙食一直都很好。其他学校就不一样了,校长单独先吃,然后教师单独吃,最后才是学生吃。夹菜用公筷,大家先把菜夹在自己的碟子里后才吃。吃完了饭,一双筷子搁在碗上,坐着,等都吃完了才一起离开,这是规矩。
1996年是学校百年诞辰,我们请杨绛题词。她坐在客厅的一张写字台前,挥毫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然后又写了一行小字“季玉先生训话”,落款写着“杨绛敬录”。她小心翼翼,自己端详着题词,一再说,写得不好。九十五岁的高龄,写出如此笔虬劲的字,让我们欣喜。
回来以后,我们精选了金山石,把题词镌刻其上,树立于西花园。这是杨绛对母校的纪念,她把她对季玉先生的情感,都凝聚其中了。杨绛说,季玉先生上课特别凶,可是等到晚上,就完全与学生打成一片了。校舍是老房子,有一条很长的陪弄,从前头通到背后。晚上,弄堂里只有一盏灯,点在大课堂的门口。季玉先生站在灯底下,我们学生都站在灯底下,我们说的话,她都听。有一次,我对季玉先生说,你叫我一声阿姨吧。我说,今天太先生(即振华的创始人、王季玉校长的母亲王谢长达)和我说话,她叫我‘季康妹’。季玉先生与我们亲密无间,没大没小。有时,我们有点儿什么不愿意,就当面跟她嘀咕,没有隔阂。我们可以与她吵,与她犟,与她胡来,什么都可以。我们的感情却是顶顶好的,大家都很爱她。
那时候,我们振华的老师都是东吴大学的老师,兼职,水平特别高。振华学生的成绩也特别好,我们用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的,数学、化学都是,音乐、唱歌也都是。课堂上我们也都说英文。许多好的老师,都是名人。
对杨绛这次拜访,给了我们启示,学校改造的时候,我们把历史与文化,物化以后散落在校园之中。建造了“季康亭”,亭子后面连着一条蜿蜒的长廊,长廊与西花厅相连。季康是杨绛的字,她是值得纪念的校友。亭廊里有许多石刻,镌刻着杨绛读书时许多老师的画像与生平,王骞、叶楚伧、颜文樑都在那儿,小小的振华学校,能够延请到他们,可想杨绛到是何样的教育?
杨绛说,振华有许多“会”,像今天的学生社团,如“英文会”,两个礼拜一次。活动时不许说中文,只许说英文。还有什么“演讲会”,所有的人都得上去讲。我刚到振华那一年,才十二岁,真吓死我了。到图书馆里去找篇目,找到一篇,背了出来。演讲会就在大礼堂,站到台上,看见下面全是人,吓死了,背到一半背不出来了,吓得我直哭,没办法,我要下去,迷迷糊糊,竟直接从台当中跳了下去,逃了。评判的时候,老师说我上半段讲得还可以,竟给了我鼓励,不可思议。后来,我还当上了学校演讲会的会长、英文会的会长。振华的许多同学,毕业后都考金陵大学。我也去考了,考取了,还考了第一名。金陵大学校长吴怡芳到我们学校来,季玉先生叫我坐在她旁边,动员我,可是我放弃了,报考了东吴大学,最终又去了清华大学。振华的课程比其他学校的都要多,丰富,要求也高,我们考起来分数也总比别人高。我们每一个星期六都要“会考”,中学、小学部,所有的人都要参加,考常识,许多时候我都会考第一名。也考时事,时事我不行,我不看报,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考,考不出,也得坐着,到时间才能离开考场。
振华条件一般,与其他学校过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我们艰苦,又都是自治,样样都靠自己。其他学校教室的地板是广漆的,拖地的有“娘姨”。我们没有,早上起来头一件事就是做值日扫地。地板都是烂的,有的烂成窟窿。扫头发,头发都被缠绕在扫把上。桌子,也是自己抹,衣裳呢,也是自己洗。都用井水,自己吊水。舍房里,每一间都有房长,每一个人轮值,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当时,常打仗,有一次得到消息,我们出去躲,每一个人穿个大棉袄,带一个小包包,里面一块洗脸布,一支牙刷。大家排着队,黑地里,就跑到“景海女中”。她们每个人让出半个床,与我们合床。穿着衣服,脱了鞋,挨头就睡。第二天早上起来,没吃早饭,也没有洗脸漱口,排着队,又回到自己的学校。回到学校,正是大考的时候,马上照旧考试,一点也不松懈。
杨绛说,那时振华十分重视户外活动的。校舍很小,活动余地不大,季玉先生常赶我们出去,可是只有一个操场,也就一个篮球场大,紧贴着就是墙根,地下铺的全是泥沙。于是,每个星期组织我们去南园,南园在城南,当时是一片田园,去散步、跑步,偶尔还去菱塘里采菱。学校还经常组织我们去东吴大学参加大学生的活动,各式各样的,有的活动幽默、风趣,也要“捉弄人”。一次台上大叫,叫大家掏钱扔钱,说谁掏得多、扔得多,就会生个大胖儿子。季玉先生耳背,听不清楚,也没有弄明白,就学别人的样,也在那儿掏钱、扔钱,大家忍不住开怀大笑。我是一个淘气、爱玩的人,可成绩还不错,季玉先生就让我跳一级。但课程不能少,初三与高一的课都要我听,同一年里我学了两个年级的数学,居然都跟上了,我再也没工夫淘气了。
杨绛与费孝通是振华的同学,还同班。杨绛说,有人说我们同桌的,其实不是。他是好学生,我是坏学生。上体操课,我们排队,我长得矮小,排在最后边,他就再排在我的后面。体操课要学跳交际舞、民间舞,两个人一组,手勾着手。我发育得晚,啥也不懂,费孝通懂事早,不与我跳,只站在我旁边。跳不起来,我就生气,就与他吵架。我说,你比我高,你应该排到前头去。他说,前面是女生,不能去。我说,我们都是女生,为什么还来这儿?我在沙坑里画他,画一个丑化的脸,张着嘴巴,哇哇叫。后来费孝通的夫人只要见了我,就会提起这个事,她对费孝通说,你女同学可凶啊。杨绛讲这件往事的时候,一脸的笑容。学校的任务,是要保护孩子们的那种童真,直至永远,除此之外,无他。

杨绛为母校题词时的情景
杨绛是振华的学生,后来又回来当校长。那是在1937年,苏州沦陷了,振华搬迁到上海租界。提到这件事情,杨绛问这算不算?问得挺真诚。我们说,这是历史,当然算,不仅算,还要大书一笔。杨绛说,那个是季玉先生“逼”我当的,她对我哭,说把自己都嫁给了振华,日本人来了,不能再在苏州办学,只能去上海,你不帮谁能帮呢。我被感动心软了,我对季玉先生说,我帮你。她很高兴,马上请孟宪承先生(他后来成为华师大第一任校长)到教育局去立案。我那年二十八岁,看样子很年轻,当校长要老成,我拼命装老,装也装不像,把头发卷起来,像个传道婆婆。很可怜的,我什么事情也不会做,但什么事情都要做。包括去找校舍,我与季玉先生天天出去跑,要六个班级,至少六间房,看中了大房子租不起。季玉先生交给我一个存折,是美金,是她省吃俭用多下的钱,她让我带着,是全部的办学经费。三千块钱,物价飞涨,三千块钱像泡了汤一样,不值钱,她吃的是什么?是糠虾,蘸蘸酱油下饭。牛奶馊了,也不舍得倒掉,说那不等于酸奶么,就吃酸奶。季玉先生有一句话 “居无求安食无求饱,先人之忧后人之乐”,是她自己的写照。我曾给她买了一件羊毛衫,给她,她死也不肯收。我说,学生孝敬你,你为什么不能收?她回答我,“我从来不收人家礼物的。”我给她织了双袜子,她是大的小脚,我是按着她的尺寸给她做的,她说,我不穿的。我对季玉先生发脾气,当着她的面都拆光。杨绛说到这儿很深情,她接着说,季玉先生在在这个方面是非常伟大的,对我影响很大。她还交给我一枚振华的校印,我都拿了。除了管学校,还再教一门高三的英文。爸爸说我这是“狗耕田”。
八十多年之后的回忆竟是那么清晰。杨绛知道我们要来,一大早,坐在桌前,默忆当年的校歌,然后恭敬地把它抄在纸上。我们坐下以后,她唱给我们听:“三吴女校多复多,学术相观摩。吾校继起,德知体三育是务。况古今中外,学业日新月异。愿即时奋勉精进,壮志莫蹉跎。”开始是小声地哼,慢慢唱出了声。杨绛说,我耳朵背了,那个音也就掌握不准了。她还记得唱校歌穿什么衣服,深棕色的校服,黑鞋子,白袜子。

杨绛为母校题了“实事求是” ,如今石刻留在校园里
杨绛有血压高,激动了,血压就波动得厉害,就流鼻血。她风趣地说,往外流不怕,就怕往里流了,往里流可就有问题了。多令人尊敬的老人啊。先生离她而去了,女儿也离她而去了,一个孤独的人,每天浸润在对亲人的怀念之中,她为钱钟书与女儿整理文稿,她说,那是打扫战场。累了,身体不舒服,就闭上眼睛。学校西北角,有一小丘,树木葱郁。最高处有一小亭,杨绛兴致很浓地说到了它。她在老宅子读书,毕业之前学校被允搬迁到清朝织造署遗址,她参加了搬迁劳动,这个小亭是她参与一起搬砖头建起来的,是毕业纪念物,现在就成了杨绛念想。拜访即将结束,我们要告辞了,杨绛说,请把我对母校的想念带回去!
2005年的拜访,九年过去了,似乎仍在眼前。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教育是什么?学校是什么?很难说得明白。我又想到杨绛,她说“振华有一股味儿,这股味儿影响了我一生”,杨绛所说的味儿是什么呢?就是她那天与我们叙述的往事?以及往事中蕴含的意义?此刻,我坐在校园里的一角,那是桂花园。桂花园三面是教学楼,坐在其中似乎坐在密林里,枝叶繁茂。寂静,除了寂静还是寂静。振华的味儿,今天还有吗?每一个师生身上是不是还带着这股味儿?一只鸟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飞出的是一条美丽的弧线。一只鸟呼唤另一只鸟,呼唤声与应答声是那么不一样,一个婉转,一个清脆。我坐在石条长凳上,内心平静,只听得叫鸟鸣。平时似乎从没有听见这么多鸟,叫出这么复杂、这么多样的声音,那不是天籁吗?
刚刚举行完毕2014届毕业生纪念物正式启用仪式,这是一个传统,108年的办学延续至今。最西面的己巳亭,有杨绛的印记,从西向东延伸,如今东操场上建起的“张羽轩”,张羽是振华的老师,地下中共党员,一边教书,一边迎接苏州的解放。组织了许多振华学生投入了革命。杨绛一再说,振华有一股味儿,感恩、纯朴、朴素、简单、执着、本色、有情怀、有念想,代代相传,这味儿一直荡漾在校园。 (2014年6月11日)

我与杨绛合影
补充的花:
杨绛是我的前辈校友,她去世多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经常在眼前出现,是一个被大家尊敬的人。我2014年写了此文,写了杨绛与她母校的关系,写了我们与她的交往。这是一段历史,也是研究杨绛的第一手资料。今天发于此,与大家分享。
栁袁照
2022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