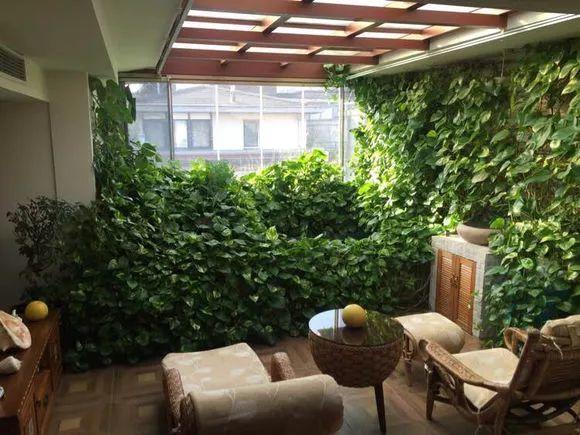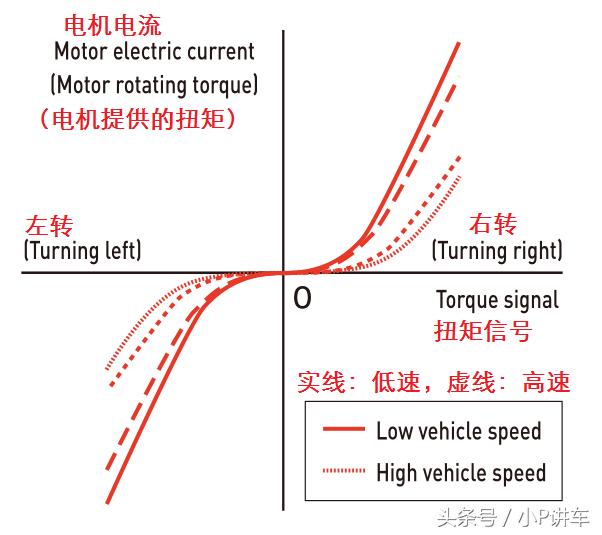清代乾隆年间,江西南昌县有个知县叫张志堂,张县令思为明晰,擅断疑难案件,在百姓中口碑很好那年有一起村民状告寺院僧人侵占岐山地的案子事情缘由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叫李四的村民,由祖上传下的山地20余亩,虽未连成一片,但东西南北四面,界限清楚近日,李四发现有寺院的僧人伪造地契,在山地里掘墓埋葬寺院里的僧人,便据状控告僧人,要求其迁葬归田张县令升堂传唤僧人询问,僧人辩解说,此块山地是雍正年间他们的师祖用现银从李四父亲手中买下的,并没有伪造田契,还当场拿出抄录的气文为证李斯不服气,便称说此乃胡说我的父亲在乾隆34年间,为此田产曾经跟村里人打过官司,前任县令经办此案当时县衙画了山地四周地界的图纸,标明是我家地产,如果师雍正年间卖给了寺院师祖,因何图上没有注明呢?僧人也申辩说,这是几十年前的买卖,我们哪里知晓当年的事由,只是按照我们保管的田契办事,哪里有错?李四和僧人坚持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张县令叫他们在歇,当场调取了库存案卷进行核查,细看下来,果然如李卷里画的田产图示里的确没有标明此田填产已经卖给寺院僧人师祖,但章县令没有据此做出僧人的契约系伪造的判断他想,或许是当年办案人疏漏了呢?张县令又命调取僧人元契约查队拿来一看,是张白条,上面倒是清晰地写明,雍正11年间,李四之父麦田给僧人师祖李四说,这张白条连雅府的印章都没有,怎可为据?章县令并没采纳,说道此时私下买卖,常有白条为据,是为了避免缴纳关税,还不能就说是伪造田契章县令接着传讯田契的代笔人,可几十年过去,代笔人早死了,传来其儿子询问,却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张县令接着询问僧人,你们在田里埋葬的是什么人?是你的师祖师父僧人答道,近日埋葬的是师叔师祖和师父多年前圆寂时都是埋在自家的墓地里张县令不解的问,为何不把你们的师祖和师父埋在这块山地里呢?僧人回答,我们以前不知师祖买了这块山地,是近日清理经卷时,无意中在经卷箱里发现了契约,刚好没几天师叔病故,就把他藏在这里了询问至此,张县令心里大致有数了民间此类买卖房产、地产的案件,首先要见证的是代笔的中间人,其次是盖了官印的契约可这个案子,原来经手的买卖人和代笔人都死了,何况买卖双方的契约只是一张白条,加之僧人称此白条是在近日无意中发现,有什么可信度呢?参与办案的师爷也劝说张县令,此案据现有的证据,只能判定僧人伪造田契,侵占李寺祖产山地,这样判决不会有什么错,可以使人信服另外,从田七的笔迹来看,是善于书写文气的人所写,此人或许就是教唆僧人,争讼者应抓来一起追究其责张县令听了师爷的话,随即升堂令僧人招供伪造田契之事,和同伙僧人喊冤拒招张县令下令掌泽长贵接着审理其他案件,审问一见就询问僧人是否招供,一连审了四起案件,僧人挨了40个嘴巴,最后实在熬不过去了,大喊这块山地推还但还是不肯认罪张县令见状,心想他是口服心不服,看来还不能就此下定论此时天色已晚,张县令叫衙役把僧人带下,明日继续审讯退堂之后,张县令就寝在床,久久不能入眠,翻来覆去想到四更天再也睡不着了,爬起来立即吩咐衙役去传唤代笔人的儿子问待代笔人的儿子来到县衙,张县令在偏房询问道,你平时以何为生?会不会写字?你的父亲在世时是做什么事情的?代笔人的儿子答道,在下务农,从未上过学,大字不识俺爹在世时当过私塾老师,经常为乡亲做代笔人张县令又问,你家里有没有你父亲?当年黛笔留下的文书字据,代笔人的儿子想了想,回答说,记得旧箱子里有一本俺爹的账簿,上面记得什么不大清楚代笔文器俺村里不少亲友家里都有张县令当即命令衙役随他回家取那账簿来,还叮嘱一定要从邻居那里借取文器,一并带来这天上午,衙役和代笔人的儿子赶回来,送上取来的带有官印的契约五件和他父亲的账簿张县令当场细细阅看,认真核对代笔人的笔迹、画押、年粉无异,而且还在账簿里发现真凭实据,里面记载着雍正11年4月17日,连收三家代笔资费,第二家就是僧人师祖的法名,并注明笔资数额和为李四父亲及僧人失足代笔买卖田产的事由事情到此,张县令总算喘了口大气,僧人没说假话,事后再审,还僧人清白张县令当庭向他赔礼道歉,李四控告不实,但念其的确不知实情,并非恶意相告,徇则一番宽大处理案子虽结,可张县令为自己自以为是,没有坐实证据而任意责罚,后悔不已,以至于他以后美林公堂看到堂上那公正联名几个大字,都内心惭愧,感到无地自容,从此以此案为鉴,更加仔细认真办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县令不同的命运?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县令不同的命运
清代乾隆年间,江西南昌县有个知县叫张志堂,张县令思为明晰,擅断疑难案件,在百姓中口碑很好。那年有一起村民状告寺院僧人侵占岐山地的案子。事情缘由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叫李四的村民,由祖上传下的山地20余亩,虽未连成一片,但东西南北四面,界限清楚。近日,李四发现有寺院的僧人伪造地契,在山地里掘墓埋葬寺院里的僧人,便据状控告僧人,要求其迁葬归田。张县令升堂传唤僧人询问,僧人辩解说,此块山地是雍正年间他们的师祖用现银从李四父亲手中买下的,并没有伪造田契,还当场拿出。抄录的气文为证。李斯不服气,便称说此乃胡说。我的父亲在乾隆34年间,为此田产曾经跟村里人打过官司,前任县令经办此案。当时县衙画了山地四周地界的图纸,标明是我家地产,如果师雍正年间卖给了寺院师祖,因何图上没有注明呢?僧人也申辩说,这是几十年前的买卖,我们哪里知晓当年的事由,只是按照我们保管的田契办事,哪里有错?李四和僧人坚持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张县令叫他们在歇,当场调取了库存案卷进行核查,细看下来,果然如李卷里画的田产图示里的确没有标明此田填产。已经卖给寺院僧人师祖,但章县令没有据此做出僧人的契约系伪造的判断。他想,或许是当年办案人疏漏了呢?张县令又命调取僧人元契约查队拿来一看,是张白条,上面倒是清晰地写明,雍正11年间,李四之父麦田给僧人师祖。李四说,这张白条连雅府的印章都没有,怎可为据?章县令并没采纳,说道此时私下买卖,常有白条为据,是为了避免缴纳关税,还不能就说是伪造田契。章县令接着传讯田契的代笔人,可几十年过去,代笔人早死了,传来其儿子询问,却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张县令接着询问僧人,你们在田里埋葬的是什么人?是你的师祖师父。僧人答道,近日埋葬的是师叔。师祖和师父多年前圆寂时都是埋在自家的墓地里。张县令不解的问,为何不把你们的师祖和师父埋在这块山地里呢?僧人回答,我们以前不知师祖买了这块山地,是近日清理经卷时,无意中在经卷箱里发现了契约,刚好没几天师叔病故,就把他藏在这里了。询问至此,张县令心里大致有数了。民间此类买卖房产、地产的案件,首先要见证的是代笔的中间人,其次是盖了官印的契约。可这个案子,原来经手的买卖人和代笔人都死了,何况买卖双方的契约只是一张白条,加之僧人称此白条是在近日。无意中发现,有什么可信度呢?参与办案的师爷也劝说张县令,此案据现有的证据,只能判定僧人伪造田契,侵占李寺祖产山地,这样判决不会有什么错,可以使人信服。另外,从田七的笔迹来看,是善于书写文气的人所写,此人或许就是教唆僧人,争讼者应抓来一起追究其责。张县令听了师爷的话,随即升堂令僧人招供伪造田契之事,和同伙僧人喊冤拒招。张县令下令掌泽长贵接着审理其他案件,审问一见就询问僧人是否招供,一连审了四起案件,僧人挨了40个嘴巴,最后实在熬不过去了,大喊这块山地推还。但还是不肯认罪。张县令见状,心想他是口服心不服,看来还不能就此下定论。此时天色已晚,张县令叫衙役把僧人带下,明日继续审讯。退堂之后,张县令就寝在床,久久不能入眠,翻来覆去想到四更天再也睡不着了,爬起来立即吩咐衙役去传唤代笔人的儿子问。待代笔人的儿子来到县衙,张县令在偏房询问道,你平时以何为生?会不会写字?你的父亲在世时是做什么事情的?代笔人的儿子答道,在下务农,从未上过学,大字不识。俺爹在世时当过私塾老师,经常为乡亲做代笔人。张县令又问,你家里有没有你父亲?当年黛笔留下的文书字据,代笔人的儿子想了想,回答说,记得旧箱子里有一本俺爹的账簿,上面记得什么不大清楚。代笔文器俺村里不少亲友家里都有。张县令当即命令衙役随他回家取那账簿来,还叮嘱一定要从邻居那里借取文器,一并带来。这天上午,衙役和代笔人的儿子赶回来,送上取来的带有官印的契约五件和他父亲的账簿。张县令当场细细阅看,认真核对代笔人的笔迹、画押、年粉无异,而且还在账簿里发现真凭实据,里面记载着雍正11年4月17日,连收三家代笔资费,第二家就是僧人师祖的法名,并注明笔资数额和为李四父亲。及僧人失足代笔买卖田产的事由。事情到此,张县令总算喘了口大气,僧人没说假话,事后再审,还僧人清白。张县令当庭向他赔礼道歉,李四控告不实,但念其的确不知实情,并非恶意相告,徇则一番宽大处理。案子虽结,可张县令为自己自以为是,没有坐实证据而任意责罚,后悔不已,以至于他以后美林公堂看到堂上那公正联名几个大字,都内心惭愧,感到无地自容,从此以此案为鉴,更加仔细认真办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