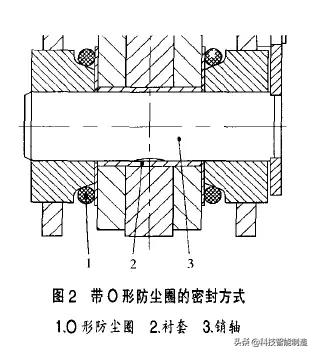▲河南宜阳籍画家刘大洪 国画作品《说书人》
文 陈曦
贺治财贺治财命里就是说书的人,因为他干什么都挣不了钱,只有说书还能过日子。他二十来岁追随陕北说书大师张俊功学说书,出师以后并不是就一门心思搞了“艺术”,社会上的杂事他都搞过,骑摩托车拉过人,开四轮拖拉机拉过货,甚至也干过非法的勾当,每一次行不通了他就只好回头说书。他曾经爱好赌博,不仅没有获得经济效益,反而赔了十几万,搞得几乎倾家荡产,从此戒了赌,摸牌的一双手位移到了三弦上面:“弹起三弦定准个音,众位明公请坐稳,今天我不把别的论,单说说前朝古代人。”说书虽然不能说他不爱好,但是几乎也是生活所逼。从来没有听到说书能把人说富的,最多能达到温饱和小康,贺治财要靠说书是“治”不了“财”的。
陕北说书源于乞讨,是一种乞讨的艺术,或者是艺术性的乞讨,而且是盲人的专利,虽然后来升格为老百姓的艺术,但毕竟还是苦命人的求生之道。到现在,说书的被称为书匠已经是高抬,到哪里说罢书,拿了工钱走人,不会被奉为上宾,更不会有追星族日夜等着签名。
但是随着陕北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政府需要古老文化装点、扮美的时候,书匠们的地位似乎也就提高一些了。于是,贺治财在正月间,背着三弦,带着徒弟就上了榆林城老街的鼓楼来说书,这就接近了明星们的出场表演了。扩音设备早有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准备好了,匠人们定定音,调调弦就能开言。实际上贺治财在榆林的星明楼上已经火了两年了,城里人都知道,正月间星明楼上有个横山的艺人说得一本好书呢!陕北说书起源于横山,横山艺人的腔调似乎更能代表陕北,更有独特魅力。老贺说书尤其底气十足,最适合人稠广众的场合。榆林老街上的阁楼众多,每个阁楼都有一班艺人在演出,春节演出的组织机构已经觉出了贫富不均,他们不希望火暴的过于火暴,冷淡的过于冷淡,他们要老贺为一贯冷淡的鼓楼加加温。贺治财悉听尊便,他知道人是认人的,不是认楼的。市民还是买他这张瘦干老脸的面子,鼓楼附近的交通于是出现了拥堵,老街被听书的人塞得满满当当。两辆小车开到人群中间,实在无法前行了,司机索性停下车专心听一段。
老贺这天带了两个徒弟,一个是刘建军,一个是小女孩李慧,刘建军为老贺弹三弦,李慧为老贺弹电子琴。这一天师徒几人居然把闹秧歌的衣服热热闹闹穿了一身,增些节日的喜庆,也增些表演的氛围。现在的艺人们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再不是那烂袄子一裹,老羊皮一披的样子。老贺一手握两片木板,学名叫做“四片瓦”,碰得啪啪响,左胳膊一落就是两声,右胳膊一起就是三声,左右手上下一磕又是一声,“四片瓦”经老贺把玩竟然让人听得出神,竟然能和他模拟出的老音嫩调胶合得妥贴。站在话筒跟前老贺说得眉飞色舞,说得手舞足蹈,他一开口,好像满脸就是一张口,又瘦又干的脸几乎不存在了。
鼓楼下听书的男女老幼们或者伸长了脖子仰望,或者低头细听细品,或者站直了身子叉了腰,或者坐一个小板凳翘起二郎腿,听累的干脆圪蹴在地上手托腮帮……有的是丈夫带着老婆听,有的是女儿带着老娘听,有的是一家老小一起听。男人们听书各就各位,都保持一定距离,女人们听书是一个揽着一个的胳膊,一个攀着一个的脖子。人们听得一会皱了眉,一会呲牙笑。等到书板一落,老贺说一声“说到搭价算完成”,人们还等着再听,老贺却说马上要到横山去赶另外一个场子,和大家后会有期,众人才满不情愿地缓缓散了。
52岁的老贺不仅学了张派的说腔,在创新意识上也秉承了他师父的传统。传统的陕北说书不过是一个人手拿三弦或琵琶边弹边说,没有其他什么伴奏,也没有什么表演,到了张俊功那里,书匠有时候就和三弦分离了,而且又增加了其他乐器,增加了表演性的身形步态。那时候老贺除了给师傅弹三弦,还拉二胡,吹笛子,敲铜锣,击碰铃,打梆子,一个人使唤五六种乐器。老贺说,他是奏打击乐器出身,他似乎在标榜自己打击乐器比其它乐器更在行。老贺出师以后,居然把电子琴也加入到说书乐器中来。爱赶新潮的他坦白说,到现在他都一直在学习,他害怕哪一天被时代淘汰了,那时候最后一个饭碗就要被砸掉了。老贺的认真是一般艺人比不了的,他要做到的是从头到尾不管多长的书,一个错误都不出,就像一个泥匠砌一堵高墙,一块砖都不能砌歪。他把民歌加入说书中间,常常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他把戏剧表演的动作加入说书中来,扮演不同人物的音容态度,无不惟妙惟肖。老贺从事过各种职业,对他来说,虽然有点不务正业,但是也便于使说书更加贴近普通老百姓。现在陕北的说书艺人约有近300人,老贺在这个圈子里是有声望的。一次说书比赛,老贺的一个徒弟得了十佳艺人奖,另一个徒弟得了新人奖,老贺却什么也不是,艺人们为此闹乱了会场炒乱了营——老贺不进“十佳”竟然犯了众怒。老贺一直保持着自信,并不以获奖为念,他认为说得好不好,不在于你能不能进“十佳”,关键是要人们喜欢。
当那些历史演义、民间传说、才子佳人、绿林豪杰、神话故事的老书现在已经快要没人买单的时候,老贺只好以新书迎合大众,以前烂熟于胸的老书现在只能说全《白玉楼挂画》、《奇冤记》、《血墨记》、《劈山救母》等少数几个。人们的审美品味只在于热闹,甚至在于下流,这也是让老贺烦恼的事情。老贺虽然半生混迹社会,但毕竟不同有的艺人,口无遮拦什么都敢说,传统的某种艺术尺度还在规范着他。
老贺到横山说书时换了一身行头,那是一身传统的立领黑色疙瘩襻布纽扣衫子,显得严谨整肃,人更显得清癯消瘦。横山的场子有当地政府官员在,老贺的书词就变成了自编的“主旋律”书词,他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书,这一点早就拿捏得恰到好处了。这种功夫都是生活逼出来的。老贺本人并不善于与人周旋,同行们觉得他有点不合群,每次说罢书,别人都是吆五喝六地喝酒打牌,他却一个人远避一边一根一根地抽他的低挡香烟,抽得瞌睡了一个人兀自睡去了。他最怕和领导一起吃饭,到了饭口他就说已经吃过了,却悄悄跑到街上喝一碗豆钱钱饭或者吃一老碗面。在戏里找角色,在生活中也找角色,这时候老贺的羞赧、自卑和身份认同的焦虑与一个普通农民没有区别。
老贺的徒弟说起来不少,现带的刘建军是个半盲人,腔口不算高妙,乐器不算精深,但是靠着苦练说一个月书也可以不打重板。他的手机是盲人专用手机,除过打电话,还可以查万年历用来批八字算命,最重要的是手机能录大量说书,既有师傅贺治财的,也有其他艺人们的。他白天黑夜在听,在学,平时说话都要带几句自编的书词,近乎走火入魔。刘建军的开场白一般是:“手弹三弦啪啦啦响,我盲人说书没有文章,说得不好大家原谅,歪歪好好就说一场。”
另一个徒弟是小女孩李慧,只有十九岁,就是在说书大赛中得新人奖的。她入道不久,耳濡目染也会说几种小书,拿手的是劝世书《大小老婆》,说的是大小老婆争风吃醋抢老公的事情:“大婆说,今天你要跟我睡,我给你吃一个鸡大腿,二婆说,今天你要陪了我,我给你买一个肉夹馍。”说到这里,你看着她促狭的表情,保准会开心一笑。说书人中女性奇缺,最早的女艺人是韩起祥在延安开始培养的,而张俊功的女弟子则首次到山野庙会说书。女艺人能否大有作为不是师傅们说了算,恐怕最终取决于时代的风尚了。
鲁锋
陕北说书艺人当中,书词词工最硬,古书记得最多的人现在当推盲人鲁锋。鲁锋,横山高镇人,自从四岁上发了一次高烧,眼睛就坏了,只能有微弱的光感,勉强看到物体的大概轮廓。二十岁的时候,鲁锋经名师指点学习说书,不久师从横山说书兼算命大师王学师,开始了说书兼算命的生涯。这是陕北盲人的一个普遍出路。
我见到鲁锋是在横山政府宾馆,一起的朋友打通了鲁锋的手机,约他来宾馆说书,我吃了一惊,一个盲人,你不去接他,他怎么能摸得到宾馆?朋友说,他不是完全失明,况且大白天光线好,路又熟,没有问题。果然不久鲁锋就到了,他和我想象的盲人截然不同,腰并不深弯,手并不拄拐杖,身形甚至颇有挺拔之势。鲁锋长脸长鼻子,皱纹除了在眼角活动,还占据了鼻子的上半部分。他出生于1962年,算不上老,但皱纹使他的年龄增大了不少,有一个比他大得多的导演居然把他称为老人家。他头上戴着假发,只是假发显得凌乱了些,而且身上的人造革皮衣很有些陈旧了,也许是他看不出衣服的陈旧,也许是日子过得有些紧巴。他将身上背着的三弦放下和大家攀谈起来,说着就开始咳嗽,我将水杯递到他跟前,他在空中抓了两下都没有抓着。他笑着说,家里的炕洞上不去烟,收拾炕洞被烟呛了嗓子。我有点过意不去,他说不影响说书。虽然嗓子被烟呛了,别人递烟他照抽不误。水喝好了,烟抽好了,鲁锋拉开口袋取出三弦,要试一试音,不料大弦不知何时已经断掉了。他大概是很长时间没有说书了。好在宾馆有其他艺人的三弦,他不需要回家去取。鲁锋调好了弦音,摸索着将书板绑在左腿膝下。这个熟练的动作在他一生中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按照老规矩,他右手应该绑一个麻喳喳用以和音的,但他没有带,后来不少人发现麻喳喳的使用对于录音很有影响,也就不多用了。
“林冲雪夜上梁山——”弦音落定,一句出口,鲁锋的唱词那样的苍凉、高远、厚重、古朴,长音拖得那样恰到好处,回转得又那样自然天成,那是漫长的苦寒岁月练就的腔口。我马上对于鲁锋刮目相看了。这是他打的一个小段:“孙二娘十字坡开酒店,诸孔明败在了五丈原……孙悟空三盗芭蕉扇,关老爷月下斩貂蝉。”这是陕北说书的意识流,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就这样随便地摘取,自由地拼凑,说不准某一句会打动你,某一句会引发你的联想。小段的精彩在于它的高度概括和凝练。鲁锋对于贪色的劝世书让你不得不频频回味:“白的是露水夫妻不久长,尽都是沉溺苦海水茫茫。休将那花容月貌当奇遇,交杯酒点点吃的迷魂汤。桃花面就是牛头和马面,杏子眼瞅得骨肉两分张。樱桃口能吞高楼与大厦,糯米牙嚼了田土又嚼房。杨柳腰比作绑人桩橛木,小金莲勾魂取魄见阎王……”这个十字腔的经典小段并非鲁锋专利,但是出自他的口,就是一种悲凉的力量,能把虚妄说透,能让人想到《阿弥陀经》的某些段落。
鲁锋是一个记忆的巨人,虽也略通盲文,但是他的老书全部得自师傅口授,无论是《杨家将》、《英雄小八义》,还是《五女兴唐传》、《金镯玉环记》,无论是《罗通扫北》、《绿牡丹》、《粉妆楼》,还是《薛仁贵征东》、《破孟州》、《汗巾记》,都完全地保留在记忆深处,就像一坛坛老酒深藏在鲜为人知的地窖里。一种功能消失,别的功能就要增强,盲人的听觉和记忆力一般能够优越于常人,大概是上帝给与的特殊眷顾吧。我问鲁锋,最长的书能说多久,他说,能说七八天之久。这让我想到了新疆木卡姆,想到了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听到这么长的书,真正的大气磅礴,真正的回肠荡气大约都在长书中间吧。
在我们谈天说地欢喜交往的几天中,我发现鲁锋的口袋里装着一支录音笔,据说能录90多小时,有时候他说书前拿出来放在了录音状态。原来这是延安大学陕北民歌说书研究中心给他留下的,他们现在正在编一本说书大全的书,大部分的艺人们都找到了,也都录了音,其中鲁锋的说书数量最多,大大小小约有200多种,而且这还只是一部分。鲁锋在家中没事的时候一个人自言自语,自弹自唱,把自己的“库存”一点一点取出来。这种情况除了练习以外,对于一个艺人来说实在是太寂寞了。因为科研经费有限,鲁锋说书一个小时只能挣到20元钱,但是他没有嫌钱少,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对于陕北的意义。我相信,有些书如果鲁锋不说出来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人能说出来了,那个巨大的宝库终究要失去它对后世的作用。
鲁锋的才华和他的落魄境遇是不相协调的,他文辞典雅的古书只有少数老年人和文化人愿意听,能听懂,古书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已经产生了距离,这种矛盾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凸显了,现在的情形可谓尤甚于前。于是,鲁锋面临的是无人邀请的尴尬境地,他被这个喧嚣的时代悬置了起来。偶尔有少量的活路,他也挣不了多少钱,一个三天的庙会他说五场书能挣300元左右,但是这样的好事一年中并不多。以前横山县有一个政府组织的曲艺队,里面有一些盲人书匠,由政府指定他们到某些地方说书挣钱。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职能变了,少了指令和计划,由盲人自己找钱挣去,从此以后盲人的生计成了问题。激烈竞争的时代打破了古老的规矩,明眼人说书者更受欢迎,他们形象好,善表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抢了盲艺人的饭碗。我突然想到,鲁锋的戴假发大概是为了在舞台上表现一种好的形象吧。听说盲人们为生计还闹过几次事,但是终究不了了之。鲁锋没有闹事,他找到一个擅长物理机械的本家兄长,央求他给自己教授了修理缝纫机的方法,从此以后养家糊口主要靠修缝纫机。一个盲人修理缝纫机有点天方夜谭,我问鲁锋怎么修,他说主要靠摸,当然要掌握机械原理,否则修不好。我觉得他有点像古代的庖丁,庖丁解牛熟练到一定的时候,闭着眼睛也能操作。但是庖丁毕竟是明眼人,所以他比庖丁还强,他等于是从一开始就闭着眼的。鲁锋在横山的乡下几乎跑遍了,甚至还跑到周围的县去修理,客户们说他比明眼人还修得好。但是修一台缝纫机也不过挣一二十元钱,抛过路费就剩不了几个钱,所以他要等某个村子或一条交通线路上的缝纫机坏了几台,才去修理。我担心有些人急着要用,不会硬等他的到来,除非是出于一种同情。一个更坏的情况是,现在即便是偏远农村,缝纫机也越来越少了,鲁锋的收入当然要每况愈下,成衣的世界,发展的时代又要将鲁锋抛却了。终究是痛苦的,难道要让鲁锋学电脑学开车去不成?聪明、好学、肯吃苦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用的。鲁锋另一个算命的本事偶尔也能派上用场,他说几年前延安有一个人专门请他去算命,他去了以后管吃管住,招待甚周。说到这里他有微微的满足和得意。我请他替我打上一卦,他算得居然八九不离十,看来真的有点道行。
在横山我和鲁锋见到了另一个年轻说书艺人白云飞,他说自己出场说书一天要挣3000元,也许他真的挣了钱,居然开了一辆破旧的小车,艺人中的暴发户模样。他为了联系说书的事宜,敢于和不同部门的领导联系、交往,落实说书经费。他说的书可谓行业书,交警队要宣传交通法规,他能说,移动公司要为手机做广告,他能说,政府要反邪教,他能说,公安局要宣传戒毒,他也能说。与其说他是一个说书艺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政策宣传员、产品广告员。我对白云飞说,你路子广,挣钱多,多带一带鲁锋,别一个人挣钱。他笑而不答。我知道他嫌鲁锋形象不适合搞宣传,做广告。但是鲁锋根本没有接我的话茬,更别说央求,他是一个乐天派,更是一个自由派,对于和白云飞的合作似乎并不感兴趣,没有书说他宁肯修缝纫机。
不管怎么说,鲁锋的说书总还是有追捧者。某一次因为一个酒后的误会鲁锋被关进看守所,而且遭到了其他人犯的欺凌。正巧所长听过鲁锋的说书,竟给他开了单间,格外宽待。从此打他的人犯把他奉为上宾,每天要敬奉他一盒烟抽。尊重说书人就是在尊重一种文化,如果陕北多一些所长这样的人,陕北说书就能传下去,就不至于到了濒临抢救的边缘。
古圣先贤传经布道,说书艺人讲说传奇,谁会真正的影响世人?在蛮荒的陕北,艺人的传播之功、教化之力恐怕无人可以取代。听了鲁锋的书,尤其能感知到陕北民间各种观念中的精彩之处。它可以将人带到辽远的过去,接起和传统相连的某条线索,让人体味一个民族的生存履历。这样的人的存在是陕北的福气,这个社会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边缘化呢?
孙金福在天荒地贫的陕北,苦命的说书人一般没有多少文化,有文化就会求取功名,岂能“沦落”为社会底层的说书人?但是这些书匠中有没有文化人?当然有,孙金福就是一个。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孙金福在他所生活的横山县的穷乡僻壤中是一个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乡村的高中生已经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他天资聪颖,如果能上大学,人生轨迹就会彻底改变了。但是天不遂人愿,孙金福早在七岁的时候,他的当矿工的父亲因为煤矿的一次透水事故而蒙难。他的母亲养活他们兄弟姐妹五个人,孙金福是最小的一个,能够将他供到高中毕业,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母亲来说已经是竭尽全力了。
说书这条路是孙金福自己选择的,因为他什么活都干不了,也吃不下苦,用陕北话说就是没有“苦水”。当然,孙金福本来就喜欢说书,他从小听了无数的书,自己心里也记下了不少。说来也巧,横山县当时有个曲艺队,队长就是孙金福的本家孙旺生,孙旺生是陕北说书一代尊师韩起祥的小舅子,也是韩的大弟子和秘书。于是孙金福就投奔到孙旺生门下当了弟子。孙金福天生是一块说书的料,任什么书,师傅说一遍他就能记下来。各种乐器也是一样,一教就会,丝毫不费力气。学到第三个月,孙金福的技艺已经成熟了,大场子都能给师傅撑下来。
但是独特天赋也好,艺术才情也罢,都没有转化为生活的福祉。按规矩,当学徒不仅不能挣钱,还要给师傅交学费,这对孙金福这个贫寒的家庭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刚开始到乡下说书还好一些,都是包吃包住的,至少能混个肚饱。但是后来到城里说书,往往是食宿自理,只给钱,而钱都在师傅的口袋里,一个子儿都到不了他手中。没有钱,没有住宿的条件都无所谓,关键是没饭吃,师傅又不给赏饭,他实在饿得不行,只得回家。
回到家,干什么?孙金福没有想好,学好的技艺丢掉又心有不甘。就在这时他碰到了说书大师张俊功的弟子贺治财。贺治财已经出师,在单独说书。他们两人本是同乡,又是同校的校友,话语分外投机,于是决定一块说书,挣来的钱贺治财拿大头,孙金福拿小头。从此后,孙金福终于可以靠着说书养活自己了。那个时候,好多人其实是喜欢听古书的,但是孙金福从师傅那里学的全是新书,这个时候他就翻阅大量古书的说本,然后请教贺治财,看他是怎么将一本本古书说下来的。贺治财比孙金福大五六岁,这种亦师亦友的交往使孙金福受益匪浅。到后来,一个完全陌生的古书的内容,只要贺治财讲述十几分钟,孙金福就能配合着他在台上完整地说下来。孙金福这种超常的天赋让贺治财大为吃惊。而贺治财深厚的功底和良好的素养也让孙金福深感钦佩,直到几十年后孙金福还是逢人就说,贺治财是陕北说书人中书说得最好的。
一般人学知识都是在学校里完成的,说书人的知识是通过说万卷书、走万里路而获得的。孙金福结合两方面的优势,加上勤勉好学、博闻强记,对历史地理、阴阳五行、民间杂学都烂熟于心。逐渐地他和其他艺人有了区别,他成为说本的研究者,书词的诠释者,也成为说书艺术的评判者。如果不是后来生活的变故,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大师级的人物。
1986年,孙金福24岁,命中注定这一年他要“动婚”了,他借了一笔钱,可心可意找了一个米脂婆姨。老孙两年生了两个男孩,喜和愁同时降临。靠着说书眼看着一家人要跟他饿肚子了,没有办法,只有改行。他和老婆摆地摊卖小吃,卖的是羊杂碎和碗托。虽然挣不了多少钱,但是每天都有收入,生活就可以稳定下来。然而,老孙并不着意于生活的稳定,他要赚一笔大钱。那时候陕北各地贩卖羊绒成了一股风气,老孙找到了一个做羊绒生意的朋友,借了钱,贷了款,入了一股。不料,因为羊绒中间掺沙子作假,他的朋友坐了牢,他跟着一下子赔了个盆空碗空。老孙连结婚时候借的钱都没有还完,又欠下一屁股债,日子真的就要过不下去了。这时候他听说神府煤田大开发,淘金的人都往那里涌,于是举家迁到神木大柳塔卖小吃。没想到在那里一扎根就是20年。
那时候老孙夫妇拼命赚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快将欠债还清。所以无论他们赚多少钱,生活都是一贫如洗。日子难过的时候,一天一家人只买过一颗土豆;过八月十五,只买一个月饼给两个孩子吃;过年时,身上只有两块钱,不敢家里待,害怕朋友上门无法招待人家;好久吃不上白面馍,有一天他们用两层的蒸锅蒸了十三个馒头,上面一层七个,下面一层六个,等到蒸好了,老孙夫妇连馒头长什么样都没看到,就叫两个孩子吃光了,老大吃了上面的七个,老二吃了下面的六个。那时候给客人做的饭如果坏了,他们不舍得扔掉,在锅台上烤干,孩子们饿了,用开水泡开继续吃。这个苦日子全靠老孙的老婆撑着,家里所有的重活累活都由老婆承包了,老孙只是给客人卖个饭,收个钱。家里,老婆除了要喂饱他们几个人,还要喂饱三口猪,她每天得到各个饭馆担泔水喂猪,有时候,泔水中有好吃的,老婆舍不得喂猪,自己就捞出来吃了。
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孙金福夫妇就将欠账全部还清。之后,他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段卖小吃,生意越来越火,短短几年时间不仅买了住宅,还买了门面房。有了自己的门面房,老孙就挂出了一个招牌:书匠饭馆。这时候,老孙给贺治财打了一个电话,叫老贺来一趟。老贺提个三弦来了,以为是有书说。老孙瞒着老婆悄悄给老贺一万块钱说,做个买卖吧!他知道老贺日子难过,老贺书说得再好,五个孩子靠他说书要吃西北风。老孙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当年和老贺合作,老贺没有亏待他,他就一辈子念着老贺的好。老贺没说什么,知道这是兄弟的一份心意,那时候的一万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老贺用这些钱买了一个机动三轮车去延安贩菜,可惜他财运不好,居然赔了钱,后来只好继续说书。
老孙的书匠饭馆不算大,但是名声不小,它成为陕北说书人的集散地。南来北往的艺人们到老孙的饭馆,老孙吃住全包。用贺治财的话说,老孙这个人爱穷人!当然,老孙其实也还爱着说书,说书、听书成了老孙补养精神的特殊方式。有时候他撇下饭馆,摇身一变,又成了说书人,他酣畅淋漓地和各路书匠们一起说几天书,过一过瘾,好像唯有如此,日子才过得踏实。参与说书活动对老孙来说,早已不是为了赚钱,好多时候他都是贴着钱。穷朋友交往得多了,没有不贴钱的。有一次横山盲艺人鲁锋找到老孙要借两万块钱,他说没这个钱,儿子娶媳妇娶不到家。老孙二话没说答应了他。老孙多年接济过不少日子窘迫的艺人,他的慷慨众所周知。
几年前,师傅孙旺生找到了老孙,这让老孙吃了一惊。原来说书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几个国家组成的采风团到榆林来调查陕北说书,找了横山的好多说书人座谈前朝古代的事情,那些艺人们都是一问三不知。他们又找到孙旺生,想了解一二,不料孙旺生懂得也多是新书,对于古书并没什么了解。于是年过七十的孙旺生带着考察的专家们找到了徒弟孙金福。青出于蓝的孙金福肚子里的确有货,他将说书的文化讲得头头是道,引起了专家们的兴趣。政府的人要求孙金福在榆林市表演说书,孙金福硬是要拉上贺治财,众人不了解老贺,不同意。老孙说,没有老贺说不成。于是老孙老贺再次合作,到了市上,几场书下来就说红了。政府官员感了兴趣,每年正月搞文化活动都要叫他们去捧场。
延安大学要搞一本说书的集成,他们搜集了不少资料,因为错误甚多,典故庞杂,书词难辨,就找到孙金福帮忙,把他聘为特约顾问。从此老孙牛气起来,穿一件黑色风衣,俨然一个说书的学着。他的手机铃声就是一段说书,走在哪里别人一听到三弦声音响起,就知道老孙来了。老孙来了,少不了就要聊聊说书的事情。现在,他进出大学校园讲课说书,参加各种说书比赛和学术会议,甚至跑到广州、西安去交流民间曲艺。老孙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他认为在当代真正能称得上陕北说书大师的有三个人,他们是韩起祥、张俊功和王学师,碰巧的是,他们都是横山人。老孙为此感到无比骄傲。老孙步着大师们的足迹,总结出了说书基本要领、说书艺术的评判标准等等,他正在由一个说书艺人转变为说书评论家。而且他还有着更大的野心,他要对说书进行巨大的改革,他想把曲艺形式改为戏剧形式,并将其称为说书剧。为此他搞策划,拿方案,四处游说政府官员,但是至今没有寻找到真正的支持。
老孙一心想把陕北说书搞成一个像陕北民歌一样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产业,但是以他的一己之力看来难以成就大业。虽然如此,他并没有气馁,一条路不通他走另一条。他利用广泛的人脉资源,搜罗了一百多本从民国到明代的说书的说本,这些说本中仅小段就有一千多个。一个台湾商人看上了他是书本,想出20万将它们全部买断,精明的老孙说,他才不卖呢!老孙现在的饭馆每天收入上千元,他不缺钱。实际上,陕北民间文化需要一大批像孙金福这样的搜集整理者和并非学院式的评判者。至少,说书有了他这样的人,应该是这门艺术的福气。
▎陈曦,1970年生,陕西榆林人,现居西安。主要作品有随笔集《着装的自由》、电影《盗剑72小时》、电视剧《海棠》等。
关注陕北民歌微信公众号(sbmg66)
看更多【陕北民歌-往期内容】
随时免费看更新,请点击下方“订阅”,订阅↓↓↓陕北民歌头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