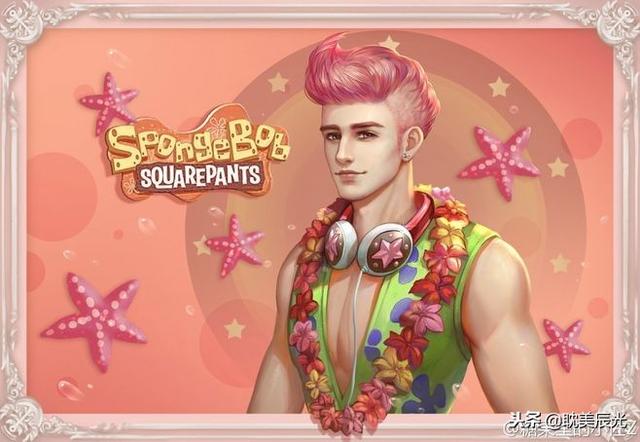|
|
|
罕见病患者小杰在家中坐着,一旁是他以前会骑的自行车。 南方日报记者 张迪 见习记者 张宇晴 摄 |
|
|
|
小杰一家人在惠州的家中,门口的对联寄托着他们的期望。 南方日报记者 张迪 见习记者 张宇晴 摄 |
|
|
|
可爱的黏宝宝 等待的一家人 |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珠江岸边的草坪上,一对父子席地对坐,歌声和欢笑声飘向远方。走近细看,才能注意到孩子浓眉阔嘴,面目异于常人,歌词也唱得断断续续。
这是陈林和他的罕见病儿子小杰。4岁确诊、6岁远赴异国参加临床试药,如今小杰已经9岁。他患的罕见病,被称作“黏多糖贮积症”,已列入国家《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体内积聚的“糖”让小杰身体每况愈下,智商退化到了婴儿时期。“孩子生病后,更加黏我了,最喜欢抱抱和亲亲,坐在我腿上玩,真正成了一个黏宝宝。”
罕见病的保障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4月1日实施的《佛山市医疗救助办法》将国家罕见病目录中的罕见病纳入医疗救助范围。12月1日上线的广州“穗岁康”商业补充健康保险,没有将罕见病及其治疗药物拒之门外。
陈林并没有放弃求医问药之路。他希望,可以陪着小杰等来那一天,“一家人始终黏在一起”。
●南方日报记者 严慧芳 统筹:羊建溶
迟到
4年才最终确诊
2011年2月,小杰出生在惠州博罗县一个小山村。除了后背上有大块青色的“蒙古斑”,这个小男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刚出生的时候很可爱,睫毛长长,耳垂大大,大家都说他很有福气。”27岁的陈林和妻子没有料到,生活跟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2个月时,小杰被发现有腹股沟疝气,医生建议大一些再处理。“当时根本没有联想到有什么大病。”陈林告诉记者,1岁多学走路时,小杰总是踮着脚走,手指也有点弯曲,但这些症状也没有引起重视,以为做个疝气手术或者腱鞘手术就能解决。
当时,最困扰一家人的是小杰频繁发烧。“一个月少则两三次,多则四五次,一发烧就到39摄氏度。家人带着小杰四处求医,被怀疑过结核病、寄生虫病、血液病等,又都一一排除。”陈林回忆说。
3岁后的小杰,已经开始一点点显露出黏多糖贮积症Ⅱ型的典型特征:爪形手、脾脏肿大……更令陈林难受的是,逐渐长大的小杰,智力却在一点点退化,像一两岁的孩子,“幼儿园学的儿歌古诗,现在已经不太记得了。有时候还会把我叫成‘叔叔’。”
直到2014年10月,在广州市妇儿医疗中心,小杰的“怪病”才找到了原因——黏多糖贮积症II型(MPS II)。
根据缺乏酶的不同,MPS分为7种分型。小杰所患的黏多糖贮积症Ⅱ型,因为身体内缺乏“艾杜糖-2-硫酸酯酶(IDS)”,致使糖胺聚糖(GAGs)在体内积聚,疾病累及多器官系统,出现面容粗陋、下呼吸道感染、爪形手、关节僵硬、听力受损、肝脾肿大等多系统症状。病情严重的患者会在10—20岁死亡。因为疾病知晓度差,患者平均确诊时间在4.8年。
“当时只觉得天旋地转,大脑一片空白,怎么出的医院都不记得了。”陈林回到家,拼命搜索网上关于这种病的信息,“越查越怕。”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遗传与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丽,是帮小杰确诊病情的医生,也是国家卫健委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员会的成员。10多年来,她所在的医院,已经陆续诊断过200多例黏多糖贮积症病例。
2020年发布的《中国黏多糖贮积症患者生存报告》显示,经过确诊后,目前国内患者组织正式注册的患者为378名,其中儿童患者约占84%。
“罕见病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诊断。很多病人都是辗转了很多医院才能最后确诊。”说起小杰,刘丽很惋惜,“如果2岁前能获得诊断及时干预治疗,可能不会引起神经系统的损伤。”
无药
迫不得已出国试药
罕见病面临的另外一大挑战,是无药可用。有统计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只有不到5%的罕见病能得到有效的药物治疗。
2017年,小杰在患者组织的帮助下通过评估,得到去韩国接受海外临床试药的宝贵机会。尽管当时家里因为亲人患重病,经济负担沉重,陈林还是决定咬牙去韩国尝试一下。
在韩国试药的这一年,给父子俩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用上药后,小杰的身体有了明显的改善,肝脾缩小了三分之一,体能也变好了,每天可以跟着我走一万步。”
在韩国时,父子俩形影不离,一起走了很多路,还结识了很多患者朋友。陈林说,20个试药的患者家庭,没有歧视,像一家人一样,每周用一次药后,有很多时间可以陪着孩子。
但因为家庭原因,试药一年后,陈林和小杰不得不提前回国。停药后的小杰,“体力下降,经常咳痰,睡眠也不太好,情绪变得更加暴躁。”
小杰试的“特效药”是一种酶替代疗法。这种黏多糖贮积症II型的特异性治疗药物,在今年9月份通过了国家药监局审批在国内上市。这让陈林看到了希望。
但罕见病面临的第三大挑战,仍然将小杰拦在门外。
“罕见病治疗用药存在2种情况,一类是药价便宜但生产有限,病人买药非常困难,另一类为高价值药物,动辄百万,一般老百姓难以承受。”刘丽说,小杰的病情,如果使用新上市的酶替代疗法药物,每年的费用上百万元,而且需要终身用药。
期盼
保障完善能重新用药
陈林没有放弃。
一方面,他在不断给医保等相关部门写信,祈盼药物及保障政策能早日在广东尤其是老家惠州落地。另一方面,他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陪着孩子。“我们患者群的家长经常说,孩子生命有限,我们就毫无保留地给予,就当把孩子将来上学的费用、结婚的费用提前消费了。”
原本在东莞打工的陈林,回到老乡一家餐馆帮厨,每天下了班就陪着孩子,教他复习曾经学过的儿歌、古诗,带着他出门逛逛商场。“医生说,孩子将来可能会走不了路,需要坐轮椅,也可能心脏会有问题、视力会有问题,那我们就趁现在带着他多出去走走。”
“孩子生病后,更加黏我了,最喜欢抱抱和亲亲,坐在我腿上玩,真正成了一个‘黏宝宝’。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做父母的应该都会很享受孩子黏自己。”陈林说,现在只希望小杰当一个长不大的宝宝,一家人就是要黏在一起。
爱踢球的陈林,偶尔也会带小杰重温小时候的时光。小杰四五岁时,父子俩还能在村口小广场踢上一两个小时,夕阳下练习着传球、带球,是陈林陪伴儿子成长中最美好的回忆。不过如今9岁的小杰,越来越“安静”,对滚到面前的足球,只能懵懂地踢上一脚,不知道该踢往什么方向。
“罕见病可能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要救孩子,家长必须走出来,让社会认识罕见病。”陈林告诉记者,希望有更多人了解罕见病,也希望保障能完善,小杰可以早一点重新用上药物,“多陪他一天,就幸福一天。”
■链接
罕见病保障日趋完善
“缺医少药保障不足。”刘丽将罕见病现状总结为8个字。
罕见病又被称为“孤儿病”,世界卫生组织将罕见病定义为患病人数占总人口0.065%到0.1%之间的疾病或病变。目前国际确认的罕见病约有7000种。
这一群体的总数并不“罕见”。2020年中国罕见病大会数据显示,我国有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每年新增患者超20万。
80%的罕见病跟遗传因素相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隋宾艳介绍,每个人身上约有5至10个基因缺陷,一旦父母双方拥有了相同的基因缺陷,就可能生下罹患罕见病的孩子。虽然这种概率只有万分之一甚至更低,但是对于遇到的家庭和患者来说,这就是100%的概率。
如今,动辄百万元的罕见病治疗费用有望逐步降低。不管是此前出台的《佛山市医疗救助办法》,还是近日上线的广州“穗岁康”商业补充健康保险,没有将罕见病及其治疗药物拒之门外。据刘丽测算,以脊髓型肌萎缩症为例,按照“穗岁康”的政策报销,个人自付总金额将从140万元降到45.7万元,自付比例为31.5%,“对于罕见病家庭来说,会是很大的助力”。
今年6月,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在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254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正积极会同财政、民政、卫健、红十字会等部门,通过全面摸底、精确测算,尽快研究制定出我省罕见病医疗保障机制的筹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