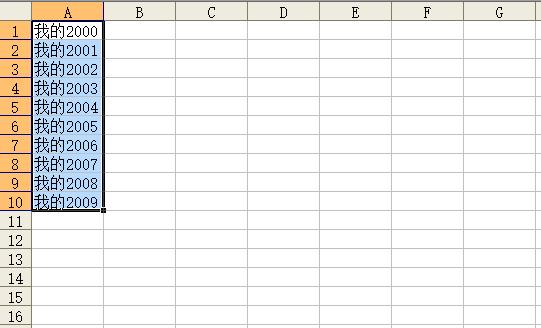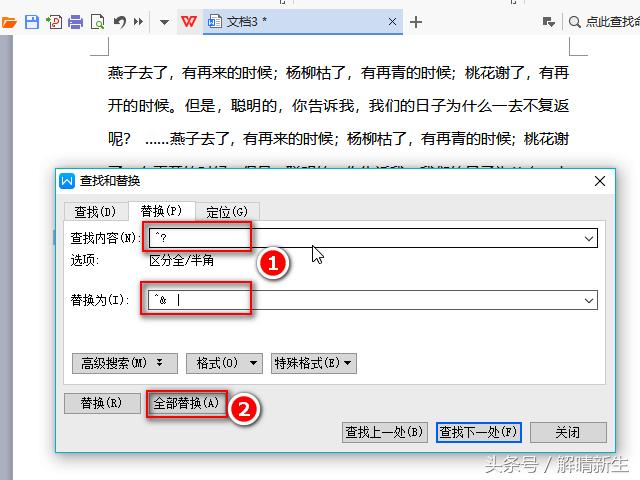在南京博物院里,有一件嵌松石青铜卧鹿的展品。
“呦呦鹿鸣,食野之萍”之句,自然而然地从《诗经》里走了出来。这头出土于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葬的铜鹿,瞬时勾起了我的浓厚兴趣。

嵌松石青铜卧鹿
它四脚蜷卧,双眼有神,两耳直立,仿佛在小憩之时忽有所思,欲呼朋唤友一起来分享身畔的水美草丰。
这仙境之鹿犄角槎枒,显示出极高的制作和审美水准,让思绪一下就发散到它出土的地方——涟水三里墩!
在古墓下面,是一处距今五千余年的新石器时期遗址。
五千年前的涟水是什么样子,我不得而知。在河谷滩野上,人们当是披荆斩棘,烧荒种田,纺纱织布,然后繁衍生息。我无法勾勒出斗转星移里的更迭和诗情画意的沉淀,可从一河一径一木一草中,依然能领略到沧海桑田的变迁。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与其它大江大河相比,淮河只能算是一位年轻后生。在三千年前,它才在属于自己的河道上呼风唤雨,可这并不妨碍河的两岸,桑绿千里,鹭鸟飞翔的诗画之美。是河,就得入海。萦望眼、云海相搀。淮河把一路风景和坎坷,一古脑儿地丢在了它的尾闾之地——涟水!

涟河风光
这“东临渤海,西带沭河,三涟绕北,长淮襟前”之地,在春秋时属吴,在战国时又先后属越、韩、楚,到了秦时干脆属东海郡。
千回百转,盘盘旋旋,走走停停,河水最懂得顺势而为的力量。东涟河、西涟河、中涟河在涟城附近汇出“涟河”的英姿,再流入淮河。我们对这片滩地应该改变态度,而多了一些飞在诗画之上的印象。
公元前117年,这片土地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护身符,人们称之为:淮浦。
田畴肥沃,宜植五谷。秦汉时期,就有“江淮熟,天下足”的谚语。
曾经水来成湖,水去成滩,成了美轮美奂的风景。万物之根扎在泥里,喝着淮河水,在阳光里可着劲儿长着。
瘟疫、蝗灾、战乱,让山河失色,大地黯然,士庶居民四散,北方人南迁,动荡与这片土地形影不离,跟随这片土地的名称也换来改去。
乱世,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隋文帝杨坚统一了分裂数百年的中国,开皇之治是华夏民族难得的短时盛世。他听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改变“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势在必行。
建议一旦由帝王发出,那就得郑重其事地执行了。议事堂上,官员们殚精竭虑地议着“淮浦”之地,也是那时的襄贲县,取一个什么名称来替代呢?
是恢复旧称,是维持现状,还是独辟蹊径?
东涟河、西涟河、中涟河全然不知议事堂发生了什么,依然在涟城附近融入“涟河”,汇入淮河。
大家争来论去,也没个统一意见,决定每人写个地名以供挑选。当摊开纸上所有的地名后,“涟水”两个大字,赫然成了主角!
隋开皇五年,襄贲县一个转身,成了涟水县。河还是那河,滩还是那滩,可世道轮回了许多次。
大唐诗人高适写诗赞道:“煮盐沧海曲,种稻长淮边。四时常晏如,百口无饥年。菱芋藩篱下,渔樵耳目前。”

《五岛胜境》摄影:许军
岁月流金,大地膏腴。
后世众说纷纭的“烛影斧声”成语,影响力也只止于京畿,很难企及这淮河尾闾。倒因岁岁稔熟,宋太宗赵匡义置涟水军,直至宋神宗赵顼当政,又改回涟水县,到了宋哲宗赵煦之时,涟水又复为军。
淮河入海口,在交通、经济、军事上都举足轻重。难怪它在朝堂之上,起起落落。可涟河是那涟河,淮河也是那淮河,戮力同心地滋养着两岸生灵。
战事频繁是历史里的家常便饭。涟水是南宋在东边的桥头堡,又是金过淮河必经之地,双方你争我夺,斗得不可开交。涟水时为宋,时属金,时而响起的蒙古铁蹄声也会横插一下。山河为之戚然,宁静很容易被打破,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处养兵牧马之所,是谁都惦记的。

景定三年,南宋统治者希望他的东边安定,因涟水在淮之东,又东滨于海,故改涟水军为安东州,这是寄予美好的期望和祝愿。明洪武二年正月降安东州为安东县。
水流千遭归大海。民国初年,安东县因与奉天省安东同名,改为涟水县。
如果选择一个王朝让我穿越,我还是愿意穿越到大宋王朝。纸醉金迷的光阴虽少了些许热血铿锵,可千古流传下来的,照例是那些梦幻一般的文字在光阴里的脉动。
“宋四家”书法大师里,就有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与涟水结缘。
熙宁七年,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时,顺路看望涟水好友盛侨,到密州后就写下“不羡京尘骑马客,羡他淮月弄舟人。”的千古名句。
钱钟书说: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

《五岛晨光》摄影:孙利
苏轼像一个提线木偶,在大宋那只巨大的转盘上,身不由己。苏轼由常州领命赴任登州途中第二次经过涟水,留下:“自古涟漪佳绝地。绕郭荷花,欲把吴兴比。倦客尘埃何处洗。”“涟漪”一词,为涟水打上了十足粉底。如今,涟漪湖成了涟水胸口上的一块温润碧玉。
苏门弟子黄庭坚,求学涟水,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诗文对涟水也是盛赞有加的。
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以太常博士来知涟水军。他守涟二年,多惠政,人称清官。涟水有洗墨池为证,说他在离任之时,洗去墨汁,以示清清白白,为涟水大地注入一股坦荡刚直的气息。
米芾写过:“千古涟漪清绝地。海岱楼高,下瞰秦淮尾。”之句,和苏轼的《蝶恋花•过涟水军赠赵晦之》首句仅有一字改动,与其说是“化用”,莫如说是借用最贴切。

《一泓秋水胜瑶池》摄影:许军
在涟水大地,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宋真宗赵恒年过四十方得一子,日夜啼哭不休,遍请名医皆束手无策。无奈之下,张榜悬医。时涟水承天寺内的和尚娄守坚,闻知揭榜,赶至京城,接过太子,对其屁股便打,并念念有词道:“莫叫莫叫,只怪一笑;莫哭莫哭,文曲武曲。”孩子竟然不哭了,可和尚还在不停地打着屁股,约莫打到四十,真宗及皇后看不过,上前拦住,卧佛长叹一声:“在位四十年已矣!”
仁宗即位时,卧佛早已云游四海,听母后讲起这段神奇经历,为表达对卧佛谢意,敕建妙通塔,以悼卧佛之异。
传说虽无从查考,但妙通塔建于天圣元年,也确为宋仁宗御旨敕建,这已被后来开启的妙通塔地宫内“敕赐承天院造塔记”所证实。
可以想象,当妙通塔落成之际,乡人请求仁宗为这里题“妙通塔”三字,仁宗欣然应允。彼时彼刻,涟水荣耀之至。然而,在鼎沸的掌声里,人们敲锣打鼓地将御赐匾额迎进拜殿时,这个王朝已开始走入命运的下半程。

妙通塔
一个传说引人入胜。在我想来,它应该是镇水镇灾的风水塔,毕竟,四渎之一的淮水在此入海需要十分礼遇。
社会动荡、河道淤塞,加之大海东去,使能仁寺活动日渐凋敝,而兵荒马乱的光阴,彻底终结了涟水大地之上属于大宋王朝的盛华。妙通塔和它一样,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如今,默立在公园西面的建筑庙通塔,就像大宋盛华的注脚,把涟水史上的黄金岁月与庙塔建筑艺术的高峰,小心珍藏。
因水而兴,因水而衰,仿佛是一个颠簸不破的轮回。黄河夺淮,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万千苦难。“沭阳财主宿迁庙,泗阳姑娘嫁人不坐骄,涟水人讨饭上学校。”活着,就要奋进,是大河留下的万千嘱咐。
当黄河离开之后,暴戾无常的那面消散,余下的只是作为一个母亲的温情脉脉。黄土沉积特盛,又受两岸人工堤的约束,成了高出地面的平原。

《一湖开宝镜》摄影:庞桂玲
在古淮河大堤上,长剑对弯刀,正义终战胜邪恶。亲历涟水保卫战的涟水籍军旅作家吴强在著名长篇小说《红日》里的开头描写了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
妙通塔常常寂静得有点过分,我们若看到了其背后闪现的光芒,就会明白,涟水大地在它悠久的年岁里始终凝望着脚下子民,那最动容的地方,是它悄无声息地把无数故事汇聚成一座定海神针的气息,再把这悠长的情愫缓缓渗入人间。
当我翻阅完资料准备写下这片土地的无数更迭之时,也就差不多翻完了半部华夏史。
此时,1676平方公里的县域确实和淮河、大海没啥关系,可瓜果稔熟四季分明麦浪翻滚却是不争的事实。历史的到来和远去,就像河水一样无声又富有生命的张力。如果它可以照鉴未来,正是这个地方越来越好的样子。
大河安澜,国泰民安。涟水又开启了新的纪元。不管它叫“淮浦县”、“襄贲县”、“海西郡”、“海安郡”、“安东州”、“安东县”……它都奔涌着人们最深情的期盼,这份期盼就叫:家。

妙通塔在每一个夜晚都会通身亮起霓虹,彷佛在告诉匆匆路过的人们,这里有过怎样的唱和,有过怎样的铿锵。博物院里的那头嵌松石青铜卧鹿也会出来,问询每一位涟水人,故乡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作 者:黄 睿
黄睿,男,生于1997年,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悠悠岁月》《我要寻找的方向》等散文集,发表作品累计950余篇,获《柳州紫荆花》《宁阳美主题征文》《保利杯书写大美匀城》等全国散文征文大赛一等奖,还获《首届汨罗江文学奖》《第二届中国(日照)散文季刘勰散文奖》《2017“诗兴开封”国际诗歌奖》等多项奖项。
审核、发布:张一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