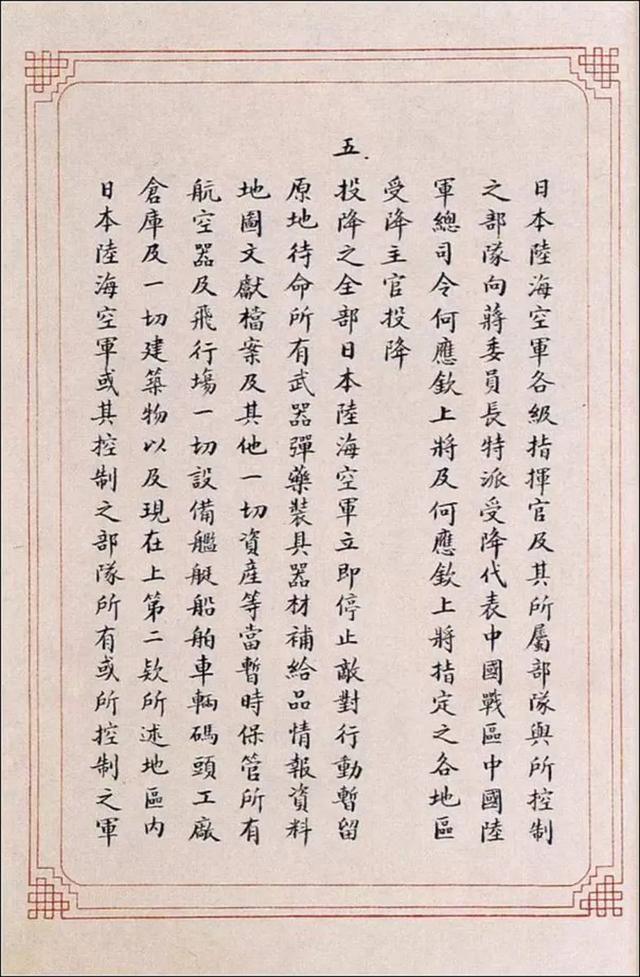引子
有人说:“生活是一袭华丽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在伪善的世界里,我们的爱不比任何人高贵,也不比任何人卑微。

影片《绿洲》以残疾这一边缘女性人物形象为主要叙事主体,将通常意义下的弱势群体转化为影片关注的主体人物,申诉着失语者的情感欲望,呈现出极具特色的批判主义与文化立场。导演李沧东以自身的男性视点审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摧残与迫害。

身体的维度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瘫痪的恭珠在和忠都通电话,画面镜头全部给到忠都,背景远处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着花样滑冰,肢体动作优美轻盈的花样滑冰极具观赏性,而电话那头却是身体因瘫痪而扭曲变形的恭珠。夹在两者中间的忠都是一个平凡操作身体的普通人,没有残疾,也没有任何技能。所以,在这一层面上,忠都从某种意义上更像是恭珠的另外一台“收音机”,帮助恭珠连接外面的世界,获得真实的生命。
同样作为边缘人物的忠都,刑满释放后发现自己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怪异的行为与小心翼翼略带试探的肢体语言无不标志着社会对他的排斥。

想象的维度
导演在影片中较多倾向于呈现粗粝且市井的真实世界,初看《绿洲》我们甚至会被影片所呈现的世界吓到,作为电影它似乎不太美,没有精美的人物造型,没有绚丽夺目的城市灯光,有的只是镜头中朦胧阴暗色调下呈现的与现代进步标榜的高楼大厦所形成强烈对比的低矮破败的住宅,但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狭小昏暗的房间里,瘦小扭曲的恭珠蜷缩在角落里,碎裂的光斑变成了蝴蝶飞舞在屋顶,带有“oasis”字样壁毯中的大象和印度舞者从壁毯里走进了恭珠的房间,脑瘫的恭珠变成了行动自如的正常人。那些被恭珠操控的“蝴蝶”光斑,是恭珠肢体的延展,某种程度上也是恭珠渴望自由肢体欲望的具象表达。
壁毯中的大象、印度女人是恭珠渴望行动自如的具体象征,身体残疾的恭珠渴望像个正常人一样被对待。影片中每到夜晚就投射在壁毯上的阴影则更多的是刻在恭珠心里的阴影,从内而外对恭珠造成的伤害与压迫。只有忠都一个人理解恭珠,给予她神秘的力量克服夜晚阴影的恐惧,实感的情感力量冲破迷障,汹涌而来。

爱欲的维度
两次的亲密接触让忠都对恭珠的爱完成从卑劣到纯粹的转变。第一次当无力反抗的恭珠昏厥过去,忠都立即用冷水将她救醒。第二次则是恭珠主动提出,动人、苦楚,却被突然返回家里的哥哥误认为是强暴,并再次被关进监狱。无法解释的恭珠只能用自残的行为表示抗议。
导演安排了恭珠涂抹口红的主动性欲望投射,但最终却无法推卸掉“脑瘫”的符号,无法为自己爱的人辩解。两个边缘人物的感情突破了传统符号化的爱欲,抵达未被世俗污染的纯粹情感,而这种纯粹的爱情也正因为越过了人们传统的认知,饱受着来自世界的误解与敌意。恭珠与洪都以两人爱情的牺牲也未能换来人们的反思与觉醒。

影片所展现的更像是被人们遗落的世界:一碗豆子饭,一张艳俗的壁画,一段甚至看起来都可笑的爱情。《绿洲》用它深邃的目光打量着这个泥沙俱下的丑陋世界,并重定义纯洁的定义:纯洁不是人类童年时对世界美好的误解,不是作为奇观和风景的某个远方,甚至不存在于人类过往的文明,而是在你尝过无数次人性黑暗,挣扎于无数鲜血与泥沼后的依然留有的天真。
导演以他独有的诗性叙事完成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这个病态社会的绝望与控诉。正如《绿洲》中的“恭珠”与“忠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被权利规训与压榨的身体,被生存规范与道德压榨的牺牲品,被主流价值否定的亚文明。


一影一话 谱人世虚实
俱是覆舟风雨 书字可抵愁
SuperFlaneur
公众号团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戏剧与影视学
终南影话 电影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