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夏
最近,一段短视频在网上传播,视频里,华坪女高的张桂梅校长,说自己拒绝曾经的学生,现在做了全职太太的女性的捐款,并且对她说“滚出去”。视频里张校长的表达较为愤怒,不断强调“女人必须要靠自己!”一时间引发了社会热议。
一种声音说,为什么要对全职妈妈这么大恶意?女性可以选择任何职业,包括全职做主妇。另一种声音说,不能仅凭一个两分钟不到的短视频就评判张校长的想法,她所强调的,是女性的自立自强而已。
又有一种表达是,正因为社会上有一股鼓吹“霸道总裁娶娇妻”的金丝雀生活方式,让“全职太太”这个不成职业的职业反过来动摇了许多想做独立女性的人的意志。一种表面看似“轻松”的人生,在整体上瓦解着之前几十年国家倡导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识。所以选择做“全职太太”的女性,是在女性往独立道路上努力前进时,拖集体后腿的人。

那么,张校长口中的“全职太太”,和我们日常生活中说的“家庭妇女”、“贤内助”、“女主内”等概念,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家庭范畴内,女性总和“经济无能”“情绪化”“婆婆妈妈”等负面词语相挂钩?谈论家庭事务里的女人时,她们本人在发声吗?
《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是一本1974年的作品,这是首次严肃对待家务劳动的研究,它第一次将“家务”这件表面上个体化的事情,放置在更广泛的公共领域进行讨论。虽然这本书已经距离我们半个世纪之久,但当代的《卫报》依然会在头条写:“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四十年了,女人仍然从事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这本书里提出的种种主妇之苦,眼前的世界依然没有解决,每一位女性都会被刻板印象裹挟,从而选择性地“被看不见”。
本书虽然不是所谓传统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但它在开篇就犀利而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学这一学科在家务领域的缺席与漠视。由于学科建立的过程中,多数都是不参与家务劳动的男性学者在论述和研究我们这个社会,因此“家务”几乎从未进入学术言说范畴,更谈不上“家务社会学”分支的建立。在西方社会学奠基的五位“元老”——马克思、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和韦伯——之中,仅有马克思和韦伯持有女性解放的观点,但他们的“解放”也基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婚姻模式,因此并未真正正视女性在整体社会活动中的价值。而这本书,划时代地完成了“家庭事务社会学”的显形,以40名伦敦家庭主妇作为样本,以深入的定性研究作为依据,让被调查的全职太太们说出她们的故事,让学术田野第一次展开在此前未被关注的领域。
妈妈最伟大?作为“职业”它最廉价
张桂梅校长一再强调女性要靠自己,老公靠不住。其实很多女性自己也明白,但或许选择了“全职太太”,是因为女性觉得自己难以承受家庭和工作的双份压力。这并不是说工作和家务皆苦,而是说,家务实在是太苦,苦到如果你顺从传统观念进入家庭这种组合后,只能承受这单一的苦痛。
事实上,职场给予女性的精神和经济支撑,永远是大于单一家庭生活的。
《看不见的女人》在调查了数十位不同阶层的女性后写道:“在女性的表述中,家务工作与职场工作相比是相形见绌的。因为无论职场工作是何种性质的,它们都能给女性带来陪伴感,社会认可和经济效益。”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职场妈妈”,这个概念乍一听,好像是很独立,给了女性多元身份的词语。其实,将“有酬劳”的工作和“无酬劳”的家务叠加起来,表面上似乎肯定了两种角色,却没有细细探究:家务本身,也应该被视为工作。
家务不被视为“有价值”,是从一个有毒的三段论开始的:
1、家庭生活中,女主内,男主外;
2、因此,男人工作,女人不工作;
3、因此,家务活动不是一种工作。
第三个论断似乎是前两个的推论,但这个三段论是错误的。它的错误在于,“家庭”与“工作”之间被刻意地切割了。
什么是“工作”呢?一种定义认为,工作具有五个属性:它需要消耗能量;它允诺对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做出贡献;它定义了社会互动的模式;它为工作的人提供了社会地位;最后,工作会带来收入。
在此定义下,有薪工作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家务劳动是无酬劳的。荒诞的是,仅仅因为一个要素的缺乏,家务在理论以及社会实践中,就被默认排除于工作类别之中,连带着做家务的家庭妇女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称呼眼前这一摊子繁琐事情,逐渐深陷泥潭,既没有金钱奖赏,也找不到对应的社会地位。
《被缚的妻子》的作者汉娜·加夫隆意识到了“双重角色”概念隐含的深意:今天的女性被认为有两种选择——外出工作或待在家里。这就意味着留在家里无关工作。吊诡的是,在其他工业化世界正朝着每周40小时运作而迈进的时代,女人,她们中很多人每周可能工作至少80小时,则被引导要视家务不是工作。
可能很多人觉得,半个世纪过去了,《看不见的女人》里所说的繁重的家务劳动已经可以被现代化的电器所替代了。那么,主妇们真的解放了吗?
《82年的金智英》里,金智英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你们认为我的劳动负担可以被洗衣机,吸尘器解除吗?那我问你,买来最先进的家电后,操作它们的是谁?还是我,不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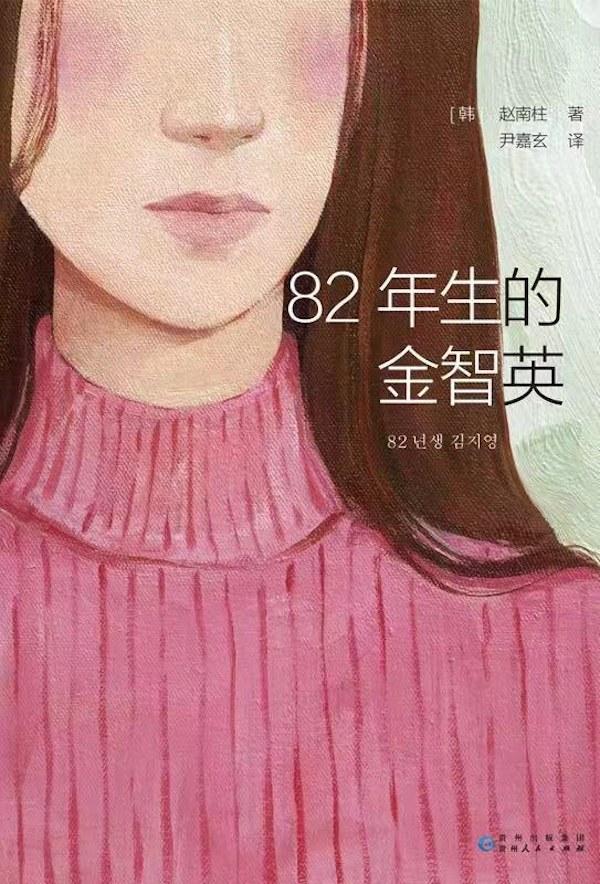
机械化大生产解放劳动力,放在社会化工厂里可能是事实,但放在具体的一个个家庭里,对于一位位具体的主妇来说,并不意味着解脱。赫茨伯格、毛瑟纳和斯奈德曼三位学者的研究报告《工作的激励因素》中观察到,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有助于减少工作上的不满情绪,但是并没有起到增加满意度的作用。也就是说,即便做家务能够稍微轻松一些,主妇们也只是抱怨少一些,但幸福感并不可能增加。
由于主妇所从事的都是“时间不灵活”的例行常规劳动,如做饭和洗衣服,而她们对干净的标准并无上限,因此会不断进行自我压榨,家里的活儿,永远会是做不完的状态。家里的清洁更是一项孤独的任务,需要做清洁的感觉与人性想要去社交的愿望相冲突。
调查中,一位做了妈妈的主妇说:
为什么每天要清洁厨房地板两次?好吧,那是因为孩子无时不刻在地板上玩耍,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让他爬在肮脏的地板上不好——他容易从上面感染上什么。
也就是说,外界认为的家庭主妇反正就是赋闲在家,“做自己的老板”。其实完全是大错特错,她们在家务问题上始终状态紧绷,心理压力巨大。
仅仅是因为家务活儿是“在家里”完成的,就足以让家庭主妇体验着某种程度的孤立。当孩子还小时,主妇唯一忠实的陪伴者是她的孩子,但一旦孩子求学离家,家里就只剩她自己。出门买菜、购物、遛狗等家务的外延行为,并不能增加她们与社会的连接,相反,白天与陌生人的短暂交流实际上会使她们产生负面情绪。流于表面的社交在不断地提醒家庭主妇:她缺乏的那些深入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是多么重要。
一孕傻三年?谎言!
最近某平台有一篇题为《我只是生了孩子,为什么整个社会都要惩罚我?》的文章指出,65%的职场妈妈有抑郁倾向,工作996+带娃007的模式,使得她们无法喘息。很多人觉得,做了妈妈,可能确实不必在职场上太有进取心,何况孕产妇会“一孕傻三年”,可能并不适合在职场上担任要职。由此,“全职妈妈”像一种顺水推舟,好像既然“你不行”,不如把机会留给单身者,留给无需孕产的男性,你的“让贤”,你的“后勤保障”,是一种“伟大的牺牲”。
期许女性“不拼搏”“不奋进”,并不是善解人意,相反,这些观念可能慢慢侵蚀女性的自我满足感和成就感,将她们加速推入“无用”的深渊。
怀孕生育这种延续人类族群的重大职责,是如何被贬低的呢?
阿特伍德曾在《使女的故事》里指出非常残酷的事实:女性的子宫,可以被高度物化为全社会都可以操弄的工具,女性的身体属于唯生育论的整个集体,唯独不属于她自己。身不由己的女性,在完成了生产后,紧接着面临的就是生产被剥夺侵占的时间精力和机会如何追回。而“一孕傻三年”等污名,实质上暗示女性不必再追回本属于自己的职场与社会地位。当然,可能有一部分经济条件较为宽裕的家庭能够让女性开始做全职太太,但负面的话语以一种莫须有的定论,把不同女性的不同追求,拉低到一个共同的低水平的状态里。这种轻视其实指向全体女性:无论你选择做全职主妇还是回归职场,都将因为精神涣散智商下降而不能具备很好的表现。这种假设本身就是有毒的。
日剧《坡道上的家》就是一部对“失智妈妈”“歇斯底里的母亲”等形象进行透析的作品。高度紧张加劳累,造成了“恐怖”的弑子母亲。但我们一定要细想想,她为什么不能从传统美德里歌颂的“伟大妈妈”里获得成就感?因为歌颂里没有任何实际分担,当空荡荡的家里,陪伴她的只有婴孩,而婴孩不间断的哭闹最终变成了提醒她疲累之源的警铃,尽管孩子本质无辜,但过劳产生的恍惚让她失去了理智,最终走上了悲哀的结局。
《看不见的女人》里有一个比喻,说的是许多人觉得家庭主妇就是“卷心菜”,完全沉浸在家庭事务中。这样的负面观念传递出的结论是:她们是没有个性特色,单调乏味,了无生趣的机器人。
可是,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一孕傻三年”,这份“傻”,“无趣”甚至“歇斯底里”,是长期被漠视被忽略甚至被压榨造成的后果。主妇在家里得到的肯定越少,偏执的可能就越大,为了校正这种孕产期造成的精神创伤,很多女性选择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但糟糕的是,即使夫妻双方在有酬工作方面是对等的,但女性对家庭主妇一角所负有传统职责的认同程度并没有降低。
学者拉波波特评论说,双职工家庭模式实际上更容易引起人们对家庭领域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刻板观念的过度信奉。某些女人认为职场女性给人冷酷、“男性化”、好强的负面印象,于是转而在“负责任的家庭主妇”一职上继续奉献。
女人不傻,但女人为了证明自己不傻,活得太苦了。
女人要帮助女人,整个社会也是
《乘风破浪的姐姐》里,万茜在采访时说了一句上了热搜的话:女人是可以帮助女人的。
这句话之所以鼓舞人心,是因为它冲破了很多流俗表达里,将女性互相树立为敌人,让她们为了争夺爱情、金钱或地位而互相攻击的可怕形象。
在分析张校长的言论时,有微博博主指出,“全职太太”可能和“家庭主妇”是两个阶层,前者养尊处优,十指不沾阳春水,天天就是美容购物;后者面容憔悴,困守厨房,辛劳半生。张校长可能只是反对后一种生活。

《看不见的女人》,[英] 安·奥克利 著,汪丽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
其实,在《看不见的女人》里,我们可以读到,作者安·奥克利没有把不同阶层的女性严格划分开讨论,她是把所有女性的艰难处境当作某种命运共同体来看。
这位社会学家敏锐地看到,所谓女性的阶层分化,很多时候是依附在男性的阶层上的。她说,人们根据丈夫的职业将女性分配到某个社会阶层,这些人为的区分可能是站不住脚的,主妇之间可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社会阶层差异,这样建构出来的阶级界限实际上可能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反而让人们忽视一些确切存在的有意义的比较。
也就是说,中产阶层以上的女性的经济宽裕,并不意味着她们精神和金钱支配上真的自由。中产阶层以上主妇地位的提升可能是由于她们从事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消费领域,但“买买买”会带来有收入一方(即她们丈夫)家庭话语权的提升,这种物欲的膨胀,恰好构筑了更密更大的牢笼。
我想,以张校长一手创办华坪女高的能量,她应该也不会推崇有钱的“全职太太”,而单独反对“家庭主妇”。割裂不同阶层的女性也是一种偷换概念,所有女性都应该有自立,不依附他人的觉悟,而不是在金钱这种单一维度上形成鄙视链。
要想“姐姐妹妹站起来”,不分贫富地走向强大,这本书的作者提出,可能需要做到三个层次:
其一是理论研究的进步。别小看家庭事务社会学,在这本书出来之前,该领域是一片空白。甚至整个学术界因为不把家庭主妇当回事,而从来没想过研究她们。这种忽视本身,就是很可怕的。
其二就是完善各种制度。随着女性运动的不断高涨,对各种实际立法等的推进也在进行中。作者提醒我们,不要总说“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取得足够成就,女人受到的压迫就像是一个长在她们身体内部的恶性肿瘤,全社会必须一起来了解这份痛苦,并帮助她们解除才行。因为善待女性,就是善待我们自己的母亲、姐妹和女儿,如果你也是女性,那每一次善待,都是善待你自己。
其三可能是一个美好的长期愿景:作者希望,这个社会终有一天能消除对女性的偏见。女人们自己也要认识到,没有一种低下的位置专门就该女性去占据。所有人应当对女性这种性别具有一定的想象力:想象她能办到他能办到的一切,如果办不到,是否有什么结构性的不公平在阻碍,是否可以帮一把,是否能够一起达成。
需谨记,理性、感性、柔软、阳刚……这些只是不同面向的个性,既不专属某个阶层,也从来不专属哪个性别。人类的悲欢,应当相通,有共情能力的人,才会更好地理解他人,理解自己。而由这样的我们组成的社会,才会更有希望,更能向前进。
在张校长的视频发出一段时间后,她口中的“全职太太”,当年的学生,也站出来回应了。原来,她在被校长严厉批评后,奋发图强,于次年考上了特岗教师,重回职场。这位黄姓女生说,“张校长话丑理正,她是从我们的立场去说的”。
“我们的立场”,就是自立自强的立场,是所有女性应该共同去走的路,这样的路走的人多了,“看不见的女人”才能变少。而下一代“被看见”的,是更自信更美丽的女孩。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徐亦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