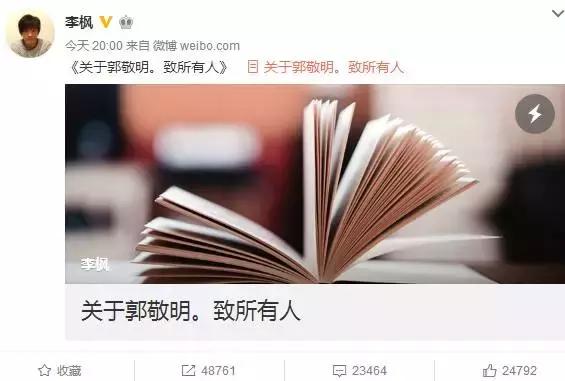【本文于去年首发,其中部分法律知识观点存在可更新之处,本期加以修改后重新推送】,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如何保护我们的消化器官?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如何保护我们的消化器官
【本文于去年首发,其中部分法律知识观点存在可更新之处,本期加以修改后重新推送】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并确定于2021年11月1日正式施行。
个人信息保护之话题在近几年甚嚣尘上。互联网时代高速发展的技术手段让人足不出户却形同裸奔。只要我们的爪机中还装着五颜六色的APP,我们就是一个“透明人”。从电话号码,到行程信息,再到消费倾向,传统上我们认为可以具化与不能具化的种种信息,全都扔在大数据的洪流中,供数据收集者分门别类、挑挑捡捡。在铺天盖地的技术手段面前,个人的反抗微不足道,这样的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法》能否从国家层面的发挥公共管理效能与法的规范作用,自引期待。
宏观来看,《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出台非是“孤立无援,临时起意”。于此之前,我国立法层面上对个人信息保护一直持肯定之态度。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对自然人个人信息保护已经做了相应规定,同时明确“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网络安全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办法》,以及《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都或多或少提到过个人信息保护这一话题。《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中,在提出要加快推进政务数据有序共享一项中,也特别提到了同时要依法保护自然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另一方面,某女子通过网络预订酒店遭遇“大数据杀熟”,人民法院判决运营商赔偿损失;某知名企业因涉嫌向境外提供不特定社会公众关键信息,可能导致国家安全受到侵犯,从而被禁止赴美上市等新闻,则是对个人信息保护和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近期在司法实务中的具现。本次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很大程度上是水到渠成的应运而生,其中某些基本原则与规范,在之前的法规规章中其实已经提及。
那么,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哪些尤为与我们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值得我们多加注意的内容呢?
<同意的撤回>
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加工等一系列处理行为,原则上均以个人的同意为前提。本次《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明确规定了,个人有权撤回其以前作出的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也应当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同时,除非是必要条件,信息处理者不得因为“不同意”或“撤回同意”,拒绝提供产品或服务。
<禁止大数据杀熟>
笔者认为,本法明确规定了大数据杀熟的违法性,此系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大重要举措,是尤为鲜明的亮点。
第二十四条规定
“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
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作出决定。”
对于身处的自动化决策网络的个体消费者而言,运营方应提供便捷的选项,使得消费者可以拒绝自动化决策的结果,且即使消费者选择接受自动化决策,运营方亦不得进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强化对敏感信息的保护>
数据处理信息的过程,既有对信息权属人影响较小的一般信息,亦会存在对其工作、生活、权益保护等方面具有特别价值的信息,立法者已经敏锐意识到在大数据时代,应对两者做区分对待,更应将后者视为敏感信息,进行特别的保护。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敏感信息的概念定义为: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同时列举了: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等具体项。
对于敏感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更为严格的授权条件和处理规范,同时,对于公民个人来说,也要更为注意对此类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和保密意识。
<个人权利>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信息权属人,个人对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和决定权,具体包括但不限于查阅、复制,要求更正、删除或解释说明等。如果个人认为自己的信息受到了侵犯,除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外,还可以采取向网信部门举报投诉的方式。
<最后的思考>
于我国而言,根据法定程序出台法律并从中央下发到地方,并不是一件难事。难题在于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下有对策”与“过犹不及”。笔者认为,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等行为并非是洪水猛兽,即使是基于商业目的而采取的大数据算法等手段,其本质上也是建立在民事活动的平等自愿原则上产生的科技营销方法,合理的运用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对个人信息保护予以高度重视的同时,不宜因噎废食,片面强调个人信息的保护而破坏正常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特别指出“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适用本法;本节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节规定。”“ 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即政府处理个人信息亦同样要遵循本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在法定的权限、目的内依程序进行。在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存储方面,政府机关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和公权力的使用,相对于一般的商业机构而言,实际上是绝对的“垄断”地位。由于政府机关性质不同于一般的商事主体,对于公民个人而言,个人信息如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受到滥用或侵害,其忧患与损失远胜于商业机构的营销行为。如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出现对个人的人格侮辱性评价,某地将不参加核酸检测作为失信信息录入公共信用归集和服务平台等其实也是广义上的个人敏感信息处理活动,部分也会引发热议。从现实情况来看,行政活动中对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危害性和社会影响远大于商业活动,但规制效果和规范力度却远不及对商业活动中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规制,虽确有复杂客观因素影响,但官火明灯的结果并不利于法的正确施行。或言之,此亦是《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中将“健全行政执法工作体系,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含义之一。
<其他>
读者如有希望深入了解法律领域的话题,可以文末评论或留言。如有兴趣了解更多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浙江禾泰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