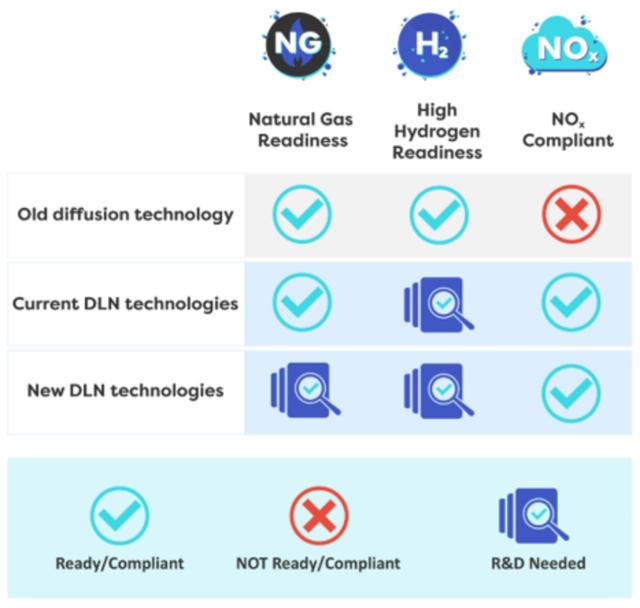七十年前的那个秋天,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位诗人发出“时间开始了”的感慨。七十年峥嵘岁月里,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国庆记忆。这记忆既是个人成长的私人叙事,也融入了宏大的家国历史,既铭记新中国创造者和建设者的丰功伟绩,也激荡着每一个中国人炽热的爱国情怀。
----------------------------------
西北之北 我在看不够的界碑边升起国旗
王子冰
16岁那年的冬天,我从寒冷而干燥的豫东平原北上参军,坐汽车、转火车、乘飞机,用两天一夜的时间来到了新疆阿图什,成了一名戍守边疆的战士。戎马倥偬十六载,蓦然回首,南疆的沙尘、北疆的风雪、高原的烈日、边关的冷月都定格成了心底的印迹。
边关,是我人生中最美的风景。
10年前的秋天,我到“西北第一哨”白哈巴边防连任职。那里的冬天雪深天寒,九月十月便开始下雪。当时,山里还没通公路,长达半年的“封山期”只能靠自给自足。为了让战友们安全顺利过冬,我要在国庆节前完成所有越冬物资的储备。直到新中国60华诞到来,军地共同组织了一场升国旗仪式,才让我暂缓了行程。
白哈巴村生活着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3个民族,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几乎雷打不动。国庆当天,每个人更是盛装出席。我初来乍到,被那次升国旗仪式所震撼。
战士把国旗抛向天空那一刻,队伍里响起了国歌,不论是蒙古族的耄耋老人,还是哈萨克族的懵懂少年,大家都跟着官兵的节奏,迎着凛冽的寒风,唱着心中的民族战歌。
队里有个名叫加尔恒·坎森的哈萨克族少年,有先天的认知障碍,在官兵的帮助下才学会识字、唱歌。他唯一会唱的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每次升旗时,都是他最激动的时刻。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村里的少数民族群众会说汉语的还不多,官兵在连队开办了“汉语教学班”,报名的人很多,最想学的就是国歌。
关山万重,祖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模样。在这个西北边陲的小牧村里,她同样伟大而神圣。
不久后,白哈巴迎来了入冬后最大的一场雪。一夜之间,孤零零的哨所便如同漂在雪海中的一叶小舟,封山期开始了。封山期最怕停水、停电。连队饮用的是雪水,用电主要靠配发的柴油发电机。遇到地下管道冻住或发电机损坏,生活就变得格外艰难。
但是,只要有机会,我依然会骑着骏马,背着钢枪,穿行在边关的风雪里,去瞻仰国境线上的一座座界碑。
在旁人眼里,界碑或许只是一砖一石,但在我们心里,重逾千斤。
封山期的时光很慢,日子就像界河里冻住的水,似乎静止了一般。我每天都会站在二楼俱乐部的窗户前,隔着玻璃,遥望远处的雪山。直到来年四五月份,山上的雪像被扯脱线的白毛衣,一点点褪到山顶,露出山坡上大片大片的青松时,春天就来了。
界碑旁有一片松树林,俯瞰其轮廓颇像祖国的版图,官兵便称其为“中华林”。为了让“中华林”名副其实,一茬茬官兵不断地修剪、移植、补种,每年国庆节,大家巡逻到这里,都会站在“中华林”前,进行一次宣誓,用铿锵的誓言吼出满腔的忠诚。
“西北之北,大雪纷飞。走不完的巡逻路,看不够的界碑……”后来,我写了一首关于边防的歌,这首《西北之北》在朋友圈里连续几天被“刷屏”。
祖国的边关越来越美。白哈巴修通了公路,接入了市电,网络也覆盖到周边的牧区,以后不会再有“封山期”。资讯发达的时代,牧民借助旅游开发富了起来,也忙了起来。但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从未间断,每家每户的门楣上都插上了国旗,清风徐来,像一片红色的海洋。
今年国庆节是新中国70华诞,除了升国旗仪式,白哈巴还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一台主题晚会。除了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哈萨克族的“黑走马”、蒙古族的顶碗舞,我和战友还为晚会创作了歌曲《为祖国站岗》,只等那天军民同台,普天同庆。
我每次休假回家,总被朋友问起:“边关那么苦,为啥你总说边关很美?”“当兵那么久,真的不会腻吗?”其实,我很想告诉他们,边关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守卫在那里的那群人。他们从懵懂无知到眼明心亮,从当兵吃饷到心怀家国,所追逐的不是一人之利,而是一国之安。
阿尔泰山物产丰富,每座哨所都处在边境前沿,许多盗猎、盗采的人员总会利用各种手段躲过盘查、遁入深山或越过边境,我听许多老兵讲起过他们与盗山者之间的斗智斗勇。狼群报恩、哈熊袭营、山盗谜踪之类的故事,总让我听得欲罢不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希望这些故事能够流传下去,让后来的战友续写这些故事时,也传承起这种精神。
守卫一条边防线,刻下一生戍边情。桌上的日历越来越薄,预示着我的军旅时光所剩无几。我知道,今后无论走到哪里,边关已和我的生命融为一体,卫国戍边的情怀永远都不会变。
(感谢“一号哨位”对本文约稿的支持)
无数难忘日夜只为那个伟大时刻
陶西平
1949年10月1日清晨,我和同学们一道,排着整齐的队伍,迎着晨曦,满怀豪情地走向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为了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经历了无数个难忘的日夜。
我在1948年考入北平四中,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四中。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奄奄一息,无人顾及教育,学校破烂不堪。由于通货膨胀,要用一袋面粉缴纳学费。初中年级已经没有完整的课桌椅,学生要抽签自备桌椅。我家从东单小市买了一套旧课桌椅,我的同桌李敖从家里搬来一张小八仙桌。还有同学摞起几块砖头,上面放一块木板当课桌。
开学3个多月后,我们到学校才发现,国民党士兵在校门口站岗,不许进校,连书包都不许取出来。原来,傅作义的部队已经把学校作为阵地,操场上架起4门大炮,军队驻扎在校园里,连我们的课桌椅也被当成柴火烧了。
学校停课到年底,忽然有的同学传来消息,希望大家回校。我们回校时,看到校长室前的地面上整齐地放着一排排步枪。国民党兵躲在屋子里,不出来了。当我正在纳闷时,几位高中同学,后来知道他们是地下党的同志,站在椅子上,对大家激情满怀地说: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傅作义军队就要出城整编,解放军就要进城了,希望同学们一起欢迎解放军进城。同学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接着,我和不少同学一道,每天来到学校,学唱革命歌曲《东方红》《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用彩色的纸做小旗子,听解放区的故事。1949年年初,北京四中的队伍在西四牌楼的路边,挥舞着小旗,高唱着歌曲,欢迎从西直门进城的解放军坦克和战车上豪迈的战士。
不久,地下党和老区来的同志接管了学校,学校开始复课。那时,党在青年中的外围组织还没有公开。但是,在学校里建立了进步的图书社,在图书社里除了有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著作,还有赵树理等作家的小说,像《李家庄变迁》《李有才板话》等。不少同学去看书,实际是接受革命的启蒙教育。1949年4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5月地下党的青年外围组织成员公开身份并转为团员,原来我所在的班里已有两位中国民主青年联盟的成员,他们也是我最早相识的团员。
当时,最令人激动的是在平津解放以后,大军南下,捷报频传的时刻。4月南京解放,5月西安、上海解放。每有喜讯传来,同学们就上街游行庆祝,白天举着红旗,晚上提着灯笼,一路高歌,一路欢呼。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下工作团,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于是学校里又掀起参加南工团的热潮,四中许多高年级同学甚至还有初中同学踊跃报名,随军南下。
当年7月,北京市为了加强学校的革命队伍建设,成立了大中学生暑期学习团。在党员班主任和班上团员的影响下,我已申请入团,所以也被允许进入学习团学习,这是为我一生理想信念奠定基础的重要时刻。学习团的主任是彭真同志,有4个分团,三分团主要是中学生,分团主任是汪家镠同志。我们每天早晨提着马扎,唱着歌排着队去会场听报告,听了艾思奇、胡绳、刘澜涛、荣高棠等领导和专家的报告,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党史、学生运动等理论。
在8月灿烂的星空下,我和一批同学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上庄严宣誓,成为最早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接着,就是迎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开国大典。当时,天安门广场还是丁字形,堆积着多年未清理的垃圾,同学们和许多群众一道来到广场进行清理,在垃圾的底层甚至还发现明清时代的残留。大家挥汗如雨,但心情舒畅,每个人都希望让广场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启航。
1949年10月1日上午,北京四中同学穿着当时最美的礼服——白衫、蓝裤子,早早地来到天安门广场,虽然位置离城楼较远,但个个精神抖擞。大家席地而坐,高唱革命歌曲,等待那庄严的时刻到来。下午3点,广播喇叭里传来毛主席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顿时广场红旗飘舞,万众欢腾。接着举行阅兵式,我们仰头看着飞机轰鸣着飞过蔚蓝的天空,感到无比自豪。阅兵式后,我们起身开始游行,校旗飘舞在队伍的前面,从广场游行到学校,已是夜晚,但大家心潮澎湃,仍然欢呼歌唱,还扭起了刚刚学会的秧歌,久久不肯散去。
70年前的这一天,镌刻在中国的历史上;迎接这一天的日日夜夜,镌刻在北京四中的校史上,也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心里。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荣誉主席)
曾经的中国骄傲至今让人念念不忘
薛一博
离开中国多年的阿塞拜疆著名汉学家、前总统战略研究中心亚洲国家内外政策首席顾问拉沙德·卡里莫夫先生,对10年前在中国工作时的一段经历仍念念不忘。2009年,拉沙德是阿塞拜疆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的一名外交人员,亲历了国庆60周年庆典。
回忆当时亲历的场景,拉沙德描述得清晰而具体。欢乐的人群、飘扬的红旗、大红的灯笼、蓝天白云下的天安门和华表,都给他带来醒目而强烈的视觉冲击。尤其是,“20万军民参与的盛大阅兵仪式,让我除了感到雄伟、壮观、惊叹、震撼,还有感动”。
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多年,精通汉语的拉沙德先生当然了解中国的发展状况和成就,他在当时的中国社交网络上也看到了网民们自然流露出的浓浓自豪感。“神舟飞船”“国产大飞机”“高峡出平湖”“高原天路”“磁悬浮列车”“北京奥运会”“一国两制”……这些词语一个个从他的口中蹦出。拉沙德还引用了他从网络上看到的一个说法儿,新中国60年,早就从“油灯岁月”发展到了“网络时代”。
拉沙德先生的一言一行都散发出浓厚的“中国气息”,如果只闻其声不抬头看人,你会误以为是在跟一个纯正的中国人对话。拉沙德说:“你可以叫我的中文名字,罗仕德。我与中国很有缘分,我曾经在这个国家学习、生活、工作了15年。是中国培养了我,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在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就没有现在的我。”
拉沙德·卡里莫夫是土生土长的阿塞拜疆人。199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巴库国立大学中文系,并在一年后通过一项教育合作协议赴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自此与中国结缘。在北语本科毕业后,拉沙德留在中国深造,先后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然后,他选择留在中国工作,参与阿塞拜疆驻华使馆的工作,为外交事业作贡献。
在北京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是拉沙德“最为怀念的时光”;亲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则是他在中国15年的“精彩瞬间”之一。直到现在,每次去北京出差,他总会回到母校坐一坐,见见老师和同学。2017年,由他编撰的《汉语阿塞拜疆语词典》由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工具书实现了拉沙德早就萌发的一个理想,尽管“编写词典的过程非常耗费精力。但看到了越来越多的阿塞拜疆青少年在学习汉语,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一切都是值得的。”
新中国即将迎来成立70周年的日子,拉沙德接着前面谈到的“油灯时代”“网络时代”话题说,仅仅10年过去,用“网络时代”已经远远不能描述现在的中国。即便是用现在流行的“5G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等,也不足以描述中国的发展状况。“新中国即将庆祝成立70周年,虽然今年我不能亲历今年的隆重庆祝活动,但10年前的经历,让我能够想象即将在中国、在北京出现的盛况。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有着更加光明的未来。”
19岁长安街的不眠夜 感觉自己站在了历史中心
蔡啸天
作为第一批90后,我即将30岁,也即将迎来人生中第三次国庆大典。虽然这样表达有些渺小与宏大的错位感,但毕竟每一次新中国十周年国庆,我和她的关系都不尽相同,因此也在个人生活中构建起了某种历史维度。
1999年,我9岁,在五线小城的家中,是一个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国庆阅兵游行的孩子,一个完完全全的观看者、仰慕者。国庆大典上的一切似乎只是庞大的象征文本,模糊的记忆,只留下了对历史赞美诗一般的遗忘。虽然那时没有互联网这样的情感出口,不过对于9岁的我而言,即便有,我也只是“点赞收藏”。
作为一个小军迷,那年的阅兵又给我从军报国的热情添了一把柴火。此后,自己的每一步努力都奔着考军校的目标而去。2008年高考以后,我搭上了国防生政策的便车,有幸步入以前未敢想过的中国人民大学就读。
更未想到,2009年,我19岁,第二次和国庆大典相遇,就成为一名参与者。那年暑假,刚参加完为期一个月的加强版军训,回家还没来得及见老朋友,就接到返校参与重大任务的通知。连夜排队买票、和家人匆匆告别,一路上班级QQ群里一直在讨论,“难不成让我们参加阅兵?”“已经快9月了肯定来不及”……
回到学校,领到花束、祥云方巾、印有“我与祖国共奋进”的T恤衫,答案也随之清晰——我们参与的是国庆群众游行“北京奥运”方阵。由于前期进行合练的同学中有部分因故不能继续训练,作为有一定队列动作基础的国防生,成了不二之选。
时间紧迫,8月27日上午,我们第一次参加校内合练就被选为排面标兵,以引导标正步伐。暑热未尽,紧张的排练对于其他同学而言是考验,但对于刚在部队摔打过的国防生则不在话下。齐步走对我们来说是基本功,更大的责任不在于自身走好,而是努力带动引导其他同学保持整齐。特别是“北京奥运”方阵需要配合《我和你》的抒情音乐前进,双手相应做出规定的表演动作,这些都给合练带来一定难度。
演练很快进入倒计时。9月7日凌晨,参演人员经过严格安检前往天安门地区进行整体合练。是夜,我见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巴士车队、轰鸣而过的重型武器装备、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游行群众。我躺在长安街的路中央仰望星空,于漫长而没有黑暗的夜中等候出场,毫无困意。
现在回忆起来,似乎在夜色中更能让人感受到历史与个体之间的有效关联。我们虽然没有穿着庆典上的志愿者服装,花束还包着塑料纸,方阵中的花车也没有搭建完成,但这反而给人以思考的空间。对我个人而言,在此之前,历史一直存在于书本或影像中。就像我9岁时一样,我观看、敬畏,为其兴衰荣辱感到自豪或悲伤,但总感觉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即便是从军报国的理想,个人化的东西也更多一些。而19岁那条未眠的长安街,让我开始感受到个人生活和国家历史的水乳交融,这种无可替代的经历,使我对胸前“我与祖国共奋进”这句话有了浓烈的感性体悟。
庆典当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在等候区高唱国歌,聆听阅兵式传来的问候与回应,仰视凌空飞过的战鹰。而之后的进场、行进、疏散,以及绚丽的花车、恢弘的音乐、挥手的奥运冠军、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则像一列隆隆而过的火车,疾驰过东西华表间的96米,震撼心灵,加速呼吸。
有同学说,走过天安门前的那一刻,感觉自己站在了历史的中心。不得不说,对大多数人而言,参与国庆游行,这种具有现场感的历史体验,的确是人生中少有的荣耀时刻。我也毫不例外感到十分光荣,游行的道具、服装、证书等,都被我视若珍宝,收藏在家中。
但没有现场感,就代表我们没有处在历史之中吗?显然不是。然而要对之有真切的理解,却需要生活与实践。
2012年夏,我作为国防生,从校门直接迈入营门,保家卫国的使命感扎扎实实也落在了肩膀上。7年军旅生活中,我经历了基层的摸爬滚打,体会了机关的严谨细致,从事过多种多样的业务,执行过大大小小的任务,工作平凡,却有意义。
在这些看上去并不宏大的人生历程中,我开始体会到,2009年参与的国庆游行不仅是谈资、标签和荣耀,更是一种契机、源起和动力,它像母校“实事求是”的校训,也像新时代革命军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要求,鞭策我、激励我、指引我,用一名军人的使命担当和干事创业的具体实践,继续保持个人发展和祖国进步间的密切联系,努力创造出比参与国庆游行更为荣耀的成就。
2019年,我29岁,虽然不在首都,但很荣幸能作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以守护者的身份祝福新中国七十华诞,见证恢弘的国家庆典。
大国重器冰冷外壳下 燃烧着炽热的心
望海洋
我是一名“军工人”,工作与国家的尖端武器装备有着密切的联系。父亲是一名人民解放军,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对军人充满了崇拜与敬意,与此同时,也对武器装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学三年级时,父母第一次带我去军事博物馆,当我看到伟岸的坦克、帅气的战机和高耸的导弹走出图画书的世界,陈列在我的面前时,我瞬间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震颤。
然而,随着我对军事装备知识的了解,年幼时初入军博的那分激动,也渐渐演变成了一种忧国之情。不论是国内出版的军事刊物,还是我自行搜罗的网络资料,都传递着一个令我不安的讯号——我国的军事装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太远了。而在与父亲的交流之中,我也感受到了他作为一名解放军军官所具有的使命感与紧迫感。我立下志向,一定要亲身参与制造世界顶尖级的武器装备。
立下志向的那年,我观看了2009年天安门广场的国庆大阅兵,希冀着有朝一日,能让国庆阅兵上的武器装备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顶尖。不久之后,我顺利考取了大学的相关专业,由此开启了真正的军工生涯。毕业季求职时,当同学们纷纷拿着自己的简历,寻找光鲜体面、薪酬优渥的工作时,我坚定地走进了现在这个规模不大、薪水不高,但却早已在我的“调研”中被锁定为“目标”的军工单位。因为它能够让我直接接触到令我魂牵梦萦的武器装备,同时也能给我一个研究和改进这些装备的机会。
说来也是一种缘分,见习期满之后,我在单位被分配到的第一个大型工作项目,便是对即将参加201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的部分装备进行检测与维护。当我摸着检测对象那冰冷而坚固的外壳时,心却在炽烈地燃烧——这不仅是因为我实现了当年的梦想,也是因为双手触及的检测对象,与10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同类装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大国重器,凝聚着东方崛起的梦想,倾注着那些和我朝夕相处前辈们的心血。虽然检测和维护已经确保万无一失,阅兵当天,我还是攥紧了双拳紧紧盯着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每一种装备。与2009年相比,我的自豪依然,那份忧思也仍在心底激励着我,但是,亲自检测最新装备的宝贵经历,使得强而有力的自信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就算我国军工产业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却在以极快的速度缩小,而在未来,我们的中国必将能够创造新的奇迹。
不知不觉中,4年又过去了,又一次国庆大阅兵将要如期而至。我的工作还一如从前——时间对搞研发的人而言,流逝得似乎总是比常人模糊、缓慢。因为研发本身就是“十年磨一剑”的“慢功夫”。当人们为那些出自我们同行之手的“大国重器”欢呼喝彩时,我深知其背后藏着多少常人看不到,也没必要看到的不易与艰辛。作为祖国的“铸剑者”,我们不必为人群的欢呼而躁动,也不必为一时没能拿出成果而气馁。对特定的武器装备而言,有些改进可能是只有专业人士和“军迷”才会注意到的细节,但在我们的心里,却已经有足够结实的分量。
因为部署变化,今年我所在的单位不再承担阅兵装备的检测维护工作,但我也不难过——这意味着另一个单位里,我的同行们在继续着守护“大国重器”的任务,那些和曾经的我有着类似心境的年轻人,将有机会体会和当年的我一样的激动人心时刻。当那些经我们这些“军工人”之手检测的装备,在70年大庆那天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心跳加速,手掌发汗。因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那些武器装备威风的外形,更是其钢铁外壳里包裹的炽热灵魂。
本文源自中国青年报客户端。阅读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中国青年报客户端(http://app.cy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