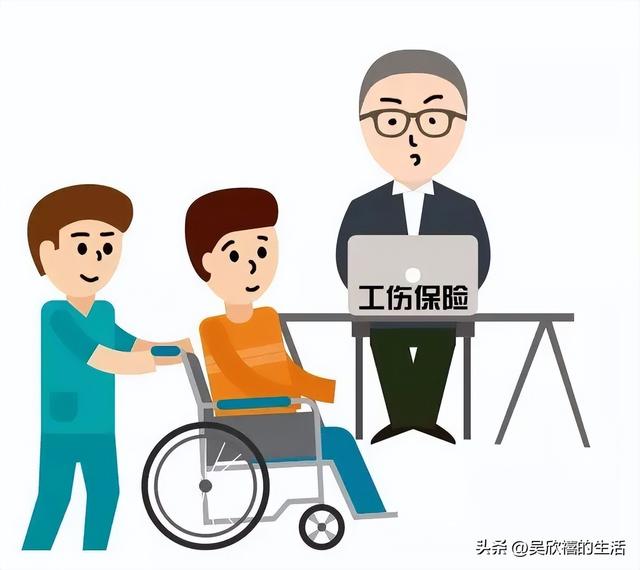以前发过的关于佩索阿的文章:
佩索阿: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裂缝
凌越:隐匿在自我的迷宫(谈佩索阿)
程一身:三问佩索阿
凤凰:
《牧羊人诗选》,看上去可能不如我们上次发的那些好读,需要更多的思维参与,但却是真的好诗。佩索阿在牧羊人诗歌中反对形而上学,反对通过纯粹思辨去把握宇宙,认为那是不得法的。这种思想和近代哲学反对形而上学的步伐是一致的。假如读者对西方哲学史有一定的了解,就会对牧羊人诗选有更深的感触。佩索阿的诗歌不是沉迷在对事物表面的感触,而是对事物存在的本质追问,虽然它在此倾向认为事物并无什么本质,它就是它显现的那样。(假如上帝存在,他就该穿过草地向我走来,告诉我说“我在这里”。)通过佩索阿,我们看到,思想其实可以化为诗歌,而并非仅仅是情感或情绪(在某些人那里还有叙事)才是诗的。因为,思想也有感觉性,也涉及我们的存在,只要不沉迷在思想的逻辑推理,而是从思想的感觉性切入,纯粹思想的诗歌也是可能的,并且有相当的深度和动人性。惠特曼、米沃什、佩索阿严格上来说写的都是关于思想的诗。这种思想的诗,和那种说理的诗,并非一回事。说理的诗是用思维的、哲学的方法写作,就像哲学家在做论文,这样的东西是不能成诗的。但假如用诗的方法进入思想,如佩索阿等人,思想就可以以诗的方式显现。两者表面相似,其实有质的差别。一个是诗,一个不是,这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说“哲学是概念的诗”,这仅仅是比喻,说的是哲学所探讨的东西具有诗性,但哲学本身却不是诗,和诗把握世界的方法完全不同,虽然两者在某些方面有交集。
风很静
风很静
正轻轻越过荒废的田野。
它好像
是那种……青草由于对自身的惊恐
而颤栗,而不是由于风。
但这温和的,高处的云
在动,它仿佛
大地正飞快地旋转而它们,
因为了不起的高度,正慢慢经过,
在这宽广的寂静中
我可以忘记一切---
甚至我难以复活的生命
在我赞美的事物里也不会有它的小屋。
我的光阴,它错误的旅程将用这种方式
品尝真理和现实。
恐惧之夜
在恐惧之夜,所有夜晚的自然本质,
在失眠之夜,所有我的夜晚的自然本质,
我记得,在摇摇晃晃的磕睡中醒来,
我记得我做过的以及在生命中我也许已经该做过的一切。
我记得,而一种怒火
传遍我的全身,就像身体的一阵寒冷或一种恐惧,
我的无法挽回的过去---这才是真正的死尸。
所有其他的死尸很可能只是错觉。
所有的死者也许还在另外的地方活着。
所有我过去的时光也许还在什么地方,
在幻觉的时空之中,存在着。
在消失的谎言中。
但从前我所不是的那个东西,我没做过的事情,我没有梦见过的东西;
什么是现在我才看清我该已经完成的,
什么是现在我才清楚地看见我该已经---
这是那个超过所有上帝的已死的东西,
这个---总之,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好的部分---它甚至
不是上帝所赋予生命的……
如果在某个确定的地点
我转向左边而非右边;
如果在某个确定的时刻,
我说了是而非否,或说了否而非是;
如果在某次交谈中
我忽然想出一个句子,而现在我在昏睡中却要仔细推敲---
如果事情是这样,
今天我就会截然不同,也许整个宇宙
会在昏迷不醒中被复活成另一个样子。
但在那不可挽回地失去的方向上,我不曾改变,
一点没变,想都没想过,只是现在我才认清了它;
但我并未说YES或NO,只是现在才注意我没说过这个;
但我未能完成的诗句如今却在我心中翻涌不息,它们全都
清澈,自然,逼真,
最后,谈话集中了,
全部的问题都解决了……
但只是现在,那从未存在的,也的确不会存在的事物,伤害着我。
我确实已错过的,在任何的形而上学体系中,
都没有抓住一点希望。
也许我能将我梦见过的带到另外的世界。
但我怎能将我忘记梦见的事物带给另外的世界?
是的,这些将要去乞求的梦,是真正的死尸。
我把它永远埋葬在我心中,为了全部的时间,
为了全部的宇宙。
今夜,我无法入睡,而宁静环绕我
像一种我无缘分享的真理,
而月光在户外,像我无法拥有的希望,
对我来说是看不见的。
《牧羊人》 选
1.
我从未照看过羊群,
但仿佛我曾经看护过它们。
我的灵魂像一个牧羊者,
熟悉风向,了解太阳,
与四个季节携手前进
去跟随去倾听。
悄无人迹的大自然的全部静谧
来到我身边坐下。
但我留下了悲伤就像落日
因为我们的想象泄露了它,
当一场寒流降落在山谷遥远的一侧,
你感到黑夜已经闯入
像一只蝴蝶穿过了一扇窗户。
但我的悲伤是宁静的
因为它自然,正确
必将出现在灵魂里
当它正思索着,它就是存在的
而双手正摘下花朵,看都不看是哪一朵。
在一阵刺耳的牧铃声中
在道路拐弯的地方,
我的思想是满足的,
只是,我很抱歉我知道它们心满意足,
因为,如果不知道这一点,
它们就不会既满足又悲哀,
而是又欢快又满足。
思考是难受的,就像在雨中散步,
当风正升起,雨似乎要越下越大。
我无欲无念。
做个诗人在我便是毫无野心。
它是一种让我独自呆着的方式。
而如果有时我渴望了,
为了想象的缘故,渴望成为一个牧童
(或成为一大群羊
为了漫山遍野地跑动,散开,
在同一时间里变成许多种快乐的生命),
那只是因为我感受到了我对落日进行的描绘,
或当一朵云在光芒之上掠过它的手,
而一阵寂静穿过敞开的草原漫游。
每当我坐下来写诗,
或者,当我沿着道路或短短的隧道漫步,
在我大脑里的白纸上写诗,
我感到双手似乎像牧人的手一样蜷曲
看见了我自己的轮廓
就在山巅上,
倾听我的羊群,看守我的理想,
或倾听我的理想,看守我的羊群,
出神地微笑着仿佛一个不明白
什么正被言说的人
试图要假装明白。
我向所有那些可能阅读我的人致敬,
向他们脱下我脱了线的帽子,
当他们看见我在我的过道里
而公共车好不容易才抵达山巅,
我向他们致敬,祝他们风和日丽,
享有雨水,当他们需要雨水的时候。
他们的屋子也许
就在一扇打开的窗户下边
一把可爱的椅子,
他们也许就坐那上边,读着我的诗篇。
而当他们阅读我的诗篇,也许会想到
我是某种本性的事物---
比如,一棵老树
在它的浓荫里,还是孩子的时候,
他们猛地坐下,厌倦了游戏,
擦着滚烫的额头上的汗水
用那带条纹的罩衫的袖子。
5.
丰裕的形而上学存在于全然的不思不想当中。
我欲何为 思考这个世界?
我该怎样理解我思考的这个世界?
如果我病了我就会琢磨它。
关于事物我拥有怎样的观念?
关于因和果我拥有怎样的观点?
关于上帝和灵魂以及世界的造物
我有着怎样的冥想?
我不知道。对我而言,思考这些等于关闭我的眼睛
再不思考。应该画出我窗户的
窗帘(但没有窗帘)。
事物的神秘?我该怎样了解神秘是什么?
唯一的神秘是那儿有个人他也许思考着神秘。
一个站在阳光中的人,闭上眼睛
开始忘记太阳是什么
去想许多炙热的东西。
但他张开眼睛,看见太阳,
现在他再也不能想着任何东西,
因为阳光远远胜过
所有哲人所有诗人的思想。
阳光不知道它正在做什么
所以它不会堕入迷途,所以它平常,它不赖。
形而上学?什么形而上学让世界有了这些树?
那正在绿着,长出树冠和枝干
在它们的时辰里交出果实的树,---它们不是用来
让我们沉思的,
我们,不知如何去认知它们。
但还有什么形而上学比它们的更好
不知道为何它们活着
不知道它们的无知?
‘事物的内在结构’……
‘宇宙的内在奥义’……
都是假的,都意味着虚幻。
人们能想出那些,简直不可思议。
那就像思考理智和终结
当早晨来临,带着一线
曙光,越过树木的边缘
一块模糊的灿烂的金子扫荡着,冲散黑暗。
去思考事物的内在奥义,
是浪费精力,就像思考健康
或把一块玻璃投入泉水当中。
事物唯一的内在含义
是它们没有任何的内在含义。
我不相信上帝,因为我从未看见他。
如果他想让我信他,
他当然应该前来与我交谈,
应该穿过我的过道进来,
对我说:我在这里!
(也许那声音对某人的耳朵来说,
有点滑稽,他不知道观看事物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那个用事物本身所教导的知识
谈论事物的人。)
但如果上帝是花朵和树木,
是群山,是太阳和月光,
那我就信他,
那我就每时每刻地信他,
我全部的生命就是一次祈祷,一次弥撒,
一次看得见、听得着的圣餐仪式。
但如果上帝是树木,是花朵,
是山峦,月光和太阳,
为何我还要叫他上帝?
我叫他花朵,树木,山峦,太阳和月光;
因为如果,为了我看见他,他把自己变成
太阳,月光,花朵,树木和山川,
如果他化身树木,山川
月光和太阳、花朵向我现形,
那是他想让我认识他
就像认识树木和山川和花朵和月光和太阳一样。
因此我服从他
(关于上帝我还能比他自己知道得更多?),
我本能地服从他,
就像一个人睁开眼睛,看见了
我叫他月光,太阳,花朵,树木和山川,
我爱他但不想着他,
我想着他通过凝望和谛听,
在所有的时辰我与他同行。
7.
从我的村庄我察看,就像从大地上
人能看到的宇宙一样繁多……
所以我的村庄像任何别的星球一样大
因为我就是我看到的事物的尺度
而不是我自己身高的尺码……
在城里,生活比起
我的山巅之家的生活更加渺小。
在城里房屋关闭视野,把它锁起来了,
藏起地平线,将我们的视线从整个天空推开,
把我们缩小因为他们夺去了我们的眼睛
所能赐予我们的东西,
让我们变穷因为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观察。
13.
轻盈地,轻盈地,非常轻盈地
一阵风,一阵非常轻盈的风,吹过
又溜走,依然是非常轻盈。
而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也没有知道的愿望。
14.
我不为诗韵发愁。很少会有
两棵并肩伫立的树是均等的。
因为花朵拥有色彩我沉思并写作,
但表达自我的技巧远远不够熟练。
因为我缺乏变成万物的
神圣的质朴,徒俱外表。
我注视着,感动着,
我感动是因为当土地倾斜,水开始流淌,
我的诗歌自然得就像一阵风在升起……
24.
我们观看的事物才是事物。
为何我们只看见一个事物如果那儿还有另外一个?
为何看见和听见会是自欺欺人
如果看见和听见真的是看见了,听见了?
最根本的是要善于看,
善于不带思辩地看,
当看着的时候真的能看见,
看的时候不去思辩,
思辩的时候不去看。
但做到这一点(可怜我们给自己的灵魂
穿上了那么多的衣裳!)
要求一整套学习的课程,
一段学会忘却的学徒期
一种遁入修道院的自由的隐居
诗人说那种地方群星就是永恒的修女
而花朵就是某个独立日的热情的悔罪者,
但那儿,在尽头,星辰仅仅是星辰
花朵仅仅是花朵,
所以我们才称它们星星和花朵。
25.
这孩子不停地从芦管里
吹出的肥皂泡
半透明地表达出一种完善的哲学。
明亮,没有目的,无常,就像自然。
像万物一样是眼睛的朋友,
它们就是它们所是的东西
带着匀称而无形的精确性,
谁也不能,就连放飞它们的孩子,
也不能假装它们会比看上去更有含意。
有些东西在明亮的空气中几乎不能看见。
就像微风,它经过并且显然触摸了花朵
我们也知道它在经过
那只是因为有些东西是用空气运送给我们
它更加透明地容纳了万物。
26.
有时,在完美的明亮的日子,
当事物获得它们能够获得的全部现实性,
我停下来问自己
为什么我把美
归因于事物。
难道一朵花会想方设法拥有美丽?
难道美丽会想方设法把美丽赋予果实?
不:它们拥有色彩和形状
还有存在,仅此而已。
美是一种并不存在的东西的名字
是我把美给了事物,用来交换它们给予我的欣悦。
它什么也不象征,
那么为何我还要说这些事物:它们是美的?
是的,纵然是我,只和生存活在一起,
也一样卷入人们对于事物的谎言
对于简朴地存在的事物。
变成自身,除了可见的什么也不去看,是多么困难!
30.
他们就想让我有个神秘主义,好吧,我有一个。
我是玄妙的,但只限于我的身体。
我的灵魂是单纯的,从不思考。
我的神秘主义不是指望去了解。
是为了去生活而不是去思考它。
我不知自然何物:我歌颂她。
我住在山顶
在一间孤零零石灰刷白的屋里,
这是我的限定。
44.
夜里我突然醒来
我的钟表正在占据整个黑夜。
我无法感受户外的自然。
我的屋子是一件围着模糊的白墙的黑色的东西。
在外边,唯有寂静,仿佛什么也不存在。
唯有钟表继续咔哒作响。
这个放在我桌上的嵌齿轮的小东西
窒息了大地和天空的全部存在。
为了思考它象征着什么,我几乎丧失了自我。
但我稍作停顿,便感觉到我自己在暗夜中
挂在嘴角的微笑,
因为我的钟表 当它用它的渺小填满了巨大的夜
它所象征或意味的唯一事物
就是那填满了巨大的夜的奇异的知觉
用它的渺小……
47.
一个狂暴又晴朗的日子,
是那种你希望你已经干完了一大堆工作
在那天什么也不用干的日子,
我看见,像前边林中的一条路,
那也许是个大神秘的东西,
那假诗人空谈过的伟大奥秘。
我看见没有自然,
自然并不存在,
唯有群山,峡谷,旷原,
唯有树木,花朵,青草,
唯有小溪和石头,
但没有一个统领这一切的整体,
以至任何真正的联系,
只是我们理念的一种疾病。
自然只是部分,而整体并不存在。
也许这才是他们念叨的神秘。
我认清了,这个没有思想
甚至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的东西,它一定是真理,
大家动身去寻找却没有找到,
我独自一人,因为不想去找,找到了。
49.
我让自己呆在屋里,关上窗户。
他们带来灯,向我道过晚安。
我也用满意的声音向他们道晚安。
哦 我的生活也许应该就是如此:
日子充满了太阳,温情的雨,
末日似乎降临时还会有暴风骤雨,
夜色温柔,人群走过,
好奇地从窗口张望,
最后的友善的一瞥落在寂静的树木上,
然后,关窗,点灯,
什么也不读,什么也不想,也不睡,
而是去感受生命溢过我恰如小溪漫过河床,
而在外边,巨大的寂静就像一个熟睡的神。
(杨子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