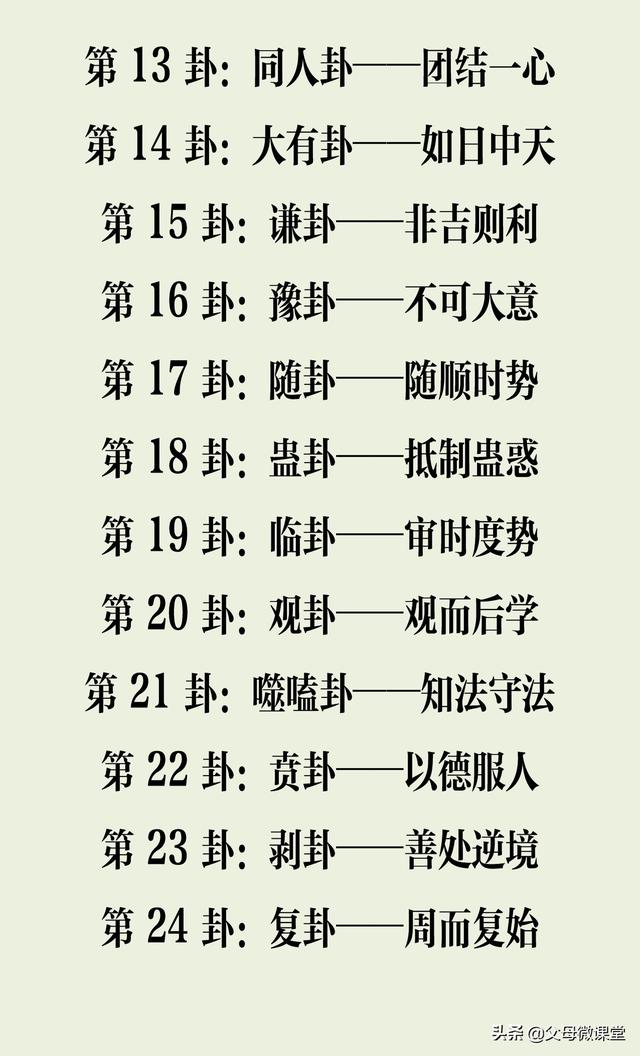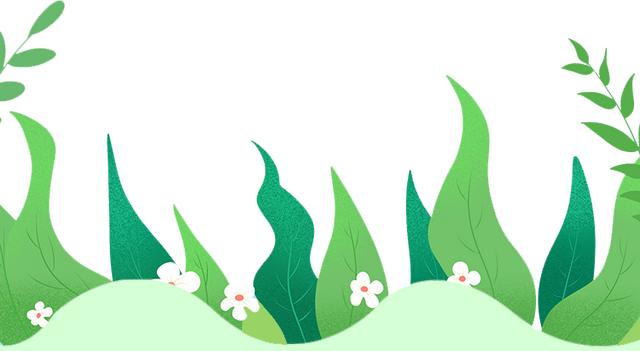在文学史中,他属于那种最熟悉的陌生人:
但凡念过几句书的,谁不知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征战人未还”?
谁不知道“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谁不知道“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他的诗,既有被评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出塞》所满载的雄浑大气象,又有“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使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的无尽闺怨,更有深受楚风越俗影响兼具民歌风情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外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无论何格调,一出,均传唱千载。
他,就是几乎天下无人不识的“诗家夫子”王昌龄。

一生行状厘不清
这样一位大才子,诗词我们熟悉,但其一生行状却存在各种是耶非耶的疑问。
我们只知王昌龄,字少伯,约生于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约卒于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旧唐书》中,有关他的记载不过寥寥51字,《新唐书》为98字,均语焉不详。如有关他的籍贯,《新唐书》说他是江宁人,《旧唐书》说是京兆万年人,《唐才子传》又道是太原人。又比如他的流放之地“龙标”的具体位置,一说是湖南黔阳,一说是贵州隆里(锦屏)。关于两次被贬谪的罪状,只以“不护细行”四字含糊带过,甚至连遇害地点,也存在两种争议:有人说他死于濠州,也有人说他死于亳州。
诸多疑云且抛一边,我们只道他是正史里无足重轻的寻常官吏,是大唐盛世里郁郁不得志的才子之一,更是乱世里草芥般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已。
王昌龄生平既缺详尽记载,大致只可知其早岁贫寒,渔耕而读。他的《题灞池二首》其二说:“开门望长川,薄暮见渔者。借问白头翁,垂钓几年也。”后奔走干谒多年以求仕进,足迹遍河南河北,又往陇右,沿黄河游历兰州、凉州、甘州一带,再达甘肃玉门关,甚至有学者推测曾抵碎叶城。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他边塞求功未成,但“高高秋月照长城”、“青海长云暗雪山”的苍凉景致造就了他的诗名。是时,中国版图空前壮大,强烈的自豪感与自信心遮天蔽日,正所谓大漠边关事,千秋万岁名,这使“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是如此理所当然。
王昌龄同样心怀抱负,执着功名,这些在其边塞诗中均有体现。同时,字里行间又有种大悲悯,落笔更有历史的厚重感,与他“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不无关系,他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全面而客观地思考战争。
后登进士第,两《唐书》本传都未载其登进士第时间,徐松《登科记考》也未载。《唐才子传》说他为开元十五年的(727年)进士,与诗人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里所言一致。此时王昌龄约37岁。进士及第后,补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自古由文学之士充任,为当世所重,至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入选博学宏词科,超绝群伦,于是改任汜水县尉,这大约是他生平最为快意的一段日子。
其间,孟浩然进京,二人交往甚欢,“数年同笔砚”,同时还与王维、王缙、裴迪、储光羲等联唱迭和,名动一时。

才如江海命如丝
花无百日好,人无千日红。
好景不长,开元二十五年(737)王昌龄便遭贬岭南,《听流人水调子》里他信笔写下“岭色千重万重雨,断弦收与泪痕深”,道尽当时心境。有说他是因为同情张九龄罢相而著文惹祸,此论成立与否尚待考证,但王昌龄的个性正如其自云“得罪由己招,本性易然诺”,不宜于官场却是无疑。
开元二十七年(739)获朝廷大赦,他由岭南北返长安,游襄阳重访挚友孟浩然,“时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二”(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或许,因为他们都沾不上这盛世的荣光,惟有以杯中酒一浇块垒,孟浩然亦可谓舍命陪君子。沈德潜曾在《唐诗别裁集》里评孟诗:“语淡而味终不薄。”
其实,王孟二人的情谊,也正合此语。由至情至性如孟浩然,颇可想见其友王昌龄为人。
开元二十八年(740),王昌龄离京赴江宁丞任,岑参在《送王大昌龄赴江宁》里感慨“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经东都洛阳时,李颀、綦毋潜等追饯至白马寺惜别,李颀有诗云“叹息此离别,悠悠江海行”。

王昌龄一生仕途多坎坷,所幸拥有很多朋友,他现存近200首诗作里,送别诗就占据四分之一的篇幅。李白、孟浩然、王之涣、岑参……纵然“谤议沸腾”,却有相互间的肝胆相照,朋友们的诗文唱合给了他几许暖意。
古往今来,做官总以在天子脚下为重,传统士人们眼中远离政治中心无异于被放逐在主流社会之外。王昌龄明显对江宁丞这一人微言轻的职务并不满意,常作牢骚语,如《送韦十二兵曹》诗中抱怨:“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平明趋郡府,不得展故人。”他希冀自己不会在江宁任上久留,“不应百尺松,空老钟山霭”。
性格决定命运,如他这般不拘小节,江宁任内已被人罗列出两大罪状:一曰“好酒贪杯”。从长安赴江宁任所,他在洛阳一住半年,其原因无非是“薄宦忘机栝,醉来即淹留”,其送别诗中,留下了自己饮酒必醉的数十处描写。县丞为全县之总管,既要处理公务要案,岂能因酒误事?二曰“不守本职”。开元二十八年冬日接调令,二十九年夏日才离洛阳南下江宁任所,这一年实际在任时间不足半年。
任职一年多后,又于天宝二载春离职上京,直至天宝三载冬日才始返江宁。回江宁后,又曾去太湖、浙江一带游览。这种明显以怠工作为消极反抗的手段,过于意气用事也实在太容易授人以柄。
不出几年,便再次被贬龙标,李白为此写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相送:“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一个人的失意,成就了另一首千古传颂的诗歌。
关于时人谓其“不护细行”、“不矜小节”,平心而论,唐人多有此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亦谓唐人轻狂,不护细行、不矜小节的绝非王昌龄一人,偏他却因此频遭贬谪。他出身孤寒,在承南北朝旧俗、极重家世门阀的唐代,全无靠山可言,却又有着“卷舒形性表,脱略贤哲议”的不羁个性,难免为人诟病。
王昌龄不同于他的挚友孟浩然,即使大半辈子都只是被支来使去的芝麻官,他始终期待着“黄鹤青云当一举,明珠吐著报君恩”,“明祠灵响期昭应,天泽俱从此路还”,虽也写下出世的虚无句子,却从未真正有过出世之心。

孟浩然尚有另一方净土安顿他的人生,王昌龄却无处可逃,只有不断的企盼与落空,再企盼与再落空,他的宫怨诗里,以男子写闺情,实则处处都有自己的影子。曾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般血性文字的诗人,如今吟咏着“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的一片闲适里,始终有份化解不了的苦涩,那些栏杆拍遍、拔剑击柱的壮怀激烈,只能被岁月煎熬成茫然无奈的长长叹息。
然而,对节义操守的信奉,对功业理想的执着,在磨折他灵魂的同时,也支撑着他的灵魂。这一生,说不尽的长亭短亭多少次折柳相送,他却少有消沉颓丧之语。送柴侍御那日,挥毫写下“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乐观旷达一如多年前那以边塞诗惊艳文坛的青年才俊。
在龙标,王昌龄也是一个颇有政绩的地方官,《黔阳县志》记载他洞悉民情,为官清廉,为政以宽,因此被老百姓赞颂道“龙标入城而鳞起,沅潕夹流而镜清”。
可惜的是,他的济志之志,他的冰心玉壶,再也等不到“鸿恩共待春江涨”,随着李三郎的开元盛世零落成泥,一切都成为了泡影。

天宝末年,安史乱起,两京沦陷,渔阳鼙鼓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唐玄宗避于蜀地,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
肃宗即位灵武后,大赦天下,此时,曾经为“一时之秀”的王昌龄已经垂垂老矣。
66岁的他,在兵荒马乱里选择离开龙标,后世曾多方揣测他的用意,有说是去投奔永王,因为好友李白在那里,也有说是省亲,又或许他只是走向冥冥中的结局,也许在濠州,也许在亳州,被拥兵自重的刺史闾丘晓所杀,一如捏死一只蚂蚁般随意。
“才如江海命如丝”,陈独秀的这句诗,足以概括王昌龄悲剧的一生。

诗文千载亦清晖
关于他的死,《新唐书•文艺传》里如是记载:“(王昌龄)不护细行,贬龙标尉。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张镐按军河南,兵大集,晓最后期,将戮之,辞曰:‘有亲,乞贷余命。’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晓默然。”张镐所言正道出时人不平之意。闾丘晓究竟为何事杀他,凭什么杀他?始终是无头公案,由生至死,王昌龄仿佛都由无数谜团组成,只有他的诗句,清澈优美,在粗粝荒凉的命运里闪烁珠玉般的光泽。
正史中,对这落魄才子吝啬笔墨,但散落的野史和笔记中,却有不少关于他的记载,颇能访其足迹,窥其性情。譬如左迁龙标尉时,就有“苍头拾叶供爨”、“峒蛮遮道乞诗”、“蛮女隔岸听歌”、“花联苗汉”、“琴书自随”、“江楼送客”等。龙标在唐时甚僻,属于蛮荒的五溪地区。龙标尉日子过得清贫却也清闲,常自己背着书和琴在青山绿水间散心,让跟随的老仆人沿路捡拾落叶枯枝回去当柴烧。而那座小小的芙蓉楼,承载了太多后人无法忘怀的佳句,他的才情倾倒过酋长美丽的女儿,化解过苗汉间的纠纷。而最著名的,莫过于薛用弱《集异记》里绘声绘色描述的旗亭画壁故事。

话说玄宗开元年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这三位诗名正盛却同样郁郁不得志的朋友,某日于酒楼小饮,恰逢天寒微雪,有宫中乐官率众梨园子弟前来宴饮,其后更有四位绝色歌妓相继而至,选奏的均为当时名曲。三人于角落里听得兴起,遂约定以各自诗作入歌最多来分个高低胜负。虽然故事最后峰回路转,以王之涣胜出结束,然而入歌最多的,始终为王昌龄的诗作。
后人传奇杂剧中多以此事为题材,但明胡应麟《庄岳委谈•笔丛》卷四十一便力言其诬妄,近人汪辟疆也认为此事不足信。然三人结交却是史实,只是与王昌龄同样出身贫寒的高适后来官至淮南、剑南西川节度使,任散骑常侍,并被封渤海县侯,而原本便为太原望族的王之涣虽仕途不显,亦得以死于安乐。其中只有王昌龄,逾耳顺之年仍不得善终。

不得善终并深受谤议的王昌龄,在文学上的成就却无人能够否认。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曾道:“七言绝句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李白天才英丽,气挟风雷,自是盛唐诗坛上的喷薄红日,而王昌龄其人其文,则如寂寂寒江明月心,千载之下亦难掩清晖。
王昌龄近20年的贬谪生涯,对个人固然是种磨难,然诗家不幸文章幸,其间所写下的大量诗歌为他树立了一座文字碑。更为难得的是,即使现实逼仄,理想无从触及,种种痛苦求索并没有异化他的独立人格,他始终未失雄杰之气,字里行间充溢着盛唐之音,充溢着清刚劲健之美,同时代的诗坛视他为体现“风骨”的代表,并推许他是东晋以后400年内振起颓势的“中兴高作”。
《唐诗纪事》亦云:“晚节谤议沸腾,言行相背,及沦落窜谪,竟未减才名,固知善毁者不能毁西施之美也。”
一句“善毁者不能毁西施之美”,王昌龄若泉下有知,定当含笑举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