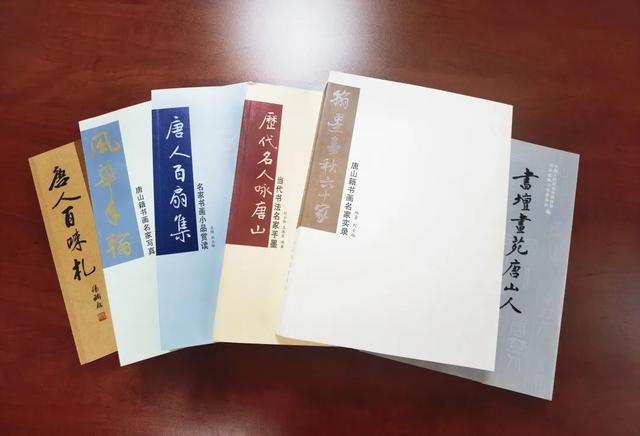杨家堂,书画上的家园
鲁晓敏
清朝咸丰二年的一天,一个叫宋斤的人背着手在杨家堂一户宅院中来回踱步,过了许久,宋斤爬上梯子,提起饱蘸浓墨的毛笔,举笔向墙,只见他轻抖腕力,一排轻盈的行书落在了白粉墙上:“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才……”
宋斤写的相当轻巧,露出几许得意,跳着几分惊艳,或许在今后的日子里,让他重新再抄写百遍,再不见得可以重现眼前的经典。
宋斤只是杨家堂一个普通的壁书者,类似这样的壁书杨家堂还有二十多处。假如我能够摆渡到清末的杨家堂,说不定就在哪片白粉墙上遇见一个或者数个杨凝式一样的书家,他们将杨家堂的白墙当做一张硕大的白纸,行书,草书,隶书,各种书体纵情挥洒,俊逸、雄健、流美、沉郁的思笔在眼前铺排,他们的心境以书法的方式进入了公共阅读的视野。我不懂书法,但是读懂了他们的情趣,他们在抒发性灵,一笔一趣,一书一境,举重若轻,原本是很压抑的字意在他们的化解下变得空灵轻巧。茂密的行数也不觉得拥挤,显现出众多乡野村夫的文笔驾驭能力,也显现出一派天成的真性情。一两百年后,粉已不白,一些字迹已经不清晰,仿佛氤氲的水雾从墙体上升起,浮起一朵朵饱满的祥云,满墙的墨书幻化出山隐水迢的风景。
人和古建筑之间,体验的不仅仅是物理空间,更是风雅神韵。在我看来,杨家堂倘若少了文化的神韵,纵使雕栏玉砌,纵使雕梁画栋,也缺少了品位。然而,杨家堂恰恰是一个既有华堂高屋,又是一个文养极其深的地方,无论在村落的哪个角落似乎都散发着雍容文雅的气氛。拿今天的话来说这只是一些农民书画,即使那样又何妨,那也是相当韵趣的农民书画,从本质上并不亚于一些所谓的名家。在一些村落中,好些名家的字迹事实上是后人伪托,以彰显祖先的荣耀,杨家堂人抛开这些虚荣,没有名家力作,除了宋斤之外,只有各个时期族人留下的遗墨。宋氏族人将《宋氏宗谱.家训》、《朱子治家格言》、《孝经》、《孝悌力耕》、《诗经》、《论语》等经典词句及古训搬上墙面,那些隽永飘逸的字迹,仿佛书家刚刚落笔,一转眼,书家已然骑上一匹瘦弱的毛驴穿巷而去,空留无数遐想。宋氏先祖有着长远的教育规划,以大音稀声的文字天天告诫着村民,遵守三纲五常,应当循规蹈矩;遵守礼仪之道,应当敬师重道……这是一场漫长的教化过程,像一条清澈的溪流滋养着后人,“仁、义、礼、智、信”渗透到了宋氏宗族子弟的心里。

4号大屋结构精致,进入外门,穿过一条狭长的通道,一转折,进入里大门,三合院,三开间,两厢房,天井宽敞,天井中铺设着“三连钱”的鹅卵石图纹,钱眼中镶嵌着佛教的万字纹,左右两只兰花石凳上摆满了盎然开放的小花。门墙上除了书法之外还密布彩绘,右侧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棋盘上似乎还弥漫着腾腾杀气,下棋者早已拂袖而去。让人猜测下棋者是谁?为何留下一盘残局。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没有对手的棋局?人的对手往往是自己,只有在迷局中顿悟,才能够走出乱局。与棋局对应的只有一棵挺拔的松树,配上贾岛的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又是一处此处无声胜有声的画面,谜底被主人抽走,只留下了一些无端的猜测。左侧壁画更有意思,孤零零的琴案上摆放着一把琴,琴头露在琴套外。空空荡荡的画面,又留下了一出哑谜,弹琴者是谁?听琴者又是谁?这是一出模拟而来的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门外就是高山流水,“叮叮咚咚”的水流声响彻于耳,难道说房子的主人在期待着知音的到来?其实,这个孤傲的主人或许是才华横溢的隐者,他以琴棋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处世观。一面门墙,“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体现的不仅仅是装饰作用,更有主人的理想和述求,表达的境界远远超过了现实寓意,让人惊叹古人浑圆的心智。
远眺杨家堂,一垛垛毗连的白墙,仿佛开放在田野中的一朵朵百合花,独立于烟雨中;檐瓦高佻轻盈,仿佛一对对舒展的翅膀,似乎在一声吆喝下便“噗啦啦”地振翅飞走。在众多的大屋中,6号大屋最为显眼,兀立于半山腰,几丈高的蛮石砌出一块平整的突出部,整座大屋如同骑在危岩之上。大屋为当地典型的三合院,左右两厢,中间有二层木楼。当年满墙的学报尚依稀可辨,就像贴着永恒的笑脸。天井长方形,鹅卵石铺砌的金钱状图案,蕴含“金钱铺地”之意。墙上十余幅以耕读渔樵、二十四孝为主题的壁画,使得大屋充满了文化气息。与壁书并列的壁画,在祠堂、民居的墙体、大门上保留着大量精美的彩色或者黑白的吉祥图案:一对活灵活现的狮子,寓意着事事如意,母狮子伸出舌头舔小狮子,寓意着“舔犊之情”;有口衔灵芝的神鹿,代表着“禄”;还有丹凤朝阳、有福星高照、有喜鹊登梅等等,它们组成了古人心目中最理想、和谐的生活场景,使得整座老宅呈现出一派惟美的意境。

它们仅仅是装饰吗?显然不是,儒家经典旗帜鲜明地占据在理论高地,指导着宋氏后人为人处事。在村落中,每一幅独立的书画都形成了呼应,它们相互依赖,相互延续,组合成繁缛的艺术布局。一幢幢新建的大屋,将那些繁缛继续交叠着,不断繁衍,诞生出更多更壮观的书画,形成了一则久远的记忆。
宋氏族人世代尊崇礼仪,他们对文化的敬畏呈现在公共视线中,也隐藏在一些细枝末节中,壁上的书画、大屋的木雕组成了杨家堂村一道突出的文化风景,难道这只是家族为了强化封建教化的一个举措?或者说这是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法宝?我对杨家堂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在史料中找到答案。
村民主任宋荣华将一叠烟黄的《京兆宋氏宗谱》摆在我面前,我看到了一张宋濂画像,难道说明代大儒宋濂是杨家堂宋姓祖先为吗?事实果真如此。宋濂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宋濂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与刘基、章溢、叶琛并称“浙东四杰”,更兼有太子朱标老师的荣耀,主持了《元史》的修撰,四方学者称之为“太史公”。胡惟庸案发,在这场死亡三万余人的血腥大屠杀中,即使宋濂这样的人物也没有逃脱朱元璋的迫害,孙子宋慎被杀,71岁的宋濂被流放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宋濂子孙为躲避牵连,从浦江纷纷迁居各地,其中一个孙子宋可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避居松阳呈回村,他隐瞒了显赫的身份,以一个逃难者的身份融入到普通的百姓中。即使今天我们乘坐小车到浦江也要两个多小时,对于当时来说,宋可三和家人揣着重重心事,翻越一重重山岭到达幽闭的呈回村,他们的迁徙困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顺治初年,呈回宋氏第八代裔孙宋显昆偶然的因素来到了杨家堂,只见林木阴翳,山势崎岖,这是一幅让人叹谓的奇景,此处真不愧为古之盤谷。他在山腰上,生起篝火取暖,度过了一个夜晚。几天后,他又一次回到原地,发现烟火还未熄灭,于是认定这是一处宝地。他在山腰上开荒拓地,伐木筑屋,位置就在今天的宋氏宗祠。经过几年的演变,谷地里升起了一缕缕炊烟,几幢房屋奇迹般地在山腰上崛起。尽管生活相当艰辛,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人,晴耕雨读,一个家族的读书风气从他身上开始延续和流传。《宋氏宗谱·家训》记载:“勤宜及时,俭贵适中。勤俭者兴家事业之要务也。故士勤读,则功名必成。农勤耕,则衣食必丰。工勤艺,则技术必精。商勤业,则资财必裕。自来祖业兴盛,均起于勤俭。子孙贫贱,则败于怠惰者,往往然也。” 宋显昆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宋氏后人谨遵家规,勤俭持家,耕读传家,一直到清中期以后,他们从经营木材中开始发迹,兼制筑墙工具,到晚清出现了一支建筑队伍,四处筑墙垒屋。宋显昆没有想到,他的后人中殷富者迭出,就在他当年刈茅结庐的山坡上,建起了层层叠叠的房屋。今天的杨家堂尚有三百多人口,90%以上为宋姓,成为一个世代聚族而居的宗族村落。

宋濂的后人已经从历史的险境中摆脱出来,时间足以磨平他们心中的任何棱角,仿佛险象环生的历史只是他们祖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平静的生活没有一丝波澜。他们虽然有着贵族血统,已然没有了贵族的傲气,背起锄头是农民,捉起毛笔是文人,走出家门是商人。在山水的陶冶下,他们将田园风光诗歌题写在白粉墙上,出门是山水,看不厌的山水又被他们搬到了门墙上,处处风光旖旎,处处古意盎然,处处诗性勃发,表达了他们热爱山水,热爱生活,对家园的眷恋,对生活的向往,处处流露出归隐耕读的价值观。
杨家堂坐落在斜坡之上,整个村落上下屋高低落差约二至三米,伸展高层两百余米。杨家堂的村道随着坡度一级级向上延伸,弯弯曲曲,深入浅出,尽是由布满石英成分的块石随性地铺就着,杂乱却有章法,没有纹路,却体现出石头的天性。道路中间的块石稍大,两侧稍小,中间微微拱起,两侧平缓,这样就解决的雨天道路积水问题,保持路面的美观。墙基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苔,从石子缝隙中伸出细碎的小草,多少有些曲径通幽的意思。道路将整个村子连接起来,三条横向的主干道,两侧纵向小径,同样是块石铺就,显得秩序井然。鹅卵石铺就的各色图案在民居的天井和小院中开放,与道路块石的粗糙不一样,这里呈现出石头圆滑的一面。
跟着宋荣华的脚步,穿越了环形的山凹,走过二十多幢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国大屋。这些建筑无论是门屏户牖还是牛腿雀替上的雕饰都比较华丽,多为仙人、鸟兽、虫草等吉祥花纹。天井则用不规则的卵石拼成各种图案,如卷草纹、铜钱纹、八卦图。门墙简直就是一页页诗抄,有的是家训,有的则是诗文,裹藏不住淡淡的墨香,比如二号房墙上录的就是乾隆的七言诗。它就是这么一个有文化的古村落,我们在走过每一幢大屋的同时,如同浏览艺术殿堂。不知不觉中,我们进入了村落正中心的宋氏宗祠。村落所有的建筑在它前后左右拱卫着,突显出它的尊贵。
宗祠始建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民国十三年重修(1924),这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建筑,不大,两进三开间。宗祠的建筑工艺也非常精湛,从高大的墙体到细微如毛发的微雕,无一不显露出宋氏子孙对祖宗的崇仰和膜拜。明间壁龛上绘有彩画,一个身着宋代官服的大员,村里人也说不清究竟是哪位先祖。八字门墙上照样有壁画,他们几乎不放过任何一处可以描绘的空壁,一处处山水画将我们带到古人的心灵深处,这是他们的田园,不断地重复着隐逸、耕读的故事。墙头上照样布满了蝇头小字,书家沉浸在兴奋的心绪当中,浓淡顿错的字迹间跳跃着盎然意趣,时隔两百多年,读来依旧荡气回肠。四扇大门上绘着流金溢彩的文武四门神,文官是福禄双星,儒雅谦和;武官为秦琼和尉迟恭,怒目圆睁。这应该是我在松阳县看到最精美的门神,画师将古典人物画得栩栩如生,推开大门的那一瞬间,似乎也能将他们从画面中推下来。
一座村落的文化,与生活在那里的人息息相关。杨家堂人并没有辜负文化的恩泽,作为传统文化的映照,杨家堂的教育极为出彩,这个仅有三百余人的小山村,成为松阳近百年来教育最成功的村落。杨家堂村建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经过近两百年的教育积累,从清道光年间开始发力,涌现了三十多个国学生和邑庠生。《京兆宋氏族谱》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村里创办了“迪德”学堂,是松阳县创办最早的小学之一。庚子之乱后,中国遭受了空前的屈辱,中国自强的梦想就在小山村的这座破败学堂点燃。从这里走出的教授级别人员以及副厅以上的干部有46人,其中博士导师、博士就有4人。如今学堂整修一新,古旧感掩饰在白粉墙下,让人对它的历史产生了疑惑。进入学堂,当年的学子大多仙逝,他们的影像事迹挂满了四周墙壁,成了杨家堂黄金时段的记忆。

杨家堂6号大屋被称为教授之家,这个家庭占据了松阳近代教育史的致高点,从宋微封开始,一门五代人中,从教、从医、从政者多达二十余人,子孙满门,个个学有所成,业有所就。长子宋昌几曾在浙江大学任教,1950年任铁道科学院副研究员;次子宋昌存担任浙江医科院寄生虫病研究所长、教授、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兼任世界卫生组织蠕虫病研究合作中心主任,有多部学术著作面世,成为寄生虫病领域权威人物,1992年获国务院突出贡献表彰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三子宋昌中曾在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任教,译有近百万字的文学著作,成为著名的俄文翻译家;女儿宋淑持曾任上海教育出版社副编审;孙子宋康担任浙江省中医院院长一职。杨家堂另有宋氏后裔在外交部担任外交官员,以及在兰州大学等学院担任教授,可以说,杨家堂走出来的专家、学者、教授在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穿行在杨家堂华堂大屋之间,那么多的典故无从释读,我像无力的脚夫挑起数百斤重担,吃力地行走着。2013年,杨家堂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让我很难将这个普通的村名与深厚文化底蕴的村落对接在一起,这让我满心诧异。一些古村落名字非常吸引人,但是深入到村落肌理,往往会产生巨大的落差。一些古村落的村名看似平淡无奇,却潜伏着大境界。杨家堂恰恰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一代代村人守着这三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汉字,他们就没有动过一丝修改村名的念头吗?或许,杨家堂人不在乎什么响亮的村名,他们将精力倾注在自我修炼上,在乎的是文化累积,只有文化才是村落真正的灵魂。即使拥有一个非凡的名字,但是缺少文化内涵,那也只是语境上的虚境。
壁书,壁画,木雕,历史掌故,名人典故,传统民俗,绵延数百年的教育史……杨家堂人进行着一场漫长而深情的文化表达。此刻,杨家堂从简单的汉语词境中彻底剥离出来,它是那么地优雅至尊,那么地惊艳靓丽,甚至在空气中弥漫着远古的芳香。
本文为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阅后请赐金玉良言哦!栏目自荐、推荐邮箱:2085712893@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