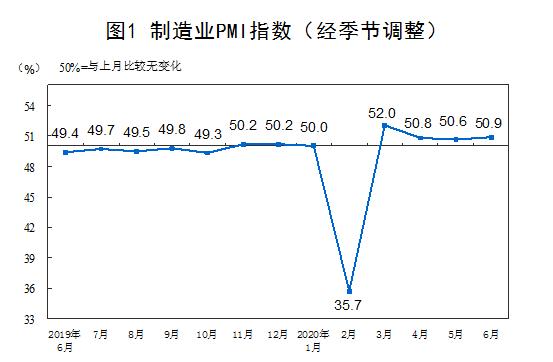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记者陈一帆 张宇琪 金一清)盲人走盲道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们会遇到哪些障碍?又有着怎样的期盼?新华社记者日前在多地城市的街头,分别跟随3位盲人体验盲道,倾听他们的真实感受。
“盲道设施日益完善,赞!”
早上6点上班,晚上10点或11点下班,手持一根盲杖,“笃笃”“嗒嗒”地敲击着地面……这差不多是穆怀鹏每天的生活节奏。
今年43岁的穆怀鹏在天津经营着一家中医推拿馆。他从16岁开始学做推拿,至今已有20多年。2012年他参演了娄烨的电影《推拿》,成为走上柏林电影节红毯的盲人演员。

工作之余,穆怀鹏沿着盲道散步。新华社记者 张宇琪 摄
穆怀鹏习惯先叫一辆网约车,坐到家附近的地铁站,智能手机的视障模式帮助他完成这项在别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到了地铁口,他直接选择坐下行扶梯进入地铁站,“踏到扶梯的金属踏板后,再往前迈两小步就行。”说话间,他的双脚已稳稳踏上扶梯台阶,悠悠下行。
台阶尽头是金属盲道,穆怀鹏盲杖的尖端顺利捕捉到道路的指引,“这盲道对于盲人朋友可太重要了”,但过了安检后,脚下的盲道没了,“有的地铁站安检没有设置在盲道路线上,刚开始走时有点不方便,但走得多也就习惯了。”
和往常一样,这时总会有地铁站工作人员笑盈盈地迎上来帮忙。“工作人员基本上都认识我,有他们领着我更方便。”穆怀鹏说。
“走完这条不到500米的路,历经重重艰险”
日益完善的盲道设施为盲人出行提供了便利,但一些“不友好”的盲道,却让盲人出行“步步惊心”。
斯勇是西部地区某市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音乐老师。临近饭点,他需要走出学校到附近餐馆就餐。这条不到500米的路,斯勇花了一个多月才适应。
“每天盲道的情况都有新变化,盲杖就是我的雷达。”斯勇说,学校门前马路的红绿灯没有语音提示,他只能凭经验快速走过这条四车道的马路,“通常都是靠耳朵听,如果有车来,就慢一点走,有时会有热心路人帮忙。”而过了马路,真正的“旅程”才刚开始。
刚踏上盲道,斯勇身旁就有一个绿化树木被挖掉后形成的大坑,前方一处突起的井盖覆盖了一半盲道,而斯勇只能用盲杖去探测这些障碍物。“全凭我的经验去猜测大概是什么东西,心里有数才不会被绊倒。最难的是商铺前的电瓶车充电线,这个很难探测到,容易被绊倒。”斯勇说。

斯勇在路上行走,盲道旁边有一个绿化树木被挖掉后形成的大坑。新华社记者 金一清 摄
横在盲道上的私家车和工程车,同样让斯勇感到忧心。一不留神,他的头就很容易撞到工程车的车尾,而遇到完全占领盲道的私家车,他的做法是用盲杖探测后,绕着圈越过这个“庞然大物”。
没走多远,一个光缆交接箱立在盲道上,斯勇用盲杖一点一点去探,绕了过去,但没想到破碎的盲道砖块又差点让他崴了脚。斯勇很无奈,“每天要历经重重艰险,才能到达餐馆。”
“宁可用盲杖行走慢车道,也不愿走盲道”
盲道受阻,同样困扰着盲人陶进。
在广西南宁市,陶进从家里到上班的推拿馆,需要横跨一条马路,转一班公交车,一共有8站。这条路陶进走了许多年,即便熟记在心,有时还会感到不放心。
下车后需要穿过人流密集的路段,对陶进而言是不小的挑战。“盲人最怕周围嘈杂,会影响判断。”陶进说,这时盲道尤其重要。他不停地用盲杖在地上左右敲击,判断前方是否有障碍物。“横空出世”的电线杆、垃圾箱……很多时候他不得不绕道而行,但不时驶来的电动车,又让他避之不及。

陶进走在一条被挤占的盲道上。新华社记者 陈一帆 摄
陶进说,盲道被占用很普遍,更可怕的是“陷阱”。走到一个路口,他突然停了下来,用盲杖敲击试探,“这个地方,应该有个石墩,前两天我就撞到了。”他撩开裤腿,只见小腿上有好几个淤青和伤口,这些防不胜防的障碍物让他心有余悸,“更别提那些临时的施工工地给盲人带来的威胁。”
陶进感慨,“很多时候,我们宁可用盲杖敲击马路牙子在不安全的慢车道上行走,也不愿意走那些磕磕碰碰的盲道。”
多年来,陶进一直呼吁各方重视盲道建设的问题。他说,盲道是盲人出行的“眼睛”,一旦被占用或破损就会给盲人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希望有关部门能多倾听盲人群体的心声,加大维护和执法力度,让我们脚下的路越来越通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