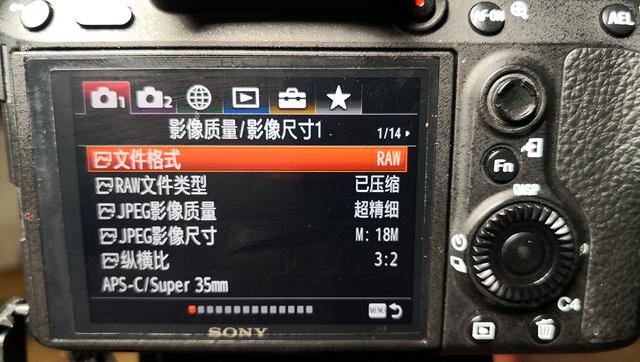追求财富自古以来都是人之天性。
不管朝代如何变迁,货币形式如何变化,人们对她的爱从未改变。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老子提倡“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孔子追求“以其道得之”财富的原则。
但司马迁把这个“道”做了自己的注解,那些“长贫贱,好语仁义”而不事劳作的处士更被贬为“足羞”。
我们还能看到其经济式的人文关怀,“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他强调共赢。
理解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形成离不开其生活的经历,也离不开前哲丰富的经济思想的滋养。
一 、司马迁认识的经济运行规律西汉初年,在连年的战争之后,土地等社会财富得到了重新的整合,以小土地所有者为主体的自耕农的比率很大。
随着社会的安定和国家各项推动经济发展政策的推出,社会财富在不断的增长,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也进行之中。
但不管其是富商大贾兼并之家还是自耕农甚至是佃农,他们都是财产的私有者,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
每个人,或者是每个家庭,有独立的决定的权力,虽然这样的权力受到这样那样的制约,如天然的、技术的、财力的、政治的等。
但这些人或家庭都在已有的制约下寻求着最大利益或者最优选择。人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或者人人都在追求财富,这种对私有制的肯定与保护,充分发挥了人们的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私有制的发展,还有自战国以来的商品经济的活跃以及前代治衰成败的社会实践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司马迁经济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
在《货殖列传》中他一开篇就竖起一个靶子,痛批老子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建立在寡欲、节欲基础上的乌托邦,他认为这是得不到人们认可的空想。
他肯定人欲,“人生而有欲”,“缘人情而制礼,以人性而作义,其所有来尚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
认为人对物质和富贵的追求是“终不能化”的,而且这种对物质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
中国疆域辽阔,各种物产分布在不同区域,并且不可能由单个人去生产自己所需的全部生产和生活资料,因此必须分工协作,才能“得所欲”。
人们由于生存和交换的需要自发形成了农虞工商四民的社会分工,司马迁引用《周书》来阐释四民的作用,“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并举齐国之例,说明分工能够使民“任其能,竭其力”,创造社会更多的物质财富,小则富家,大则富国。
专业化的分工也是致富的有效方式,司马迁在致富的案例中提到:
“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贾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濁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此处的“诚壹”其实就是专其业,通过强化发展自己的专业技能而实现致富的成功典型。
司马迁在这些论述中并没有否定人们对于财货的追求,也没有对财货的多寡造成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身份的不同进行苛责,而是认为这是“人欲”的天然性,是一种自然之理。
司马迁注意到了这个自然之理,故主张应因而导之。
另外他还论述了货币产生于农工交易之需以及货币作为等价物对经济运行的重要作用。
所有的这些经济规律,包括社会分工,供求关系以及价格的杠杆作用等都是不可违背的, 应该“因之”。
比如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重赋,就会导致经济倒退以致国家经济的衰败。
司马迁在《平准书》借卜式之口提出了对汉武帝行平准算缗之策的批评,“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贾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
司马迁上述富家兴邦的理论在文章中以范蠡、计然之策的形式做了明了的解说,表明他的赞成态度,而他的这些经济思想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有许多相近之处,无怪乎现代学者在解读其经济思想之时往往与“经济学之父”联系在一起做对比研究。
二、司马迁认为的求财之道“礼由人起。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故礼者养也”。
司马迁肯定人欲,但他对贪欲是批评的,认为是乱之源。
司马迁为商贾作传,总结治生之术,他肯定货殖,但他并不赞成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之重困”。
司马迁看到了汉武帝时代“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以及统治者“争于奢侈”用度无限度的现象,他对这种情况也是极其不满的。
司马迁基本上还是赞同君子求财“以其道得之”的,但司马迁对求财之 “道”还是有自己的发展,那些“长贫贱,好语仁义”而不事劳作的处岩之士则被斥为“足羞”,空言仁义在他看来是最羞耻的,强调求利的常态,这与孔子“罕言利”,形成鲜明的对比。
司马迁的“道”就是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求之,这个财产正义的标准就是“俱利”,而不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不管其从事何业,只要“俱利”,皆可为之。
司马迁在谈到范蠡、计然之策时有这样几句话,“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
十九年之中三致其金,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放到现在看来大概就是乐衷于慈善事业吧。
其在讲到为什么写《货殖列传》时,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劝导商人正正经经营业,只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不乱政,不害民。
这是司马迁对“逐利者”提出的要求,也是道德及规范政治的要求。
另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甚至提出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的命题,他从经济现象解释道德,并且从财富不等看到了社会关系中人的地位不等。
司马迁经济思想,来自于他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走向的深刻体会,他认为“货殖”的繁荣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其所呈现的特征反而处处和道德伦理上的态度相互呼应。
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意义不仅是看到经济运行的规律,也不仅是讲述人们如何致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人们面对财富应该有的“仁义”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不害于政,不妨百姓”。
可惜他的经济思想犹如昙花开在漫漫长夜,一瞬而逝,在长时间内被冷落,甚至遭到人们的排斥,而不显于世。
想其不显原因有三:
一则是因为其思想不符合统治者的要求;
二则是他的思想在农业为主,以农立国的时代难有市场;
三则是还有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的缺陷,就是没有明确的概念和由之构建的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