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的“行礼”也叫“坐席”,就是别人家办喜事,请你去吃喜酒。记忆中我第一次坐席好像是八九岁,或者十岁多?那时我们住在老城的一个大杂院,一个院子里住着八九户人家。那次是刘奶奶家娶媳妇,全院子的人家都被邀请了。那时候,只有生活条件好的人家,才可以这样大规模地邀请别人参加他们的喜宴。当时的礼钱好像是五块钱?记不太清了,反正差不多这个数字,但一家人就只上这么些礼钱,起码五六口人,都是要去吃饭的。
那时能坐席,是很开心的事,大人们对待此事也是很庄重的,能干活的女人们,提前就都去帮忙干活了。压粉条,削土豆,拣豆芽,捏油糕……每个人都满脸的喜气,一边聊着天,一边干着活,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这时候的小孩子们,也像过节一样兴奋,满院子跑着玩。
到了正式坐席那天中午,我们都穿上平时不舍得穿的好衣服,等待“安座”。因为宴席不像现在,都设在大饭店,而是设在家里,每个邻居家的炕都被占用做席座。但即使这样,也仍不能满足所有的客人同时安座,所以吃饭就需分批吃。第一批吃的,叫“头派”,第二批吃的是“二派”。吃头派的都是重要客人,比如娘舅家的亲戚、媒人。
席面上是八个凉菜,八个冷菜,或是六凉六热?但记得其中重要的一道菜是“扒肉条”,也就是红烧肉。其次还有一道是硬菜,是肉丸子,是最后上的,意味着菜上完了。
一桌十个人,当炕一个方桌,最重要的客人坐正面,其他人也各种按身份坐在该坐的位置上。每桌有一个人,负责分菜,每一道菜上来,她会用筷子分在每个人的碗里。一顿饭吃完,盘子全光了。扒肉条和丸子这样的重头菜,大家都不吃,拿回家去,给家里没坐席的公婆或父母吃。主食油糕,管饱吃。
不管怎么说,那时候坐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件很高兴的事,而且被邀请坐席也是件荣幸的事。这样的坐席,不仅可以改善生活,还增进了邻居间的友情。
再小型的坐席就是圆锁了。圆锁是不邀请邻居的,只请来姑姑舅舅婶婶姨姨们,一家子摆两桌,家里人自己做几道菜。炸油糕,凉拌绿豆芽、黄豆芽,大烩菜上面披着肥肥红红的猪肉片,真是香极了。一大家子热热闹闹一中午。
吃完饭,收拾利落,再端上茶,炒一盆瓜子,大家挤坐在炕上,说说笑笑。直到晚上,有的非要回去了,有的再留下吃晚饭。熬一大锅红豆稀粥,中午剩菜剩油糕热了,吃完了才散。
我圆锁时,姑姑姨姨们都是扯五尺花布作为贺礼。这五尺花布,正好给我做一件布衫。等吃完晚饭,亲戚们都散了以后,我和妈妈就拿出来那些花布欣赏,计划着该做什么样式的花布衫,非常的开心。那些布的花色我至今记得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坐席开始频繁起来的。结婚下请帖,圆锁下请帖,百岁下请帖,还有满月二婚开业下请帖的。曾经我们只被亲朋好友邀请,后来不怎么来往的同学下了请帖,同事下了请帖,邻居下了请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下了请帖……礼金由50到100,再到200,300,500,还有关系硬的礼钱要上1000、2000的。坐席的次数越来越多,由原来每年两三次,到每年八九次、十来次,甚至无数次。有时候,旺季来了,同一天会收到五六个请帖,于是只好一家一家挨着去送礼金,最后再选择其中一家去吃饭。
宴席早已不在家里设了,改在大饭店里。挤挤挨挨四五十桌,像农贸市场,不是谁踩了谁的脚,就是服务员把菜汤洒在谁的貂皮大衣上,吵吵闹闹。好容易见到一个二十年没见面的好朋友,想彼此谈谈心,但谁也听不见谁说什么,要么就得把对方耳朵拉过来大声喊几句,早已没了抒情的味道。罢了,不说了吧。许多坐在一个桌上的人都互相不认识,据说还发生过陌生人进来蹭饭吃的,反正谁也不认识,就连东家,也未必认识所有的人。
大家在震耳欲聋的婚庆公司的锣鼓声中,胡乱吃些批量生产出来的肥鱼大肉。等到东家过来敬酒时,多数人已经撤席走了,留下摞了一桌子的没怎么动过的饭菜。东家打包回去,够吃一年的剩饭。
或许是年龄大了?我觉得越来越怀念儿时的岁月,那时候虽然贫穷,可是快乐;虽然吃不上大鱼大肉,可“坐席”的滋味至今难忘,扒肉条的味道至今犹在。可惜现在再也吃不到那时的味道了。
不说了,早点睡吧,明天还有两个行礼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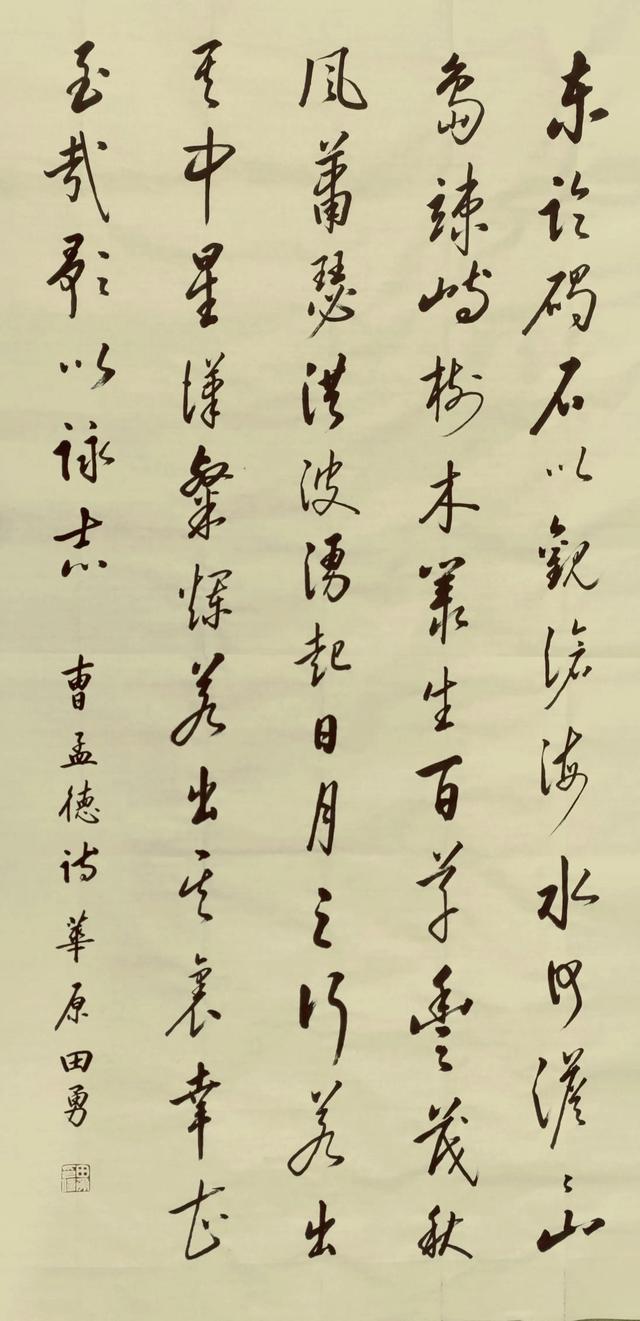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