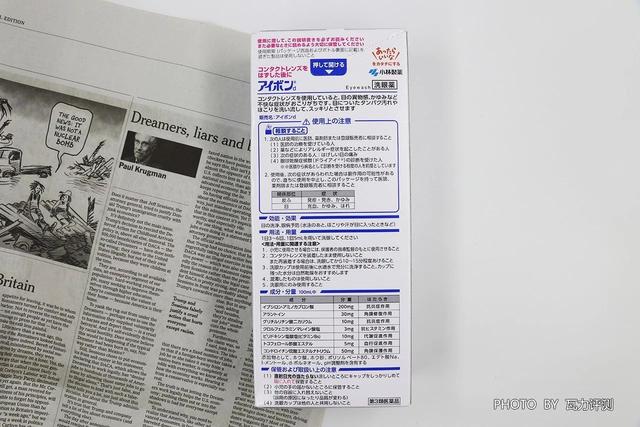文/直斋
话剧《惊梦》巡演第二次到杭州,10月7日晚这场结束时全场掌声如浪,大家被陈佩斯、刘天池、巫刚、何瑜一众大腕征服了。

“也说不出什么话了,我直接给陈佩斯磕一个吧。”有观众在社交平台说道。
陈佩斯浸淫喜剧一生,在我们熟悉的《吃面》《王爷与邮差》等作品中的经验似乎都用出来了,拿捏有度、不过火,同时意蕴深厚、张力十足。这部话剧巡演1年来,2400多豆瓣网友打出了9.4分的高分,值得一提的是,《茶馆》也是9.4分。

明暗两条线
话剧名《惊梦》对应了昆曲《牡丹亭》中《惊梦》一折,故事以昆曲戏班“和春社”的遭际为主线。
班主童孝璋带着戏班走江湖演出,刚进城碰到拉锯战,原先说好的酬劳、演出都没了,进退失据。这时,先占领城里的部队请他们唱戏,送来的粮食无异于雪中送炭,却没想到是一场见所未见、无处下手的戏《白毛女》。
一场戏翻来覆去演了两次,戏班人不知道这是个“赤色宣传”的戏,第一次大获成功,第二次却带来杀身之祸。与此同时,战乱中流离多年的戏班人,也开始考虑其他出路……《牡丹亭》没唱成,却见证了战争中一群人的生死离合。
除了主线,还有条暗线,那就是地主少爷常少坤的遭遇:得意-被打倒-得意-疯掉。战争之前,他是地主家少爷、留洋归来,一身西装革履,因为爱戏,邀请了“和春社”来唱昆曲。

城里被解放军占领后,经过土改,他成了衣衫褴褛的过街老鼠。等到国军又打回来,常少爷又重回大宅,当起了财主,穿上了绸缎。一场戏没唱完,又卷入了“赤色宣传”清算中,最终又一场战争后,家业消散,他又穿起褴褛衣衫,彻底成了疯子。
结尾疯了的常少爷让我想到《红楼梦》中空空道人,在大雪中给死去的人们招魂,“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他是故事中的人,又像独立于故事之外的旁观者。
编剧毓钺,多年前曾担任电视剧《李卫当官》的编剧。话剧《惊梦》故事内容、结构、节奏都很好,传统而简洁,冲突、误会、隐喻、笑料都巧妙地串在一起,展现了战乱年代的中国里,艺术的传承、家国的前途、小人物的命运等方方面面。
话剧中涉及的两部戏,以《牡丹亭》观照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魅力;另一部《白毛女》则致敬了陈佩斯之父陈强——他在上世纪40年代曾在延安表演《白毛女》中黄世仁一角,作为彩蛋,陈强也在其中被提到。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这句广为流传的喜剧理论,就是陈佩斯提出的。有人在知乎网上提问“如何理解陈佩斯所说的这句话”,陈佩斯还亲自作答了一番。

这句理论其实是80年代,他被卓别林启发的。当时在一本电影杂志上,他看到对卓别林戏剧理论的介绍,卓氏把喜剧的生成归结为“窘境”。
作为话剧《惊梦》导演,陈佩斯在戏中对这句话深刻做了讲解。
演了60年昆曲的老戏班,有两代人的传承,一曲《牡丹亭》无人不晓。然而当解放军送来300斤粮食点戏时,童班主为了一大家子的口粮,爽快应下来了。直到对方送来《白毛女》的本子,戏班才傻眼。
“穿这个上台?哪出戏有这么个穿戴?”传统《牡丹亭》不听了,对这群唱昆曲的是一种悲剧。实际上,任何变革对“旧人”都是一种悲剧。

而对童班主来说,一边是收了粮食必须演(尊重观众、戏比天大)的职业坚守,一边是没人愿意唱的窘境。童班主朝跪在地上的孩子啪啪抽板子、逼他们演的时候,观众纷纷动容。而当白娘子扮相的“喜儿”、赵云扮相的“大春”亮相时,全场又哄堂大笑。
“钱难赚屎难吃”这样的流行语放入台词,也搔到了观众的笑点。笑过之后想想,谁又不是“甲方乙方”中的“乙方”呢?戏班为了300斤粮食硬着头皮工作,谁又不是?
“您说哪个好,哪个就好。”童班主对着主顾鞠躬的时候,让人想到为某些坚守的那些忍辱负重。这样的遭遇,恐怕普通人都能说出来。
从西装革履到疯癫沉沦的常少爷,本是同窗、同志最后沙场厮杀的两个将军,乃至吹笛的乐师、童班主的徒弟邵伍——与白毛女一样的命运……
将军、戏班、地主,父子、爱人、同窗……故事里的每个人,身上似乎都背负着一个悲剧。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