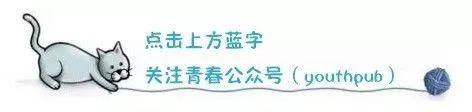

// 阅读本文需要约 8分钟


终身流放(节选)
| 尼 宁
——我的脸上有酒窝,身上有胎记,我的脖子和胸前都有痣,老人们常说脸上有酒窝,身上有胎记,以及脖子上和胸前有痣的人,都有可能是没有喝孟婆汤的人。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他是一个行为艺术者, 其实只是一个二流大学的三流大学生,在一部小说里, 他把自己分裂成了自己的父亲,他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进入他父亲的痛苦,并且觉得自己将代替父亲死去,并且为他的母亲赎罪,可是他错了,因为当他把自己奉献给诗歌的时候,一切都要为他的诗赎罪, 一切都要为他的感觉赎罪,为他的耳朵,为他的眼睛, 为他的鼻子,他的舌头,他的嘴……
你们会一如既往地看到他的诗,除了他自己觉得伟大,几乎没有人关注他,虽然我觉得对一个死者说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话显得我多嘴多舌,可是除了我又有谁知道在十四亩成熟的麦子地里,他父亲的死就是他的死呢!
下面是他生前的一些似日记又非日记的东西,还有一部分是小说稿,我是他的第一个读者,下面,我把他的稿子东拼西凑,如果你觉得这是一部小说,那它就是一部小说,因为尼宁写的东西太多但大多数又平淡无奇,我只能这样拼来拼去,最后不得不拿掉一些东西,才能勉强能看得下去。
他死去的前三天还和我一起喝酒,他喝醉了,我提着他的包回到了宿舍,那个棕色的,上面印有一只黑色杯子的文件包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孩子,一直在我那里待着。
一
今天我领到了我第三份兼职的工资,一共两千块钱,我买了两条新毛巾,一个新的剃须刀,一叠信封,给我妈妈寄了一些缓解静脉曲张的药和一些衣服之后,我一个人在外面的穆斯林餐馆里点了一碗羊肉面,在等的过程里,我通过旁边的落地窗看见外面一个满身油腻的青年男人站在烧烤架后面,熟练地转动着熏黑的铁签子上的羊肉,他快速地上下翻动,不一会儿,红白两色的新鲜生羊肉就变成了香喷喷的烤肉了,接着他会刷上特制的红亮的油和调料,然后稍稍一抖就放到盘子里,端到那些涂脂抹粉的女大学生面前了,接着他跑出去再烤一盘,端到满脸忧愁谈论着如何创业的男大学生面前,现在真的是没有人认真做学问了……“同学,你的饭好了!”一个一眼就能看出做兼职的女同学羞涩地喊了一下我,我回过神来说了一声谢谢,她便娇滴滴地转过身去招呼其他客人了。我喜欢她很黑很粗的辫子。
我回到宿舍带了日记本,然后到我经常喝酒的酒吧回忆这一个月来给女生宿舍送水时的一些见闻。
我要说的并不是我提着两桶水在楼道里吃力行走时撞了谁,因而就与她发生做爱类似的事,当然聊这些是因为我身边不乏这样的女朋友,我不用太过主动, 只要略施小计便可让她们投怀送抱,她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与我制造偶遇。当我以爱神的姿态临幸她们时, 她们会如出一辙地用白嫩的双手阻挡我,而我只能以更加果断的手法、更大的力量使她们就范,但有些姑娘会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抽泣,我一开始对这类姑娘青睐有加,但是后来对她们就丧失了好感,甚至是厌恶、痛恨,她们想要装出一个善良姑娘才拥有的贞洁来博取我的同情,最后却要使我在我的诗里赎罪以求得片刻安宁,正因为如此,我才找到了一个这样耗费体力的兼职。
我对八号和九号楼的姑娘一个月内最深的印象大概由三四幅画面组成。
第一幅是一个寂静的午后,我敲门,一个姑娘开门,我气喘吁吁地走进去时便听到了久石让的音乐, 随之我看到阳台上充满了温暖的阳光,半空有一条钢丝绳,上面挂着清香的内衣,窗台上摆放着几盆盛开的蝴蝶兰,这个宿舍优雅别致,然而五六个姑娘挤在阳台上抽着细细的香烟。左边靠着柜子的身穿橙色上衣的姑娘跷着二郎腿,她扎着马尾,系绿色头绳,别着白色发卡,在这群打扮得极不成熟的姑娘里,她用最熟练的姿态吧嗒着,显得茫然无绪,在我往她们安在阳台上的饮水机上放置水桶时,我发现只有她夹着比较粗一点的男士香烟,是我惯常抽的黄鹤楼,我莫名觉得她很美,如果她夹一支其她姑娘抽的那种细烟, 倒反而显示不出她苦闷的心情了。
在她旁边紧靠着一个身材纤瘦的黑眼睛姑娘,头发乱蓬蓬的,显得她更加局促,因为她的左手夹烟, 右手在不断遮掩着她头顶晾干的米灰色胸罩,于是左胳膊一开一合,活像王宝强饰演的树先生,我对她无话可说,只是想笑,其他的几位姑娘也闷着头吞云吐雾,甚至正在艰难地把烟雾从鼻孔里强行擤出来。我同情她们,她们因何如此,或许是家庭的变故,或许是情感的失落,或许是无法顿悟的失败,我怜悯她们, 但是这些感情都不是善意的,在我的意识里,女人太过于爱惜自己,她们可以为自己的情夫而毒害自己的丈夫,当她们的丈夫死去时,她们却像失去童贞的少女悔恨不已。所以我痛恨她们,我为自己彼时的同情心感到可耻……
我从包里掏出几片抗抑郁的药片之后觉得自己不能再写下去了,每次谈论女人都让我想起我的母亲。我想我痛恨女人的根源应该来自我的母亲。我想我今天必须写完这篇日记,因为今天的日记主要是作为回忆,明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或许明天我不用回忆,而是创造记忆,于是现在,我正强迫自己记述那一个月内遇到的其他事情,或者可以说是其他女子。
第二幅图画很简单,但直逼人的神经,画面正中央只有一个姑娘,但她全身赤裸着,所以有很多可能供你想象,但《赤裸的维纳斯》除外。
那是八号楼的二楼,我一口气便可以提上去。同样,我敲门她开门,我低着头朝里面喊,你好同学, 送水!眨眼之间便跨了进去,在我的眼皮上撩的瞬间, 一个只穿肉白色三角裤的姑娘,不,确切的说是一个挺着一对白鸽般硕乳的姑娘,如同我手持照相机看到的清澈画面一样看到她呆呆地就站在眼前,我为我多余的眼睛感到不安,我的耳根似乎着火了,我低着头匆忙把水放在饮水机旁边便灰溜溜地逃出去了,出门的时候绊了一脚,似乎扑到了另一个正在急行的姑娘身上。因为天气的缘故,我刚进去时浑身神清气爽, 但当我出来的时候已经大汗淋漓了,我在楼下面缓冲了许久才又鼓起勇气把水往其他宿舍送。
我一直在回想她,我一直觉得她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我看,我觉得她需要一个聆听的人,她需要哭诉衷肠,我觉得她渴求被人拥抱,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确定描述她的脸,或许是印象太过深刻,我反而无法把她刻画出来,所以我一直在给她寻找一张脸,我一直在想那样娇好的身材,那样鲜艳欲滴却又不知羞耻的外壳下有一张怎样经常示人的面庞。我常常把我在不同旅馆被子下抚摸过的一个个精致的面孔想起来,但她们只能在我的意志里停留片刻,因为她们的脸和性别一样,毫无差异,我也同样比她们自己更加知晓她们的身体,我的嗅觉否定了她们与她重合的可能性。那位姑娘是绝无仅有的,我一会儿觉得她可憎,一会儿觉得她坦荡。她是万物之光,仿佛她用这简单的方法便可让旁人陷入自己精神的泥淖,而她却躲在一旁暗笑,她胜利了,她骄傲地看到一个体格健壮、并且对女人时刻怀恨在心的男人在她面前惊慌失措。那时,我想起了穆旦的诗: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紧闭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她赢了,在她面前,我黯然失色。
在第三幅画里,我遇到了从未体会过的感觉,或许真如朋友所说的那样,那种感觉正是幸福。
每次送完水,我们都会把每个宿舍的空水桶收集起来,送回去。那天,楼道里大概乱摆着六七只空水桶,我的手掌粗厚,手指短齐,所以最多只能带走四只,借着喘息之机,我用脚把它们往一起拨,在我竭力设法带走六只空桶时,从我刚出来的宿舍,一个皮肤黝黑,瘦小的姑娘快步走了出来,“我帮你拿下去。”她热情地朝我说,从她的穿着和打扮,我便确定她是一个农村姑娘。从内心深处来说,她无法激起我行动的激情,我知道自己自命不凡,时常抨击来自城市那无数变形的伪善的脸,却也瞧不起和我同为农村出生的不注重品行的人。所以我用一副轻浮的嘴脸对她说:“谢谢,真的不用!”“我正好下去,可以帮你捎带两只的——”,她绯红的脸显得格外急切,我无法用其他更直接、更伤人的语言来拒绝,只是很轻蔑地说:“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提这两只吧。”我手指着两个暗淡的浅蓝色空水桶。于是,我提着四只空桶,她提着两只从楼道上走下去,我的眼睛始终没有在她的身上多停留片刻,因为她的身上毫无闪光之处,而且她在提出要给我帮忙,在等待我回应的某个时刻,在她毫不美丽的脸上闪过了一缕命令的神色,一副反客为主的神色,如同我是她的副手,这是我不能忍受的主要方面,从没有一个女生胆敢用这样的方式来号令我,当然,除了我的姐姐。不一会儿,我们终于从七楼挤下去了,这时她突然回过头来对我说,“你们真辛苦!不能换个其他的兼职做做吗?”我没有回答她,而是用老实巴交的憨厚神色告诉她,我任劳任怨。她看到我们用来拉水的电动车,径直朝它走去,在车子旁边,她又慌慌张张地、小心翼翼地把水桶放到了车厢里,接着她转身抬头看了我一眼,便箭似的原路返回了,我示意微笑,看着上上下下的带着花儿般灿烂微笑的姑娘们,突然想起了她说的“我正好下去”那句话。
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很疲惫,我用一种感激的语气朝她的背影说:谢谢你。她听不到,因为我自己也几乎听不到,在她就要消失在拐角时,她转脸看了我一眼,一束光从她的眼睛里发射出来,一种带着深深成就感的充实的东西随着她的消失更加深刻地打在了我的心底,我想起了幼年那个时常帮助别人的善良的小女孩,她永远对捉弄她的小男孩施以庇护,从而不让他挨老师的戒尺,但常常一本正经地主动为一群俏皮却长着榆木脑袋的小孩讲解数学题和她自己发现的新方法,她永不厌倦地在自己课桌的左上角摆一支干干净净的假玫瑰花,她说她的父亲说过一句话,人永远要活在自己的浪漫和诚实之中。
那时,我完全没有了在一群姑娘面前展示我力量的心思了,我依然如同往常般自问,这一生到底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那天晚上我给一个朋友讲述了这个简单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故事,并表示我不确信自己的疲惫从何而来,以及那天黄昏飞鸟的叫声为何那样清脆。她嫉妒地跟我说那种感觉是善良与幸福。
我依然能够想起我在咖啡馆讲那个故事时的宁静,我跟她慢悠悠地讲:“今天,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她质疑地问:“哪个漂亮姑娘?”我没有回答,直到满意地把它讲完。
我离开酒吧时共消费了一百零七块钱。
▍尼宁,本名刘旭光,1996 年生,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2016 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栖云文学社成员。
— 未完待续 —
刊于《青春》201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