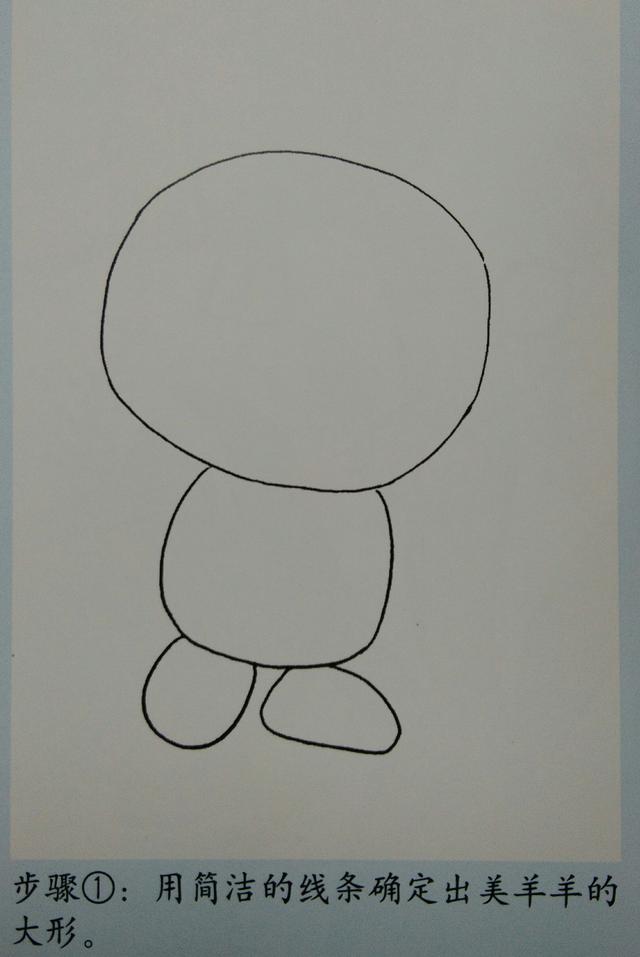文◆刘中才

鲁迅的一生中令他揪心的事情并不多,但有两件事他一直记挂在心里,至死都难以释怀。一是个人婚姻,二是与自己的胞弟周作人反目成仇。
鲁迅生活在封建社会渐进下坡路的民国,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朱安,这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不仅比自己大,而且文化水平不高,无论思想还是见闻都与留洋日本的鲁迅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包办式婚姻注定是没有爱情可言的,亦与鲁迅憧憬的幸福相去甚远。后来鲁迅遇上了自己的学生许广平,残存在鲁迅内心的那点希冀又重新有了起色。然而,就在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后,却遭到了周作人的冷嘲热讽,这给鲁迅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痛。原本就不善外露情感的鲁迅,因为师生恋而被周作人贬斥的一文不值。而周作人相对顺利的情感生活,以及对妻子羽太信子的百般宠溺,又像是在向鲁迅炫耀自己。

鲁迅先生
尽管如此,鲁迅还是以大哥的身份迁就着周作人。不过对于内心的真实想法,两人之间都没有作过深入交流,关于两家的生活,他们大都闭口不谈,其中的隐情已不得而知。但在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突然交给鲁迅一封绝交信,已经充分证明,两人的手足之情走到了尽头。只是鲁迅并没有预料到,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的猝不及防。
周作人在绝交信中说,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落款时间是7月18日。

周作人写个鲁迅的绝交信
周作人的这封信话语不多,却充满了戾气。言语之间尽是对鲁迅的责备。尤其是收尾处,要求鲁迅不得到后边院子里去,而且还用自重这样的话提醒鲁迅,这不由得让鲁迅内心震惊。
鲁迅看完这封信以后,五味杂陈,内心的感受难以言喻。那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欲邀问之,不至。
鲁迅想问个究竟,到底是何原因让周作人如此恼怒,以至于说出的话那么刻薄。然而,周作人全然不予理会。
其实,在收到这封绝交信的五天之前,鲁迅和周作人的紧张关系就已经初见端倪。那一天,周作人没有跟鲁迅一家一起吃饭。鲁迅在日记里也说:“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鲁迅二弟周作人
这一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因为自从鲁迅住进北京八道湾新买的住宅以后,他也把母亲和周作人以及三弟周建人的妻女一家接了过来。鲁迅住前院,周作人住后院,一家人的开支都是由鲁迅承担,吃饭也都在一起而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突然分开了,而且还送来了绝交信,说明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至今都没有确切的定论,因为,鲁迅去世之前没有作出解释,周作人至死也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因此,二人失和就像是一桩沉入大海的无头冤案,一直以来令后人困惑不已。
不过,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对此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解释过两人之间的矛盾。
许寿裳说,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个道貌岸然之人,表面上对鲁迅谦恭礼让,内心却总是不怀好意。周作人则听信羽太信子,许寿裳曾经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周作人,开导周作人遇事要有主见,要明辨是非。然而周作人漠然置之,并没有开窍。

鲁迅与许寿裳(前排右三)在一起
与周作人有了隔阂但尚未闹僵的时候,鲁迅就搬到了客厅外面住,但是周作人并未理解其中的意思。后来鲁迅直接搬出八道湾到砖塔胡同居住,两人失和也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鲁迅搬离八道湾作过很艰难的思想斗争。购买八道湾的房子时鲁迅花了3700大洋,房子是他一个人购置的,也是他亲自设计的,每个房间,每一处摆设都浸润着鲁迅的情感。但是除了离开已经别无选择。痛苦的是,如何安顿妻子朱安,鲁迅并没有头绪。
许寿裳说,鲁迅离开之前曾问朱安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的朱家。如果回绍兴,鲁迅会按月给她寄奉生活费。听到这句话后,朱安的内心很是悲凉。朱安对鲁迅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的母亲)也迟早会搬走。我独个跟叔婶侄儿(周作人一家)住,算作什么呢。婶婶(羽太信子)又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呀。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回,你搬走后,总是要有人给你烧饭、洗衣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跟你一起搬出去住。

朱安
朱安的这番话很沉重。鲁迅愧疚之余,深感自己有些绝情。毕竟朱安是自己的妻子,陪伴自己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亦有苦劳。而自己非但没有同情于她,还用一种不太妥帖的语言问询于她。
搬出八道湾后鲁迅借钱在西三条胡同买了一处三开间小院,东房留给母亲住,西房是朱安的卧室。安顿好以后,鲁迅回到八道湾的住宅拿书,却遭到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阻挡。羽太信子还叫人来,试图将鲁迅轰出去,周作人跟着把鲁迅的书仍到了地上。许寿裳说,这是鲁迅亲口告诉他的。而对于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这种态度,鲁迅并没有对其抱怨,他说这是家事,不足与外人道。
从许寿裳的这部著作里我们能够看出,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与羽太信子在中间挑唆有很大的关系。而周作人听信妇言,不分青红皂白,任凭羽太信子胡言乱语,造成二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

1923年鲁迅、周作人与友人在北京八道湾的家中
对于许寿裳的解释,周作人进行了反驳。他说我与鲁迅的失和在信里说过,我原本在日记里写的很清楚,但是还是用剪刀剪去了所写的字。周作人说,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那个事件到底是什么,周作人没有说,鲁迅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猜到,周作人所说的那个事件指的是女人的事。

鲁迅与周作人决裂以后,远在上海的三弟周建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明显的是,周建人站在了周作人的对立面,而与鲁迅保持着良好的兄弟之情。周建人知道羽太信子的为人,而对她的所作所为同样不以为然。
此外,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周建人说,羽太信子极不懂得节俭,一家人都要吃饭,她在花钱用度上总是大手大脚,周作人却惯着她。可一家人花的钱都是鲁迅供给的。
1912年起,鲁迅经好友许寿棠的推荐,进入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工作,8月份,袁世凯任命鲁迅为教育部佥事,月薪240元,此后涨到300。此外,鲁迅还在北大讲课,业余时间写稿,讲课费和稿费加起来也有几百,在当时属于高薪阶层。然而,这么多钱依然不够用,不到月底就已经捉襟见肘。

周建人(前排左一)与鲁迅、许广平在一起
鲁迅举家搬迁到北京后,当家的事情全部交给了羽太信子。三弟周建人说,羽太信子很不会过日子,她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而且她很懒做,什么事都不操心,唯独对钱很感兴趣,家里的活计全都雇佣人去做。更为可气的是,她总是想到一出是一出,饭菜做好了,她却突然说没胃口,想吃别的东西。新买的被子还没有盖就说颜色陈旧,直接送给佣人,周作人却由着她的性子,并不敢多说什么。
鲁迅同周作人一家生活在同一个院子里,每日的吃喝都由厨房供应,因此他就把自己的收入全部拿出来用于全家人的生活,不仅如此,他还把原来积攒的余钱也贴了进去。
这些事三弟周建人都很清楚,只是他没有跟鲁迅和周建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也不便说过多的话。但有一点,周建人对二哥和羽太信子的做法是很不满意的。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很多原因是羽太信子给家庭带来的困扰。女人总是不省心的,这一点,在鲁迅家里锋芒毕露。羽太信子的挑拨离间,应该是兄弟决裂的根本。除了经济方面的意见分歧,另有一事不得不说,那便是周作人在绝交信里有所保留也略带隐晦的问题。而这件事就是羽太信子告诉周作人,说鲁迅偷看她洗澡。
对于这件事,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酷讯与我七十年》中说,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留学的那个年代,一般的日本家庭沐浴时,男女进进出出都不回避。周海婴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女工就在厕所里打扫卫生,男子进去小解她们也不避让。鲁迅与周作人一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羽太信子又是日本人,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是一件平常不过的事,但鲁迅决然不会刻意去偷窥什么。

羽太信子(左一)
此外,鲁迅的邻居章廷谦也对此事做过解释。羽太信子告诉章廷谦,说鲁迅在她的卧室外面听窗,还造谣鲁迅调戏她。章廷谦对此解释说,羽太信子居住的卧室在北面,屋外的窗前种着满地的杂花生树,而且家里住着侄儿侄女,还有周建人的家眷,鲁迅绝不可能置他人于不顾而踩着高矮错落的花草去偷看羽太信子。羽太信子之所以造谣生事,离间兄弟二人,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因为,羽太信子花钱如流水,鲁迅每月的薪俸虽然不少,但也不够羽太信子的挥霍。羽太信子无法满足自己的花钱欲望,才把矛头指向鲁迅,由此引发各种矛盾。

1924年鲁迅搬到阜成门砖塔胡同,与周作人彻底分道扬镳。往昔的情感历历在目,心中再也难以泛起涟漪,这是鲁迅一生的痛。
1925年,周作人将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伤逝》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了《京报》副刊。其中的最后两句是“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周作人的这几句诗向鲁迅传达出一个信号,二人的手足之情如同阴阳两隔,此生再也不可能重归于好,再也不会相见。
20天后,鲁迅用同样的题目创作了短篇小说《伤逝》,此后鲁迅又写了《弟兄》,以此回忆二人之间的过往情谊。然而,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往,尽管鲁迅在小说中用故事化的方式对兄弟二人的失和深感内疚,但是周作人依旧漠然置之,跟自己的日本妻子沆瀣一气。而且在8月份的时候,鲁迅因为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运动,还参与校务维持会公开发表声讨宣言,被段祺瑞免去教育部公职。事后,鲁迅据理力争,上诉平政院,最终免职一事被平政院宣布无效,鲁迅继续在教育部工作。

鲁迅一家
多重的困惑和挫折,不仅让鲁迅在精神上深受折磨,而且身体也每况愈下。自1923年起,两年多的时间里,鲁迅先后因肺病复发而住进医院,一次是与周作人的矛盾冲突,另一次就是1925年的免职风波。此时,鲁迅已经不愿呆在北京,进而产生了南下的想法。
一方面,鲁迅与周作人的矛盾使他感到生活在北京是一个打不开心结,尽管北京早已成为鲁迅的第二故乡,还是给他的心灵烙上了难以抚慰的创伤。另一方面,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已经发展为恋人,而鲁迅是有妻子的,他的原配夫人还同他一起住在北京。他虽然不接受朱安,却也没有打算将她遗弃,但是,如果既要照顾到朱安的感受,又能与许广平在一起,两个人都在北京,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若要同许广平朝夕相处,留在北京百害无一利。
经过慎重思考,鲁迅决定南下。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受时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林语堂的邀请,就任厦门大学国文系和国学研究院教授,月薪达到400元。然而,四个月之后,鲁迅因为与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在学风方面产生冲突,而选择辞职前往广州。
1927年,鲁迅正在中山大学任职,其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极力营救被捕的学生,均以失败告终,故此愤然离开,于9月份远离是非之地,乘船前往上海。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达到上海,暂住在共和旅馆。当天晚上,林语堂、孙伏园、孙福熙3人一同前来迎接鲁迅,并希望鲁迅能在上海长期居住。鲁迅当时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再看看。

1931年鲁迅在上海家中的书房
次日,鲁迅同许广平一起到横浜路找到了三弟周建人。周建人住在景云里一弄10号,东西邻居分别住着叶圣陶和茅盾。鲁迅感到这里文化气息浓郁,生活得十分温馨,便有住下来的打算。
10月8日,鲁迅在景云里安顿下来,这一住,就是9年。
在上海的日子里,是鲁迅一生中文学创作最为辉煌的时刻。期间他出版了《故事新编》,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与冯雪峰创办《前哨》,同瞿秋白、内山完造、史沫特莱结下了至深的友谊。

然而,快乐始终伴随着病痛,尤其是与周作人的决裂,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鲁迅的衰老。本就患有肺病的鲁迅,因为抽烟过度,也几次旧病复发。加之他日夜不停地读书写作,导致身体严重透支。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中国文化战线的旗手、民主革命战士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寓所病逝,享年56岁。

鲁迅葬礼
鲁迅逝世后,胡雪峰、宋庆龄先后赶来吊唁,并在许广平的同意下,成立了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10月22日,鲁迅先生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送往万国公墓,胡风、巴金、黄源、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郎西、陈白尘、肖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萧军亲自为鲁迅先生抬棺。从离开北京到上海,一直到鲁迅去世,他与周作人再也没有联系过。
鲁迅逝世13年后,诗人臧克家写了一首纪念鲁迅的诗歌《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谨以此文,献给逝去的鲁迅。
(写作不易,且行且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