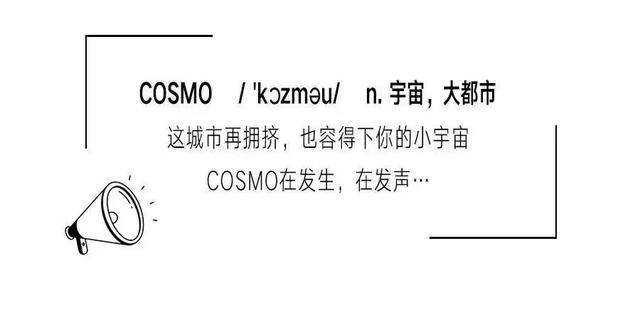巴士读书唯一人
看过电影《巴士奇遇结良缘》,始知巴士(bus)就是公共汽车;交往多了,才发现这位资深新闻工作者是在巴士上读书的唯一的人。巴士也是我的腿,但我比人家粗俗得多,从未在它移动的过程中读过书。
如果谁在呼和浩特市的公交车上看见有人读书,那此人一定是我的这位同学。他嗜书如命,常常起早逛旧书摊,有了收获,就在班群里晒,让人艳羡。他抓住一切时间读书,连坐公交车赴同学的宴请也不例外,因而,他是总迟到的那位。我戏称他是全市坐公交车而读书的唯一的人。
嗜好读书的人必然有藏书癖。这厮是旧书市场的常客,我曾与之在不同的书肆偶遇多次。碰到喜欢的书,如果不确定家中是否已有收藏,他就拿出手机,在照片中寻找,已有就作罢,没有则必须买下。他的手机里存有书柜每一格的照片。这防止重复购买的法宝,我怎么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呢?这厮果然聪颖异常。的确,记忆有时候会溜号,其实,再好的记性也不如烂笔头(照片)啊!我深受启发,正在如法炮制,以防书柜中再出现孪生甚至多胞胎藏品。过去诞生的这类书籍,我都用来与书友体会换书之趣了。这《换书之趣》也即将分娩。
这厮的书房令人艳羡,四壁图书,书柜虽没有到顶,但一摞一摞的书早已在进军天花板的战斗中遇阻。榻榻米在书房的窗下,书堆得满床。我想,在这样的所在与书共眠,一定无比踏实幸福,所有的工作怨气和生活烦恼在这里都会烟消云散。即便做噩梦,梦中的情景恐怕也是拐走女仆,与之边荡秋千边看爱情小说,结果摔了下来,抱作一团;或者飘飘然从空中坠落,一下子掉在了书堆里;再不然就是为情人唱《恰似你的温柔》时,脚底一滑,最后,一跤给摔(帅)醒了。
文人多好酒,这厮更甚。只要有他在,谁都别妄想只喝一场,事先都得做好随时移师烧烤店的心理准备。“喝着玩呗!”这得多大酒量作支撑?其实,他也曾“玩”得趴在饭桌上人事不省。人家那喝酒才叫名副其实的“樽中酒不空”,从来不干杯,不管跟谁喝,杯里总得剩下所谓“福底”。而且,自己只倒第一杯,之后不论喝多少,都得别人给斟。这个“别人”多数情况下就是我。陪他喝酒,或他陪我喝酒,是为了高兴,所以我也就一直惯着他这毛病。其实,这毛病当初就是我一手惯出来的。现在想金盆洗手不伺候他,人家已经习惯成自然,没有自理意识,觉得给他倒酒是他天然的待遇了。
这厮为人非常讲究。2001年春,我远赴呼伦贝尔工作,他在家中设宴为我饯行。这是极高的礼节。我至今心怀感激。菜很硬,一锅羊棒骨;酒管饱,一大箱啤酒;作陪者二,都是铁哥们儿。640毫升的瓶装啤酒,四位好汉每人喝掉6瓶。在当年,这已是很大的酒量。要是放在十年前,这都不够塞牙缝的。那天,为了陪他以及另外一位著名人士(即文尾所称那厮),在13个小时内,我以一己之力为42瓶啤酒换了包装,从玻璃瓶换成陶瓷杯,继而由我的肚子搭桥,最终统统换成下水道。我也真是“大肚(度?)能容”。那次,人事不省的是另外那厮。从我开始,这样的家宴就成了交流到外地工作的同学临行前的标配。有意思的是,我之后,另外那两位在他家为我饯行的朋友也相继享受了这一待遇。除了宴会的主人,我们三位都有交流经历,其中一位已经两度“出宫”,至今仍远在万里之外,没有“回銮”。
新闻工作者都有传世之作。“非典”被打败之时,这厮在其服务的那份著名报纸上重磅推出了一篇特写。其时,我正在重读《双城记》。“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狄更斯以这样充满矛盾的概括开始了充满矛盾的故事。

特写的开头曰:今天是离别的日子,今天是相聚的日子。原来这厮对上述那段话了然于胸,照着“狄猫”,画了一只“马虎”。那期间,马记者一直在医院采访,第一手材料转化成的新闻作品比小说更加真实感人。
这厮是回族,那厮乃蒙古族,小子我系汉族。我们是民族团结“铁三角”。铁到了什么程度?三年前,那厮要北上赴任,这厮为他饯行,我腓骨远端骨折,缠着绷带,拄着双拐,在一家清真饭店与他俩豪饮,导致脚肿,还伴有疼痛。几天后换绷带,大夫简单询问几句后,未经任何化验就武断地诊断为痛风。我知其为误诊,因为我的尿酸指标当时乃至今日都是正常的。
我常想,“铁三角”“几时杯重把?”(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待到那厮归家日,“一曲新词酒一杯”(晏殊《浣溪沙》),“会须一饮三百杯”(李白《将进酒》)!喝着玩呗,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