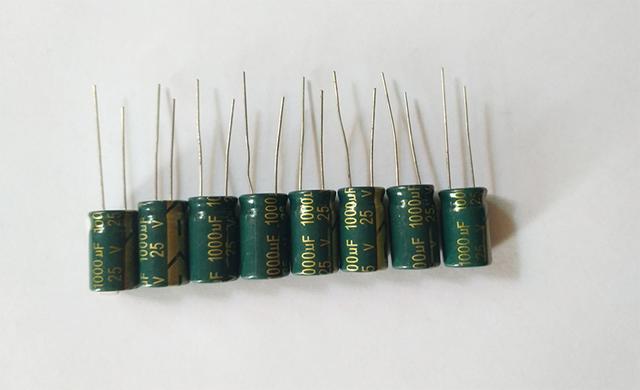“王稽”是王氏见诸秦史中较早的一位人物,《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记载王稽曾为秦昭王谒者,秦昭王三十六年使于魏国,“载范雎入秦”,举荐范雎为秦相国,封为应侯;后王稽于秦昭王四十年拜为河东太守,秦昭王四十五年王稽因“与诸侯通,坐法诛”,此时秦国诸王氏家族不仅声名未显,而且还仅是中低层官吏,于文武均无什么大的建树,即便秦昭王四十七年秦昭王任用白起“长平之战”破赵,后又赐死白起之时,王龁、王陵等人也只是白起麾下的中低级将领,王氏家族起于微末之说似乎令人信服。
但是,考虑到秦法苛酷,动不动就要灭族,王稽之死就委实令后人心生疑窦了。王稽因与六国相通的罪名被诛杀后,以常理推测,王稽一家自然不保,其子孙不必说了,可能会被株连而死,就连他的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等,也难逃大秦律法,不用夷三族那么残酷,就近将王稽本家全部杀掉是极有可能的。
如果是这样,后世王氏诸族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杰出人物位列朝堂,甚至王氏诸族也不可能兴盛起来,所以由王稽所引发的灭族之祸,是王氏诸族见诸史载的第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是怎样度过的不得而知,但王氏诸族显然却从此日渐旺盛,拉开了第一波次的兴盛序幕,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大批中级军官,现在从《史记》中能够看到的就有王龁、王齮,这似乎是兄弟两人,最高职务均为将军,未获封爵,但相比王稽,王氏家族已经跻身大秦帝国的中高级贵族了。
在王龁、王齮的同时,《史记秦本纪第五》中有“(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秦军分为三军。武安君归。王龁将伐赵皮牢,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韩上党。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四十九年正月,益发卒佐陵。陵战不善,免,王龁代将。”的记载,此时距后世秦始皇时期尚有三四十年的样子,所以,此处陵应非后世“襄侯王陵”,但可以发现,王龁、王齮应是后世王翦、王绾、王陵的先辈,很可能即是父子关系,世袭为将。
为什么王稽之死却换来了王氏二将的出现,而且其子孙即可能是世袭为将的王翦、王绾、王陵等人?要解决这个疑问,其实还是要回到王稽之死是否连带灭族的问题上去,从历史记载中,王稽之死并未牵连扩大,所以就不存在灭族的问题,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王稽可能是王龁、王齮的父辈,而是秦昭襄王异常低调地处理了王稽通敌的问题。

由于王稽曾任谒者,为秦昭襄王搜索六国人才,最后还是坏在六国这个问题上,而谒者能够及时地觐见秦王,相对私人关系也存在很大余地,这应该是无疑的,至于这层君臣关系之外,王稽家族是否还与秦王存在其他更亲密的关系,并无史料可资推考,但从躲过灭族之灾、兴起王氏二将来看,秦昭襄王对王稽的处理还是十分宽容的,对更大范围的王氏家族的关怀也是一目了然的。
在王稽前后的历史记载中,穰侯魏厓两次反复去相,最后去封地就国,同时也意味着一大批的芈氏家族成员被冷落,特别是与魏厓亲近的家族成员,这些空缺可能让另外一部分中低级贵族兴起,王氏二将无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
与后来白起被诛杀后又崛起了一批王氏将领相似,王氏家族总是在大秦帝国权力争夺中迎风而上,就不能不令人想到,王稽之时已有王氏家族与秦王通婚。毕竟谒者虽然官级不高,但却是秦王的心腹之任,能代表秦王对六国人才许下重诺,才更容易招揽到六国人才,所以,王稽时极有可能王氏诸族已经通过婚姻攀上了秦王这棵大树,才在随后两次芈氏家族主将被诛杀放逐的大的历史机遇中迎风而上,出现了两个批次的王氏诸将,并逐渐承担了很多主攻任务,在军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从这些推理可以看出,与王氏家族关系异常紧密的胡亥,不太可能是芈氏家族的妃子所出,那样的话,胡亥继位意味着追算旧账,首先可能要对王氏诸族进行清算,并再度起用芈氏家族,但胡亥却显然非常依赖王氏诸族,而王氏诸族的范畴很大,则意味着在王氏诸族两次崛起的历史过程中,胡亥的母亲和皇后都来自于王氏诸族是非常可信的。
应该说,这些分析将王氏家族在大秦帝国的活动年代上推了至少三四十年,甚至可能会有一百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王氏家族可能是同时几个族份并存朝堂,因此也就可能与秦王多次联姻,即好几代的秦王都曾娶过王氏的妃子,才会在百年多的积累之后出现胡亥这样一位历史性人物,以及王氏诸臣之盛。
胡亥在位时,先后有王陵、王离两位将军降敌,论罪至少也应灭族,但是历史记载中并不存在灭族之祸,而且胡亥在失去王离后,没有依常理更加依赖章邯,却不断逼迫章邯与项羽决战,直至将章邯逼降于项羽,失去大秦帝国最后一支主力军队,并迅即被赵高宫变所杀死,大秦帝国至此已经坍塌。
综合起来,王氏诸族能够多次躲过灭族之罪、灭族之祸,除了很早就与秦王联姻的理由之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了,这意味着王氏诸族的崛起是依赖大秦后宫姻亲的势力,并在比常理更早的时间就进入了大秦帝国的核心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