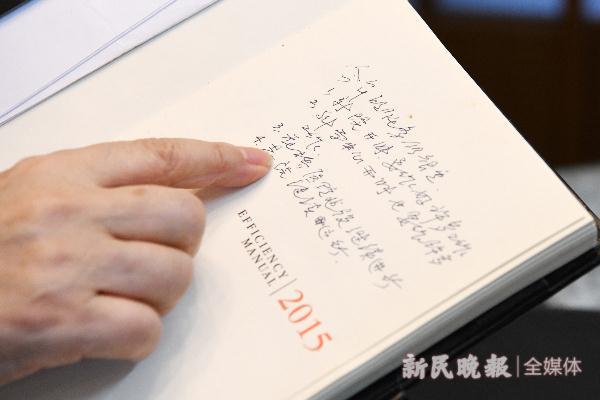孕期的某天,好友微信跟我说:等你卸货了,想干什么我都陪你,蹦迪都行。
我回:这辈子最不擅长的,恐怕就是,扭起来,跳起来。
“蹦迪”二字,唤起了我以前一段没脸的学舞经历,是小时候的事了。现在想来,一个人是否在某个领域有天分和热情,孩童时代确实可以窥见几分。
我是一个舞蹈二愣子,先不说有没有天分,连喜欢都谈不上。小学二年级,偏偏被外婆逼着每周去少年宫学舞。莫非那时就开始卷了?应该不至于,外婆只是想要丰富我的生活和艺能罢了。

依稀记得,那座少年宫是在半山腰,挺有“大隐隐于市”的自然观感。但这只是表面。每次被外婆送过来学舞,就像是进了一座魔窟。
虽然我不至于沦落到“同手同脚”的严重不协调,但我的肢体总是像被无形的铁链拴着,舒展不开,胆量不够。最丢脸的经历有如下两段,因为够丢脸,所以到现在都够清晰。
第一段。小朋友们排着队,轮流展示刚学的动作。慢慢地就要到我了,心脏急急跳动。为了拖长时间,我偷偷从队伍里出来,小心翼翼避过老师的眼睛,跐溜一下闪到队尾。动作不过关的孩子,被老师要求继续排队,于是我不停偷溜到最后。
漂亮的舞蹈服在小姑娘身上,裙摆招展,娇嫩似花,好看极了。这份好看,是她们的,不属于我。

《跳舞吧!少年》剧照
队伍的人数,终究是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一个。老师看着我,哭笑不得:
“来吧,以为我没看到你跑?”
我的脸刷地红了。音乐响起,硬着头皮向前去,在笨手笨脚和呆子似的表情中,完成了僵硬的展示。连我自己都清楚,这绝对是不过关的。在其他小朋友的众目睽睽下,我都快哭出来了。
老师走过来拍拍我:“好啦,就这样吧。”
第二段。孩子们排着队,一个个打翻叉。我看着其他小姑娘手脚舒展伸直,刚柔并济,轻轻松松地就翻过去了,像枚小风火轮。
我的心脏一如既往扑通扑通狂跳。就算老师和其他孩子示范多次,我依然不懂要怎样翻过去,只能躲,躲到又只剩下自己。老师等着我,孩子们看着我,舞蹈室的时间凝固了。

《小小少年》剧照
我数次扬起双臂、打直双腿,盯着地板,作势要翻;但又数次踉跄止步,尴尬得脸越来越热。什么动作要领、什么对美的渴望,在我脑子里是通通不存在的。唯一在我脑子里反复播放的画面是:失败了,跌倒了,头被地板撞破了,被大家笑话了。
小小年纪,就好像染上了迫害妄想症。
时间分秒流走,我还傻站着,不知如何是好。老师终于被我逼得开口了:“抱头滚过去吧。”
我仿佛得到了大赦——抱头滚过去,这个我会,在家的床上经常滚着玩儿。于是我跪下,折叠身体,胸贴腿,腿贴地,双手抱头滚了过去,算完成任务。
不知那时老师有没有偷偷叹气呢?遇到如我这般顽冥不灵的舞蹈学生,真是难为她了。

《陪你一起长大》剧照
到现在我都没尝到打翻叉的美妙感觉。初生牛犊不怕虎,连小时候都没胆量做的事,恐怕就此画上句号了吧。只是每次看到电视节目比如春晚上,那些灵活曼妙、轻盈如蝶的舞姿时,我总会想象一下自己也具备舞蹈能力、旋转于舞台的样子,算是对当年失败的学舞经历做的意识补偿。
我很清楚自己难以舞蹈的原因。从小,我就害怕被注视,不是一个可以自如展示自己的小孩。舞台和聚光灯是我的天敌。我相信这不是我的错,只是和其他大胆show出来的孩子天赋不同、兴趣不同罢了。但这不代表我不感到遗憾。
学生时代,校园里有街舞社,振奋的节奏、酷酷的动作和鲜活的青春,每次都牢牢吸引住我的目光。
高中时,有一位男生,在校园舞台上用popping(机械舞)赢得了满堂喝采。我不知道他的水平和真正的牛人之间有多少差距,我只知道当时看得眼睛都忘了眨。他的每一块肌肉都像是有电流穿过,随着酷炫的音乐,任意摆动、震荡、停止;又像是跟着无形的线,把自己的身体完完全全交付予更高一级的神。此时,意识不再是大脑的专属功能,而是派生到了身体四处的肌肉细胞——脖子、臂膀、胸膛、双腿、脚,都用各自的思想活起来了、喊起来了。

《歌舞青春》剧照
最后一幕,他把前面所有的震撼汇聚到了一个爆点:充满机械感的音乐,音阶由高往低落,像一枚炸弹从天而降划破空气的声音;他的整个身体随着这音符直落,直挺挺地往地板倒下去,在千钧一发之际,仅靠两个脚掌猛然稳住了,最后一个音戛然而止。
这画面看得全体屏息凝神,接着爆发出雷鸣的掌声。
大学迎新晚会,我也看过一个女生的舞蹈表演。她身材娇小,目测大概一米五几,一头长卷发,站在C位。并不高大的身体充满了爆发力,甩动脑袋,头发飞扬,舞动躯干和四肢,世上除了音乐和舞蹈,别无他物。最后,她从舞台深处踩着音符,迈着满满力道的步子往前踏,仿佛每踏出一步,脚下就生出威风凛凛的巨浪;她的表情魅惑又冷酷,突然跪地一滑,直冲到舞台最前端,像冲破了海浪而来。
室友在我旁边止不住地称赞:“别说男生了,我一个女生都喜欢!”
他们跳舞时的忘我、尽情,让我羡慕极了。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更加佩服。
我好奇,像他们这种跳舞跳进心流状态的人,是怎么看待观众的目光呢?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享受能力,还是也走过克服害羞的过程?
说来也巧。之前刚好在《三联生活周刊》看到一个关于舞蹈和身体的专题。在多个维度的采访和陈述中,有一篇专访最吸引我,题为《“未经雕琢的身体最可贵的,就是真实”》。
这句话出自该篇的专访对象,杰罗姆·贝尔,著名的法国舞蹈家和编舞家。从2015年开始,他和他的团队推出了一项名为《盛会》的特殊表演,以当年5月的布鲁塞尔为起点,几年间走遍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一场非常规的、接壤民间的舞蹈盛宴。每到一个地方,贝尔团队与当地的素人舞者合作——一群可能从没跳过舞、更没有经过正规舞蹈训练的对象。

《爱乐之城》剧照
贝尔不会用具体的动作来限制受邀者,只给出作品的框架结构,比如仅在立牌上提示一个舞蹈名词:华尔兹、迈克尔·杰克逊、集体舞、大跳……他认为,平等性建立在每个人独树一帜的身体特质之上。在这个平等下,人人皆可舞蹈。
比如,看到“大跳”的名词,一名残障人士坐轮椅登场,“迅速转动车轮,快到舞台中心时,他昂起头,张开双臂,轮椅靠惯性向前滑动直至离场”。身体做不到的,他靠想象和借助现有条件,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大跳和飞翔,获得的掌声和欢呼不亚于专业舞者。
“未经规训的身体,在舞蹈艺术最本质的魅力之下,释放超凡能量。”一切对于“美”或“正确”的传统评价,不再是关注点,更不再是问题。
贝尔团队所做的,是一个独特的、突破性的尝试,让我看到了一些问题的答案,甚至启发一种哲学层面的思考。他说: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听到音乐转圈几乎是人人都有的身体冲动。换句话说,所谓的身体意识其实是每个人的本能。你在理性思考身体意识是什么、如何激发身体意识时,你可能很危险,因为你正在远离它。”

《舞出我人生》剧照
是的,从小,不就是我的理性编织了牢笼,困住了身体吗?让它变成了一块僵硬的石头,而不是灵动的流水。“听到音乐转圈”,这项本能愿望被拴住了,现在已经非常难解开,简单点说,就是跳舞前想太多。
理性,是人类引以为傲的思想能力。之于舞蹈,我的理性思考也许可以分解如下:跳舞,是必须要跳得好看的,而好不好看一定有其标准,比如通过观众的眼睛和表情来判断。于是,面对他们的双眼,我心生忧虑,害怕有失误,害怕被笑话,学舞色变。
和跳舞一样,当理性作用于偏艺术性的领域时,灵感、直觉、敏锐、甚至癫狂——这些艺术最需要的力量开始消减,能否创造出富有感染力的作品便不好说了。不少作家喜欢在深夜或者凌晨进行创作,此时众人皆睡我独醒,静谧、专注赋予了想象自由。更重要的是,面对深沉夜空,理性逐渐睡去,感性被唤醒,催生了源源不断的灵光和妙笔。
已长大成人的我,此生,还可以重新迈出舞步吗?我不知道。但肯定的是,若一刻不丢掉“理性”,我就一刻也舞不起来。
在社区里散步,会经过一两家舞蹈馆、青少年街舞馆。如果我的孩子未来想学,我定会支持她——让她多一种在这世间表达自我的方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理性重要且必需,但若只剩理性和逻辑,相当于我们的世界只有黑白两色,其他色彩被抹去,这绝对不是我们愿意生活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