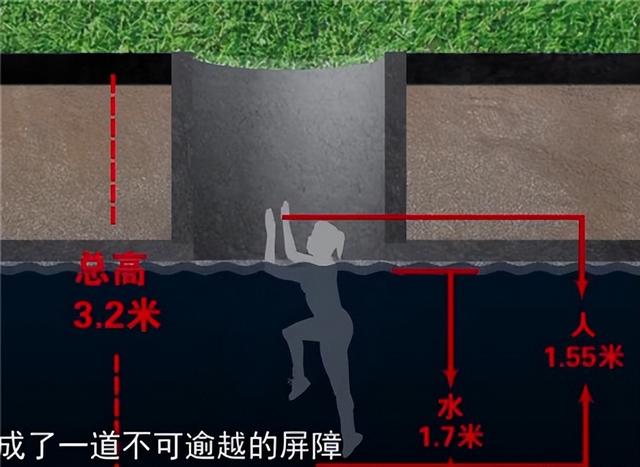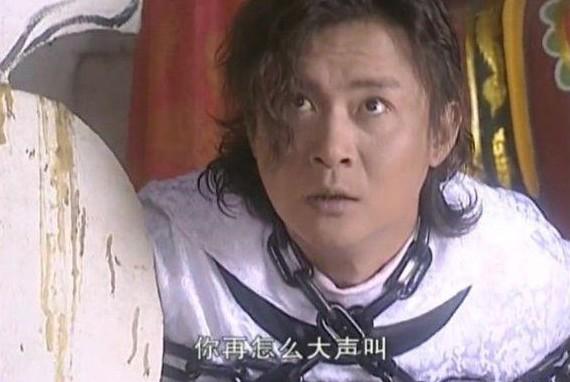|
|
|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东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文:徐立帆
1600多年以来,这里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180多年以前,这里是海上国际贸易的闸门,是通向南中国内河航道的钥匙;40年以来,这里是中国制造的重镇。
今天,这个城市站在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新经纬线上。它用“一核三带十区”为自己导航,用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为自己定位,在广深港澳四大城市的环绕中再次跨越,进行着戈特曼所谓的新“荒野驯化”。
再造东莞,正逢其时。
180年前,东莞是湾区胚胎的中枢
吃水深的外国商船按规定停泊在位于澳门东南凼仔岛的泊地。在得到粤海关监督的批准后,商船才能在澳门引水人的领航下,驶入漫长而低浅的珠江航道。在珠江航道,所有船只都需先经过珠江口东岸的东莞虎门的税馆。虎门税馆核对船长姓名等信息,给引水人颁发行船执照。手续完备后,两名官员登船随行,一名来自虎门税馆,一名来自虎门军事炮台。他们的任务是监督商船不会中途装卸货物,同时在遇到危险情况时召集珠江巡逻水师驰援。
商船经过两到三天的航行,抵达距离广州旧城20千米的黄埔锚地。这是个优质而又安全的停泊地,可以抵御猛烈的台风侵袭。虎门随行官员将监督工作移交给广州当地官员。广州当地官员被商人们习惯性地称作“JACK HOPPO”或“HOPPOMEN”。“HOPPO”就是“户部”的音译。他们称量商船货物,监督货物分装搬到“官印船”上,再分发到广州。而在广州城里和黄埔锚地水面,行商、通事、买办、屋主早已等候。他们操着混杂了英语、葡萄牙语、荷兰语的“广州英语”,在中外两端奔忙,缴纳港口费并做保,解决商船停泊期间琐碎的生活事务,给商船补给、修复,购置商人们回程或另行香港时所需的茶叶、瓷器、行销画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这是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南中国对外贸易的常见场景。这一场景以澳门为起始,以广州为中心,以香港为后备,在大约150年的时间里,粤港澳支撑起了中国最重要的生意。三地在珠江水面形成的机制化合作通道,塑造了早期的湾区胚胎。
不难看出,借助虎门的重要地理位置,东莞在近180年前粤港澳的湾区胚胎中,起着中枢作用。它既是海上安全的门户,也是中国打开国际贸易之门的钥匙。这一作用,随着汽船的发明、香港的开发、早期广东贸易体制的嬗变才渐告终止。
不过,历史机遇有时不止降临一次。2017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正式提上国家议程,东莞迎来了180年以来的最好机会。东莞不只有悠久的开放经验,其地域人文特性,北接广州、南连深圳、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要素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累,在新机遇里都足以释放出来,成为用以再造东莞的矿藏。
东莞在粤港澳大湾区这幅新画卷前的第一笔,将如何书写?
戈特曼的“人文”起手式
半个多世纪前,法国有个地理学家戈特曼对北美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全球最大、最发达的城市群感到好奇。他考察了一系列大城市,得出的结论是:城市化的本质就是荒野驯化。在北美荒野上建成全世界最发达的城市群的原动力,首先不是来自经济,而是来自清教徒们的使命感和对建国理念的孜孜追求。这个结论很法式,很缺乏经济理性,但却激发出了后来的城市带规划理论。美国城市发展规划就根据戈特曼定义划分成了14片区域。
粤港澳大湾区九市二区的发展历程自然与北美大城市带不同。粤港澳城市带不是在荒野上拔地而起,包括东莞在内,多是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浓厚的历史记忆积淀。虽然如此,仍可向戈特曼学习。戈特曼在考察北美大城市带后提出,城市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现代城市必须以城市系统、城市网络视之,而人文是这个系统和网络发展最重要的一环。面对未来,只谈经济不谈人文,注定有基因缺陷。
东莞在人文建设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东莞位处岭南文化中心区,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历史上中原鼎沸之时,岭南就是中原文化的寄存之所。具有东莞背景的杰出代表人物,也因此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和精神产品。东莞人袁崇焕“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悲壮至今为后人缅怀;出生于东莞的张穆“千古遗弓终抱恨,十年磨剑尚如新”的壮志迄今可感激昂。遗民精神、对中原文化的坚守捍卫铸造了东莞的文化底色。这也使得东莞与广州结成了牢固的文化共同体,在文化表达、生活方式、传统延续等方面共情共鸣,在文化上更亲近广州。
如果说在历史的东莞呈现出厚重的遗民文化特质,如今的东莞则更多呈现出多元包容的移民文化特质。这从人口分布就可以看出来。东莞常住人口约839万人,其中非户籍人口就有607万人。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34岁,15~45岁的人口占80%,年轻指数居全国第14位,人口吸引力居全国第5位。此外,还有大量的非常住人口在东莞从事阶段性工作。东莞的人口比例与其南面的深圳接近。深圳常住人口约1077万人,其中非户籍人口约710万人,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33岁。此外,还有近1000万的非常住人口。
相近的人口结构折射的是东莞与深圳两城经济的同构。两城之间业已形成了交通潮汐结构,深圳外环横穿东莞塘厦、凤岗,“莞深同城”正在变成现实,东莞自然而然成为深圳产业外溢的首选地。包括华为、富士康、大疆等深圳企业批量迁至东莞,使东莞与深圳结成了牢固的经济共同体。因此,东莞在经济上与深圳较为接近。
文化上亲近北面的广州,经济上亲近南面的深圳,为东莞文化的融合和裂变提供了新机会。打好人文手式,向内继承岭南文化传统,向外引进新型文化理念,东莞有机会在文化上成为广深之间的枢纽,进而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重镇。这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能够为东莞塑造新的城市品格,为未来的发展筑好人文基础。
(文、图摘自《风物中国志·东莞》,由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