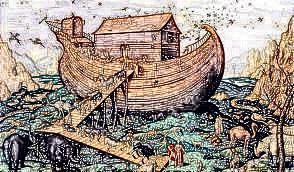我们中学学历史的时候就背过“歌德代表作《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
那时候挺好奇的,能被史书记载的小说,那该是怎样伟大的作品呢?
由于学业繁忙,虽然也读了历史书提到的某些书目,但是终究不能一一读完,年过不惑的现在,昕玥把那些如雷贯耳的书一一找来,一来是为了弥补少年时期的遗憾,二来想甄别一些书给孩子看。
坚持了些年,昕玥还真发现自己是对的,有许多被奉为经典的书,其实还真的不适合给心智不成熟的孩子看。

昕玥发现,去年读的《局外人》和前不久刚刚读完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就是如此,如果不加引导地随便丢给懵懂的孩子去看,可能真的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之前的《局外人》,主人公是一个非常消极冷漠的人,但是豆瓣书评中就有好一些读者对主人公非常深情地颂扬,以及深度与之共情,昕玥那时候想,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估计是顶年轻的人吧,也许中学生,也许大学未毕业的孩子。
同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据译者说,在当年出版火热的时候,就有年轻人读完后深深认同主人公的所作所为所想,于是模仿他走向自戕之路。
经典虽然经典,但是如果没有理性的理解和吸收,读了书未必就有益了。
就像死亡之曲《黑色星期五》,据说极其动听,撼动身体所有细胞,但是听了的人都会忍不住想死,“好“的东西未必有好的影响。
这本书的优点在于,第一,句子很优美,许多对事物的描绘都非常精彩,读到风景描写时,你像看到一幅让人愉悦的美丽风景画;读到情理分析时,你又会看到一段精辟的哲理见解;读到心理描述时,你又像感同身受,陪着书中人物一起惬意、苦闷、激动、悲伤和绝望。

感染力是一个作品成功的重要成分,然而,它对于读者来说并非全然好处,《维特》便是如此,它所呈现的消极一面,往往会给感性的读者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
昕玥觉得,这本书有两个方面会使之不适合广为普及,至少不是那么适合推荐给青少年。

据说歌德对卢梭有崇拜之情,《少年维特的烦恼》就是模仿了后者的《新爱洛伊斯》,采用了类似的书信体和展开方式,思想上亦有所追随。
卢梭的主要思想是崇尚自然,剔除人的社会性去追溯人的自然本性,他个人也身体力行,喜欢避开尘世躲到冷僻之处,屡屡拒绝加官进爵的机会。
歌德笔下的维特也是如此,他有一身才华,也被人赏识,被推荐到政府系统就业,但是他不喜欢繁文缛节,不喜欢虚与委蛇,不喜欢觥筹交错,他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呆着,听听不幸之人的诉说,画画被遗忘在树荫底下孤寂的农具,逗逗天真无邪的孩童。

从字面看,这样的人是值得赞美的,高洁、文雅、清新脱俗而让人敬佩。
歌德的文字功底确实很厉害的,他把绝大多数的读者带进了这样的意境之中。
但凡你能清醒一点,你会觉察,这样是不对的,维特是个年轻有为的人,他不是富二代,一来他有成就一番事业的必要吧——一个学有所成的青年怎么没有人生理想,或者至少对未来所有憧憬呢?
二来他得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吧?他父亲早死,还有个妈要养呢。
维特厌倦他那份公职(最终还放弃了它),与其说是遇到不好的上司,或者说周围的人不好相处,还不如说是他就是不想上班,他不想做任何事,不想面对任何烦恼,不想承担任何责任。
他就想无忧无虑地呆着,胡思乱想一番。

这样他可以毫无负担地、从容优雅地生活,失恋的路人来了,他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孤苦的穷人母子来了,他可以做一个伟大的施舍者,这种感觉让他特别满足而快乐。
多么高尚、神圣而完美啊!
歌德不呈现维特在生活上的烦恼,于是就给了读者一种错觉,会觉得他不上班挺好的,生活自由自在,而不用去应付那些“人性卑劣”的同事圈子。
但是现实不是这样的,经历过甜酸苦辣的人们都知道,也或者我们读读卢梭的平生简介也能知道。
卢梭自诩不愿与上流社会的人为伍,他厌倦社会性的东西,他要崇尚自然,喜欢未经人类破坏的东西,于是多次隐居在乡下。

可是他真的隐居得了吗?
事实上,即便是他所谓的隐居,靠得也是上流社会富人的施舍,无论是在沙尔麦特村还是退隐庐,都是别人的私产。
纵观卢梭的一生,都是在不停地拒绝,然后又不得不舔着脸向有钱有势者求助,如此过活,跟他一起的女人过得很苦,生下的孩子也全部被抛弃。
人生一世,你再不喜欢也要去适应啊,谁又能一生下来事事都随了自己的心愿呢?
社会是由人支撑起来的,谁还不是构成社会的一分子?为什么别人都能适应而你不能呢?
而那种把一大群人都说成不好的,唯独自己是清新脱俗,从另一面看,未尝不是个人的不合群,换言之,也许问题只出在个人身上。
说到底,维特或者卢梭,都是喜欢逃避实现的人,不敢面对现实生活的困难、挫折,总是设想某处某地会有一个世外桃源等着他们。
而卢梭至死没法承认的是,尽管他总是想逃避这逃避那,终究还是靠写出了作品获得了人的关注才有了身后名。
当然,你可能会用到另一个概念来反击我,说他们所处的社会腐化了,所以上流社会的可鄙之人比可敬之人更多,他们作为清流,无法与之同流合污,因为避开,实为反抗。

可是,在混乱不堪的社会状态之中,为何屡屡会有人能成就一番事业、实现个人价值呢?
比如晚清的李鸿章。
说到反抗,昕玥便来说说自己对这本书的第二个质疑。
二是把厌世的合理性传递给读者,美其名曰为一种反抗精神《五月二十二日》人从某些探索结果中得到的自慰,其实只是一种梦幻者的怠惰,正如一个囚居斗室的人,把四面墙壁统统画上五彩缤纷的形象与光辉灿烂的景物一般……
《五月三十日》然而诗也罢,场面也罢,田园牧歌也罢,统统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们亲身经历了自然现象还不够,还非得来一个依样画葫芦不可么?
《七月十八日》这世界要是没有爱情……就如一盏没有亮光的走马灯。
《七月二十日》世界上的一切事情,说穿了全都无聊。
《一月二十日》我闹不明白,我干嘛起身,干嘛就寝。
以上是摘抄书中的部分语句,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这位笔者精神世界极度空虚、对人生世界非常厌倦和绝望。

所以当维特爱上了一个女子的时候——发现了爱情能让人热血沸腾以后,觉得人生如果有爱情还是能鲜活起来的,如果没有爱情那就完全没意义了。
而他所选择的这份爱情却是无法获得未来的,因为那位女子对他不做出实质性的回应。
她对他热情,对他友好,对他微笑,对他的爱意全部笑纳,但是一如既往地和未婚夫婿谈婚论嫁,憧憬自己的人生未来,而与他无关。

没有了爱情,毋宁死——维特为了给自己的自尽行为添加壮烈和勇敢的色彩,与情敌阿尔伯特进行过无数次激烈的争论,常常把话题引到“自杀是一种英雄式的行径”的旌旗上。
那种说辞,仿佛真有种这位青年男子为了爱情、为了他所看不惯的社会现状,他要以生命为代价去作出反抗。
这本书的官方解释貌似正是这样的。
但是昕玥依然不以为然。
什么才是抗争?难道只要有死亡都能归为抗争一类?
不是的。
昕玥觉得,不管有没有以死亡为代价,或者不管有没有彻底改变什么,你做的事至少对所反对的事物是有冲击力的,这才算是抗争过。
就像孙悟空,不满被强者镇压,打到天庭打入地府,最后被囚禁了五百年,但是他“齐天大圣”的名声深入人心,哪路神仙听到这名头都要对他几分敬畏,做事都得给他几分薄面,这就是冲击力。

又说《简爱》中的简爱的抗争精神。
简爱不满舅母对她的欺负和蔑视,从被送到寄宿学校之后就坚决与之亲情割裂,即便几次濒死(差点饿死病死)也绝不回头,结果舅母临死的时候谁也不想见,偏要见她,道出了心中对看起来弱小的她的倔强与坚决态度的震撼。
再说荆轲刺秦,仿佛是很自不量力的行为,失败后死得很惨,但是他能让秦王“目眩良久”,此后再也睡不好一个安稳觉,而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更成为千古豪壮之歌。
这些才是抗争吧!
什么叫反抗精神,或者什么是抗争,其实我们心里是明白的,但是有时候就会被所谓的文学手法给带偏了,把《白鹿原》的田小娥的堕落、把《局外人》的默尔索的感情冷漠、把《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维特的厌世等等,也称之为反抗精神……昕玥不知道这都是在反抗些什么,又产生了几分效果?

当然,昕玥也不会说这是一本不好的书,毕竟能载入青史的作者和作品,它能差到哪里去呢——它肯定不是差,而是对某些人或人群未必合适。
说拿破仑戎马倥偬之际,身边常常带着这本小书——这书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也或者说不准这纯粹是某些人的个人爱好,拿破仑恰巧是那某个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