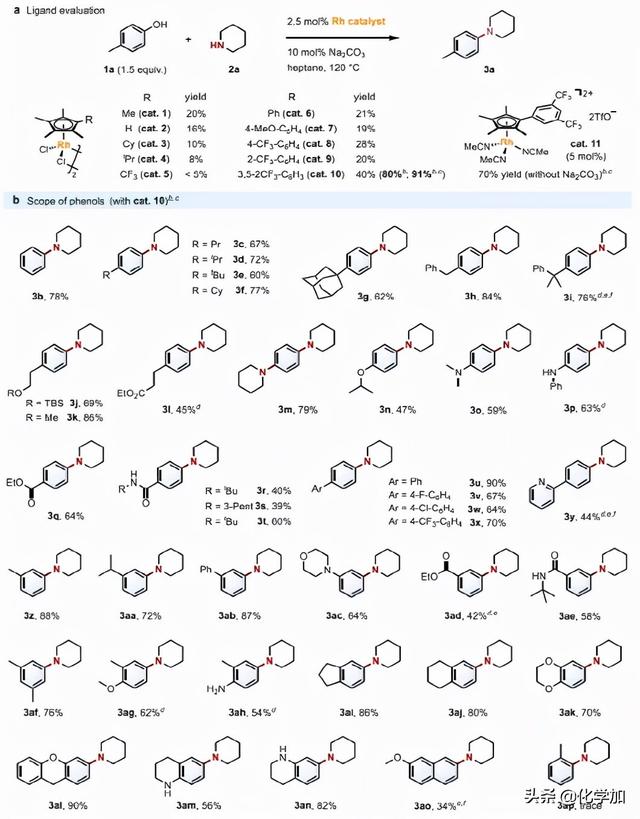聂赫留朵夫也和所有人一样,由两个人合成。一个是精神的人,追求的是自己也能使别人幸福的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幸福,而且为了自己的幸福不惜牺牲全世界一切人的幸福。
列夫·托尔斯泰是文学史上灿烂的巨星,其代表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都是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经典,而尤以《复活》被学界公认为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巅峰之作,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故事以“复活”为主题,讲述了男女主人公精神的复活、人性的复活,其中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事迹特别震撼人心。然而,这部作品主旨却并不止于“复活”,作品中的庞大叙事多呈现了当时俄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封建社会的多重现实问题。
1、人性的复活
《复活》,以女主人公卡秋莎最初的不幸遭遇为导火索,牵引出一系列的有关男女主人公精神、情感的变化,升华“复活”主题。我们且透过人物来感知。
①聂赫留朵夫的双重人格:精神的我,兽性的我
《复活》第一部不止一次地提到聂赫留朵夫的矛盾人格,即精神的我,兽性的我。
当我们刚开始进入故事,免不了会讨厌聂赫留朵夫这个角色,因为他对待卡秋莎的方式,更因为他作为贵族阶级十足的狂妄和理所当然的优越感。但是,随着故事的深入,我们便不难发现,其实自打一开始,聂赫留朵夫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面人物。
首先,他第一次见卡秋莎的时候,他是一个朝气蓬勃、无牵无挂、胸怀远大且直爽的年轻人。那时他是为了写土地所有制的论文来到姑妈家,并且当了解到土地私有制的残酷和不公,便立即把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土地分给农民。
而后,他第二次来到姑妈家,虽然他的精神人格已经发生很大的改变,但当再次见到卡秋莎并且情不自禁对她产生邪恶想法的同时,心灵上也是经历了一番争斗的。
很明显,虽然聂赫留朵夫的人性发生了质的改变,却不能将他与那些自始至终装模作样、不可一世的达官权贵混为一谈。正因为他本性的不同于人、本性的善,才在他的心灵当中反复地出现“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的相互较量。
当他斟酌再三决定不再相信自己而去相信别人,去做所有人都去做的事情时;当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渴求诱奸了卡秋莎一走了之时,兽性的人打败了精神的人。而当十年过后,他在法庭上遇到卡秋莎并亲眼见证了她的悲惨境遇,他的良心备受谴责,内心深处经历了复杂的思想斗争后,精神的人终于复活了。
在这个过程中,他为了卡秋莎以及监狱里的其他无辜者在上流社会奔走,虽然颇受周围人的非议、困难重重,但都没能使他体内兽性的人抬起头来。
聂赫留朵夫精神的苏醒虽然因卡秋莎一人而起,伴随其中的却是广义的社会认知和截然不同的人生取舍。他为了赎罪、减轻卡秋莎的痛苦,决定放弃贵族身份,和她结婚一同去西伯利亚;他也为自己之前对待农民的方式感到羞愧,再次与他们交涉土地所有权问题;他厌恶之前的生活,更厌恶曾经交往的圈子,那些贵族、官僚、上流社会人群,装腔作势的丑恶嘴脸赫然呈现在他的面前,使他急于摆脱。
精神的人一旦苏醒,周围的一切都随之发生了质的改变。
②卡秋莎的世界观,迷失与复活
和聂赫留朵夫一样,卡秋莎也经历了一次人性的迷失与复活。
迷失,是在她遭遇聂赫留朵夫的诱奸与抛弃,之后,又经历了一次次的被人利用与欺骗,走投无路,她离开了眼下那个她又恨又不理解且让她受尽折磨的世界,沦为妓女。
但她无疑是个善良、清纯的女子,尽管她经历了八年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生活。无论是在妓院里,还是在监狱里,她都赢得别人的好感与关爱。尽管在监狱里她的妓女身份和美貌引得各色各路的男人纠缠不休,但女人们不论老少,都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对她冷眼相待。
书中有一段关于盗贼、凶手、奸细、妓女的世界观的文字很是令人动容,足以引导我们不只同情他们的遭遇,还会认同他们的观点。也是在这个观点的支撑下,玛丝洛娃仅以自己囚犯的身份为耻,反以妓女的身份为荣。
以前的卡秋莎已不复存在,只剩下现在的玛丝洛娃,卡秋莎精神的人的彻底迷失,很是令聂赫留朵夫震惊。
好在,她的迷失在聂赫留朵夫出现不多久就结束了。因为她重新爱上了他,她愿意去做他喜欢让她去做的任何事,更愿意成为他想让她成为的人。她的精神的人因着聂赫留朵夫的再次出现,因着他的赎罪快速地复活了。
故事最后,两个人并没有走到一起。玛丝洛娃因为爱而放手。从最初的她在牢房里第一次见到聂赫留朵夫时,一心想利用他、向他要钱,到最后她宁愿装作不在乎什么爱不爱的,和政治犯西蒙松结婚,而不让聂赫留朵夫牺牲自己,和她一起生活,这种精神的人的质的转变已经不能称之为简单的“复活”,而是它的一种飞跃与升华,达到了崇高与至美的境界。
2、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对社会、对人生的批判及希翼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当时社会的原始面貌,意在揭露现实的同时,改造世界。
毋庸置疑,从某个层面上,聂赫留朵夫就是托尔斯泰本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他情感和思想的载体。下面让我们通过聂赫留朵夫,来了解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认识。
①贵族和官僚
聂赫留朵夫本身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当他在官场和监狱间自由游走,我们看出他独有的、充分的优越性。
他的身份是公爵,居于五等爵的第一等。加上他的财产以及家族在上流社会的人脉,他为监狱里的无辜者、受苦受难者办起事来大多时候畅通无阻。但是,这个过程同时也展现出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丑恶嘴脸。
贵族的生活穷奢极欲,那些无所不在的浮夸的排场与奢华,除了刺激肉体、麻痹精神之外毫无用处;而官僚的不作为,他们的麻木不仁、贪赃枉法,他们的残酷与荒谬,除了带给劳动人民无尽的苦难之外,剩下的也只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一出出闹剧罢了。
聂赫留朵夫一方面宁愿舍弃一切,离开家,去旅馆租两间带家具的小房间,以彻底远离以前的圈子。另一方面,为了玛丝洛娃的案子他又不得不在这些人之间周旋游走,奔波求情。
这些人当中有他早就百般厌恶的人,也有他曾经的战友、同学,甚至还有亲戚和朋友。但是,在这些人当中,无论是卑鄙虚荣的家伙,还是真诚正直的人,一旦进入官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被这个体制同化,携手步入贪欲和残忍那万劫不复的深渊。
②法律和监狱
法律和监狱,是《复活》重要的表现元素。当权者的无道,囚犯们的苦难,老百姓的贫困,曾不止一次的使聂赫留朵夫先产生生理上的恶心感,继而又产生精神上的恶心感。
在聂赫留朵夫帮助罪犯、查访监狱、平反冤案的过程中,那些省长、参政管、检察官、法官、律师,那些典狱长、军官、警察、押解官,那些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先生们,本着维护正义、教育人民的准则,他们上下齐心的表现令人汗颜。无罪的人遭不遭殃,对他们而言都无所谓,他们担心的只是如何清除一切危险分子。
而监狱里面的无论刑事犯、流放犯、苦役犯、政治犯,就聂赫留朵夫看来多半都是遭诬陷,或是被冤枉的。即便是真正的罪犯,也是他们身处的那个环境的结果。是无以为生使他们走上歧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先对他们犯下了罪过,而社会对他们犯的罪远远超过他们对社会犯的罪。
而社会对他们反的罪,则是首先剥夺了他们的一切,将他们置身于产生不幸之人、产生罪犯的环境里,再制定出法律,将逾越者绳之以法。要是他们先定出法律就好了。
这样的社会现实,使聂赫留朵夫惊讶且困惑——究竟是我疯了,所以才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还是这些人疯了,所以才做出我看到的那些事?
故事最后,聂赫留朵夫似乎在英国人送他的《福音书》中找到了路,并且为着自己的信念矢志不渝地继续努力。
③土地私有制
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使劳动人民受尽了剥削与苦难,这一不言自明的观点对于地主阶级而言,是很难从容接受的。
而聂赫留朵夫是个例外。当他意识里那个唯一正确、唯一强大、唯一长存的不受任何摆布的精神的人觉醒的时候,他便对自己对待土地的方式深深自责。他要斩断一切不应有的关系,自由地呼吸。
土地不是任何人的,是上帝的。所以,他决定不再霸占土地,放弃土地所有权。他先后来到自己的两个庄园,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把土地还给农民。
当他想到以前生活的圈子,他们的舒适和享乐,是建立在农民的疾苦之上,再眼看着自己庄园里的农民忍受饥饿和病痛,便切身感觉到那种奢华生活的残酷性和罪恶性了。
所以,尽管他放弃土地所有权的事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仍然认定自己做出了正确且光荣的选择。
④宗教与教会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曾为了一个教派信徒的案子而奔走。这是一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他们曾多次受到官方告诫,事后又遭到过度热心教务的省当局流放。
而在聂赫留朵夫看来,这种行为无非是当局为了维持他们所统治的社会的安定,而想方设法将人们禁锢在浑浑噩噩的愚昧状态之中。
书中有多处地方提到人们儿时所信宗教的愚昧性。特别强调的是监狱里面为囚犯们而设的宗教仪式,以及那赫然在目的基督像,放在以各种手段折磨人的地方,像是专门为了嘲笑基督教义而存在。
其实,聂赫留朵夫明白,宗教,特别是教会存在的意义,不过是统治者欺骗和奴役人们、维护专权的工具罢了。
那么,到底有没有上帝?托尔斯泰通过一个流放老头子来作答。
即便有上帝,他也只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就是因为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各人相信自己的灵魂,也就不必分什么门什么派了。人人都相信自己,人人都问心无愧,大家就成一家了。
⑤任何人既无权惩罚别人,也无权改造别人
其实,说了这么多,作品的主题除了“复活”外,作者想要表达的就只有这句话了——任何人无权惩罚任何人,无权改造任何人,无权奴役任何人。
就像作品最后聂赫留朵夫通过《福音书》所了悟的那样,凡自己谦卑的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而只有尽可能降低自己身份的时候,才能领略到生活的安适与快乐。
那个没有名字、不知年龄、不要国家的老头子告诉我们,上天就是父亲,大地就是母亲,自己相信自己,自己做自己的皇上,自己管自己,也就用不着当官的了。
于是聂赫留朵夫终于明白,战胜可怕的、使许多人受苦受难的恶势力的唯一可靠办法,就是人人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总是有罪的,因此既无权惩罚别人,也无权改造别人。
3、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妓女”形象现实生活中,“妓女”这个行业一直存在着。在我们的心中,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就仿佛是文明社会的毒瘤,时时处处蛊惑人心,毒害社会。就一般人而言,尽管在朦胧中能觉察出她们生而为人的不易,但在心理上仍然对其充满鄙夷且难以接受。
然而,不止一次的,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得以深入了解“妓女”形象。而几乎无一例外,她们都是被作者作为正面人物来描述。所以,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先前对于“妓女”的看法也稍稍改观。
比如莫泊桑《羊脂球》中的羊脂球,小仲马《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雨果《悲惨世界》中的芳蒂娜,还有《复活》中的卡秋莎,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从事不正当、不光彩职业的女人,在作品中都是纯洁、善良的。
她们之所以堕落是因为她们的贫穷,更因为她们所处的社会。玛格丽特、芳蒂娜与卡秋莎,她们的境遇大同小异,同属于柔弱的穷苦之人,为了自己或家人的生存被迫走上堕落。而羊脂球,虽然莫泊桑没有在作品中提及羊脂球的身世和遭遇,但单就她的善良、真挚,对国家的忠贞来看,就足以说明她是一个正直的人,而非没有道德、没有灵魂之人。
但她们善良的本性似乎注定了被命运束缚,这四人当中除了卡秋莎是幸运的,在聂赫留朵夫以及周围人的感染与帮助下,最终脱离泥潭步入入正途。
其他人,玛格丽特和芳蒂娜,直到到生命的终点灵魂才得到最终的救赎。而羊脂球,作者虽只是就事论事,没有交待她的结局,想必也不能乐观。
然而,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便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尽管穷苦之人在旧社会备受摧残、无以为生,但“妓女”在社会中毕竟只占极少的一部分,坚强求生存者乃属大众。
尊严,有时候,真的比生命还要重要。这应该是文学作品透过“妓女”形象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