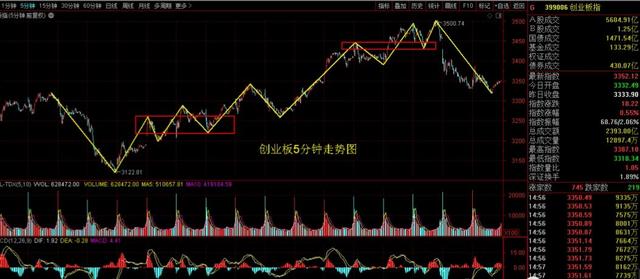汪曾祺是有名的食客,刘伶一样的人,又因一生浮沉漂泊,便带着他那副无所不包的肠胃和心胸,吃遍了大江南北。他晚年在作家的位子上安居,回味那些经口的美食,写了不少色香味俱全的文章。
汪先生《肉食者不鄙》里说,他高中在淮安县中学读过一个学期,熟悉学校食堂。但我的印象,淮安菜他只提到过两次半:一次狮子头,《肉食者不鄙》第一句就说“狮子头是淮安菜”;一次是《鱼我所欲也》里的“干炸鯚花鱼”和鳝鱼;那个半次,是《豆腐》里的干丝,“淮扬名菜”,所以只能算半个淮安。说实话,汪曾祺先生对淮安菜着墨太少了,与淮安菜的地位不符,2021年淮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美食之都”,和之前入选的成都、顺德、澳门、扬州平起平坐;但私下里又不得不承认,淮安在美食上的名气,远逊于这四个城市。
淮安美食品类繁多,渊源深厚,我不是美食家,但也近水楼台,吃过不少,探讨下家乡美食与历史、地理的关系,抛砖引玉,不失为疫情宅家的一大乐趣。

淮安市威海路美食街充满浓浓烟火气。 (IC Photo/图)
开洋蒲菜
不知道其他地方现在还有没有用蒲草作食材的。若是来淮安,春夏两季可以吃到蒲菜,尤以端午前后为最佳。选蒲茎近根处切段,长二三寸,亦可长一拃许,笔管粗细,清蒸或荤烩后,撒虾米过油,盛放于浅盘中,即得。蒲段洁白如玉,嫩脆爽口,食后齿颊留香,如沐春风,真真虽万钱珍馐不易也。
这据说是一道“抗金菜”。南宋梁红玉随丈夫韩世忠抗金,驻守家乡淮安,军粮短缺。她见战马啃食勺湖边的蒲茎,自己试吃后命军士采食,解了燃眉之急,事后淮安便有了这道菜。
其实蒲茎可食古籍早有记载,并不是梁红玉的首创。《诗·大雅·韩奕》有“其蔌维何,有筍及蒲”的句子,那么,至晚在西周时候,北方的国人就已经将蒲入菜了。汉初淮阴人枚乘的《七发》也有“犓牛之腴,菜以笋蒲”的说法,这大概是淮安食用蒲菜最早的记载。看来只有淮安把它传下来了,因为我在别处没有见到过。汪曾祺是高邮人,其乡离淮安只一百多里路,他《故乡的野菜》提到多种野生的菜蔬,却没有蒲菜,很能说明问题。
蒲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淮安河、湖众多,几乎随手可得。我在洪泽湖边见过人在自家门前采蒲。那真是极卑贱的东西,有点水就能生长,却能给人美好的满足。
古人蒲菜的吃法似与今人不同。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里说:“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啖之,甘脆。煮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笋法。”“开洋蒲菜”则是淮安人的创造。我起初不明白“开洋”是什么意思,问了不少人也无果,后来查《辞海》竟然查到了,是江浙某些地区的方言,指虾米,这就是了。
我建议以后注释《诗经》的时候,在“蒲”下加这么一条:“今江苏淮安地区仍以蒲入菜。”现存的证据,岂不比引经据典更有力?

开洋蒲菜 (雷夫/图)
文楼汤包
人多以为汤包是扬州食品,谬矣。还是扬州人朱自清先生的《说扬州》道明了真相:“北平淮扬馆子出卖的汤包,诚哉是好,在扬州却少见;那实在是淮阴的名字,扬州不该掠美。”
淮安汤包,以河下镇的文楼最有名。所谓汤包,就是薄薄的面皮儿包着些汤汁。虽说猪肉、鸡肉皆可为汁,但以蟹黄为最佳,所以吃汤包的最好时节是每年“桂花飘香菊花黄”的时候。
汤包要趁热吃,但又要谨防烫嘴,因为油很热。“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说的是吃汤包的方法。那时的汤包是用蒸笼端放到食客面前的,先要小心翼翼将汤包由蒸笼转移到盘碟,再用筷头夹破面皮,噘嘴凑上去喝汤,整个过程,就像从摇篮里抱起一个娇弱的婴儿,低头去亲吻。现在则是汤包先放在小碟里蒸熟,连小碟一起取出,而且用吸管了,这对恋旧的人来说,好像少了一点意思。但好歹都是喝汤。在文楼坐下,只听周围一片“咝咝咝”吸汤的声音。喝汤不出声的绅士淑女们,你们在这里可以放肆!
文楼在淮安区河下镇花巷69号。始建于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叫文楼,是因为还有一座武楼在对面。这两座楼是为了纪念河下镇出来的一文一武两位状元,文是明嘉靖年间的沈坤,武是明万历年间的叶允武。武楼今已不在。文楼以文名,也的确是文人汇聚之处。河下是运河重镇,江南的举子进京会试,常常在这里泊舟,加之河下自古文风很盛,所以文楼有“文友文心文趣,宜茶宜酒宜诗”之誉,驰名江浙。
文楼素有赌对侑觞的风习,就是对对子,对不出的喝酒,对出来了出题的喝,倒也是一件雅事。据说某年来了三位岭南才子,多日未逢敌手,十分得意。不料有一当地村姑在文楼吃饭,信口出了句上联道:“小大姐,上河下,坐南朝北吃东西。”三才子抓耳挠腮了半晌,想不出来,只得一拱手道:“请容我等三思,明日当来奉教。”村姑一点头:“好,明早我还来吃饭。”三才子回到下处,辗转反侧了一夜,还是求之不得,趁着天不亮,收起书箧买船逃走了。
这故事或者是个传说,而这一句上联至今还悬在文楼的院墙上,等着下联呢。才高八斗的读者诸君,你们要不要也来文楼试试?
“小大姐”是淮安方言,指半大不小的女孩子。

河下文楼 (雷夫/图)
茶馓和干丝
淮安区到处有卖茶馓的,岳家茶馓、顾家茶馓、高家茶馓、陈氏茶馓……岳家茶馓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陈氏茶馓是清真的。
茶馓据说在战国时期就有了。是将醒过的精白面拉成麻线粗细,在热油中盘曲炸制而成。形如发梳,色泽金黄,香酥松脆,是“打嘴都不丢”的淮安小吃。
茶馓与普通馓子不同,不仅在于它细得多,精巧得多,更在于一个“茶”字,说白了,茶馓是茶点,是为早茶而生的。
江苏的早茶以扬州为盛。“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说的是过去扬州人惬意的生活习惯。“水包皮”是泡澡,“皮包水”就是吃早茶。受扬州影响,里下河地区的泰州(原属扬州)、盐城,淮安最南端的淮安区也有吃早茶的习惯,我推测这是茶馓的由来。

淮安茶馓店 (雷夫/图)
淮安地区南北饮食习惯有不小的差异。大体上说,古淮河以南的淮安区、金湖县、盱眙县,吃食较精致,接近扬州,以北的淮阴区、涟水县,吃食较疏阔,接近徐州。以主食为例,古淮河以南吃米多,以北吃面多;以南的面食多小巧、柔软,以北多粗厚,有嚼劲,需要好牙口。吃过淮安区的茶馓,再去涟水吃“朝牌”(一种形似笏板的多层烤饼),就能感受到这个差异。这似乎应了晏子的那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好像一条淮河真有那么大的魔力。但我推想这与淮安的历史有关,因为南宋正是在淮河一线,与金、蒙古对峙了一百五十年。但这一百五十年的隔阂,足以造成这个差异,并延续七八百年之久吗?这个问题我无力回答,还是留给民俗学家吧。
以上是扬州饮食习惯对淮安吃食的影响,其实淮安的饮食也会反过来影响扬州。
烫干丝是扬州茶馆里吃早茶的必备闲食。汪曾祺先生在《豆腐》里写道:“干丝是淮扬名菜。大方豆腐干,快刀横披为片……再立刀切为细丝。……干丝入开水略煮,捞出后装高足浅碗,浇麻油酱醋。青蒜切寸段,略焯,五香花生米搓去皮,同拌,尤妙。”
但写到这里,汪先生笔锋一转:“我很留恋拌干丝,因为味道清爽,现在只能吃到煮干丝了。”
煮干丝又名“大煮干丝”,是淮安菜。将切好的干丝下母鸡汤,加虾米、火腿丝、笋丝,可放青菜叶。大煮干丝现在也是扬州名菜。汪先生虽然恋旧,却也不厌新,常亲自下厨做煮干丝,成了“保留节目”。
干丝从拌到大煮,从喝茶的闲食到“管饱”的菜,可以反映生活方式的变化——人越来越不得闲了。
淮鱼淮白
淮安自古产美鱼。《尚书·禹贡》有“淮夷蠙珠臮鱼”句,是说夷人所居的淮水下游一带,出产蚌珠和鱼,用作贡品。淮鱼最著名的,当数淮白。查《辞源》,列“淮白”一条,可知其见于古籍之多,而举的例子,有南宋杨万里《初食淮白》诗句。因杨诗正好提到了淮白宋朝时的吃法,所以录在后面,稍作解释。全诗云:
“淮白须将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违。霜吹柳叶落都尽,鱼吃雪花方解肥。醉卧糟丘名不恶,下来盐豉味全非。饔人且莫供羊酪,更买银刀三尺围。”
首联,说淮白产于淮水,当用淮水煮制,这未免有些夸张,但也说明当时的江南,包括国都临安,也是可以吃到淮白的。颔联说秋冬季节淮白最为肥美。颈联讲到淮白的普遍吃法。原来淮白性烈,出水即死,须用酒糟加盐腌制,方可保存、运输。“醉卧糟丘”就是说的这个情况,再加“盐豉”烹调,已经失其本味。杨万里一定是在淮河边吃到了刚出水的淮白,才兴此叹的吧?尾联,说招待金国的使者就用淮白,那可比羊酪鲜美多了。“银刀”是淮白的别称。杨万里淳熙十六年(1189年)曾奉诏到淮安迎接过金使,作《初入淮河绝句》四首,气氛低沉。这样回看首联,像是写淮白,却未必不含有对淮北故土的怅惘之意了。
东坡老饕,尤嗜淮白,有多首写淮白的诗。其《发洪泽中途遇大风复还》说,“明日淮阴市,白鱼能许肥”,表达了到淮阴品尝淮白的期盼。
今天淮安人做淮白,有清蒸、油浸、“风”、生熏数种。淮安水网纵横,当然不只有淮白。淮安的“全鱼席”,多可达一百零八品。

盱眙天泉湖湿地 (视觉中国/图)
平桥豆腐
汪曾祺应该没吃过平桥豆腐,不然一定会写在《豆腐》里。文中提到豆腐庞大的家族和各种各样的吃法,单没有平桥豆腐。平桥豆腐是豆腐切成雀舌状的菱形小片,入菱粉勾芡的鸡汤烹热,加鲫鱼脑提鲜,配以香菇、鸡丝、虾仁、蛋皮、芫荽而成的豆腐羹。
平桥豆腐最早记载于清朝内务府编制的《江南节次膳底档》,说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高宗第四次沿大运河南巡,停舟淮安府平桥镇大营码头用膳,其记曰:“平桥大营码头进晚膳,用折叠膳桌摆:莲子鸭子一品,肥鸡火熏煸白菜一品,肥鸡豆腐片汤一品。”其中的“肥鸡豆腐片汤”就是平桥豆腐。
当地传说平桥豆腐是特为乾隆皇帝创制的,没有依据。从记载看,应该是先有平桥豆腐,后有乾隆皇帝。
今淮安区平桥镇位于京杭大运河东岸,再向南就是扬州的宝应县。平桥宋朝建镇,指桥为名,当时叫平河桥。为什么叫平河?因为运河淮扬段连接长江、淮河,淮河水位高,长江水位低,经运河上多个闸坝调节,运河到平桥这里,水位才与长江同高,所以叫平河。平桥豆腐有“天下第一菜”的美誉,闻名遐迩,但知道平桥的人却不多。
据说给乾隆皇帝贡膳的是当地的官宦林秉直家。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唯一一家饭店平桥饭店就是用的林家的宅院,招牌菜也正是平桥豆腐,可以想见当年的兴隆。如今平桥饭店只剩下一堆颓垣败壁,在风日中萧瑟,令人唏嘘。

当年为乾隆皇帝烹制平桥豆腐的林秉直家,后变成平桥饭店,如今只剩颓垣败壁。 (雷夫/图)
吃平桥豆腐的时候要特别当心,因为它不冒热气而其实烫得很。虽说“一烫抵三鲜”,但还是舀到小碗里等一等再吃的好。
平桥豆腐是淮安“八大名菜”之一。你道是哪八大?——淮安软兜长鱼,盱眙十三香龙虾,白袍虾仁,平桥豆腐,开洋蒲菜,钦工肉圆,朱桥甲鱼羹,蒋坝酸汤鱼圆——皆为淮河以南出品。
丰济仓旁馄饨店
淮安市清江浦区的西大街是一条老街,和东大街一起,是老清江浦最繁华的去处。西大街靠北,有一条南北的小巷,叫草市口。草市口巷头有一家三十多年的“桂氏牛肉馄饨”店,店面不大,三四张简易的小长桌。馄饨味道不错,价格也便宜。两三位中老年妇女好像既是掌柜又是伙计,做事不急不躁,给客人如归的感觉。第一次去,她们就说:“看过丰济仓没有?去看一看,就在巷北。”
原来她们指的是清江浦的丰济仓遗址。丰济仓是明清两代的漕运粮仓,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初名“常盈仓”,与京杭运河上徐州的广运仓、德州的德州仓、临清的临清仓并称为“四大名仓”。漕运粮仓的作用,是汇集周围地区的赋粮,囤积保存,由漕船统一运往北京。
比如清顺治年间,江南每年运至北京的赋粮约四百万担,而经丰济仓进出的就达三百万担之巨。这些粮食先由江南各地经水、陆汇集到丰济仓,再由这里统一漕往北京。每年漕运繁忙的时候,漕船以外的船只一律不得过清江浦北行,只能改走陆路。今天清江浦船闸旁“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古碑复制品,说明了当时的情景。
而江南来的粮船在这里卸载后,也并不空回,河下镇是扬州以北的盐务重镇,往往从这里载盐南下。可以想见当时淮安的繁忙景象:车、船不计其数,每天数以万计的官吏、漕兵、运夫、水手、商贾在这里出入。单从吃的方面说,一定是酒楼、饭馆、食摊遍布。名厨汇聚淮安,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但如此,河道与漕运官员、两淮盐商多蓄有私厨,吃食上争奇斗艳渐成恶习。向官员、上司赠送厨子,也成了“高雅”的贿赂手段。以至学厨成了两淮地区读书之外的第一进身之道。今清江浦的清晏园,是清代的江南河道总督署,里面有一座今雨楼,是河督设宴会客的地方,那里名厨荟萃,奇珍异味不绝于席,极尽奢靡之能事,俨然两淮美食的圭臬。
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北徙经山东入海,运河水量锐减;1860年(咸丰十年),捻军攻入清江浦。由此漕运改由海路,淮安地位一落千丈,大批名厨失所,流落民间。1861年(咸丰十一年),漕运总督兼理河务,驻清晏园。这一任漕督是吴棠,此人出身盱眙农家,反对铺张奢华,要求吃食一律就地取材,不得外购奇珍异味。这原是出于经济和官风的考虑,却深刻影响了淮安菜的风格。
客观上说,官、商招聚名厨,起到了收集、保存、整理、改进民间零散食谱与烹饪技法的作用。名厨流落民间,又让名厨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把口味带给最普通的人。淮安菜,也如同孕育它的这座城市由繁华归于平淡一样,回归了吃食的本真。
“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在桂氏牛肉馄饨店要一碗馄饨,剥两个茶叶蛋,坐上半个钟头,能吃得很舒服。

清晏园,清代江南河道总督驻所。 (雷夫/图)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搁笔了,但自觉还有些不足。因为谈吃食,就该着重写出它的味道,让读者能够感知,甚而满口生津才好。可我自知没有汪曾祺先生那样的才情,又求之而不得他的烟火气,所以这个原本应该由笔尖完成的任务,要留待感兴趣的读者自己用舌尖去完成了。但如果问我淮安吃食的特点是什么,我要说,就地取材,制作精细,存其本味,众口皆宜而已。
雷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