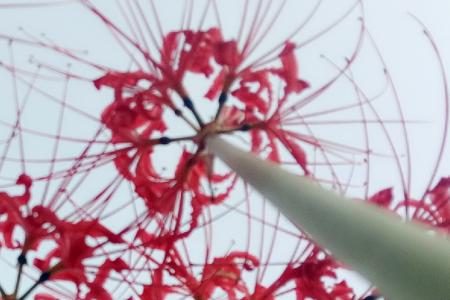河南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民间更有“礼多人不怪”的说法。
在河南,如果一个人待人接物礼数周全,谓之“懂事”“懂规矩”,反之,则遭人贬斥和嘲笑。让人礼作为河南民间通礼之一,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仅从“让人是一礼”这句广为流传的乡谚俚语中,就可以看出它在诸多礼数中的重要地位。

梁永刚 | 文
01
让人是一礼
锅里没下你的米
在河南乡间,让人礼是一辈辈传下来的,没有人刻意去教,也没有人刻意去学。在不经意的见面问候打招呼中,让人礼已经内化为一种习惯,渗透到每个人的骨子里。
可以说,上到九十老翁,下至三岁顽童,让人的话儿都在嘴边上挂着,张口就来。
庄稼人荷锄而归,沿途路过谁家门口,主人总会热情地招呼“歇歇再走吧”或者“拐家喝口茶吧”。
若是饭时,主人正端着碗吃饭,看见有人从门口经过,必然要站起身,放下筷子说一声“在这儿吃吧”或者“吃一碗再走”。
让人,是对别人的尊重,是浓浓的乡情,关乎着脸面,更决定着亲疏。
譬如,赶集赶会回来,庄稼人多少都会给老人小孩捎些吃食,进村遇到乡人,总会礼节性的让一让“拿住吃吧”,对方则摆手作拒绝状,口里回道:“不吃不吃,家里买的有”。

又如,穿戴整齐去外村赴宴,路上遇见一熟人,问起去哪里,赴宴人如实相告后,少不了要让上一句:“走,一块喝酒去吧”。知礼的人会答道:“你赶紧去吧,我家里还有事”。
说家里买的有或者家里还有事,多半是托词和谎称,话是假话,却是善意的谎言,不是虚情假意,而是其乐融融。这一让,让出了邻里之间的亲密和睦,让出了你来我往的人情世故。
当然了,说到底让人礼只是一种礼节,一种盛情,不能要求苛刻,更不能随意贴上虚假的标签。乡谚说得很直白,“让人是一礼,锅里没下你的米”,一语道出了真谛。
不过,也有一些不知礼的人,人家一让,他就顺杆子爬,真的应允下来,到头来弄得双方脸上都不好看。对于这种不耐让之人,乡间有一句俗语很贴切,那就是“虚招呼碰见热沾皮”。
这里讲一个真事,是我亲身经历的。
多年前,我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学校对面有一户人家,是个单身汉,老人很和善,每次我骑车上班从他家门前过,总是大老远就打招呼:“走恁远了,拐家喝口茶吧”。
老人说的茶指的是热水,这一让是对我这个外来老师的极高礼遇,让我心生感动。
不过,我心里清楚,老人做饭都是烧柴火,连个茶瓶都没有,平时家里是不会有热水的,我深谙老人的让人之礼,故而一次也没有去家里讨扰,老人对我的热情相让也一直延续着。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一位支教老师来我们学校后,那个小伙子是在城里长大的,不懂包括让人礼在内的乡间诸多礼节。
一日,我在上班路上碰到支教的男老师,他骑车在附近一个村庄赶集买菜,于是我们同行去学校。快到学校门口,那位单身老人冲我们摆手:“拐家喝口茶吧”,我回话后继续往前走,同行的支教老师开腔了:“正好,我的煤火灭了,也没烧茶,我带的有杯子,去家里灌一瓶”,说着顺势把自行车骑到了老人门口。
老人紧走几步到了跟前,面带愧色,话也说不囫囵了:“今儿个起来哩晚,也没烧茶,随后再来中不中?”我和那位支教老师回校了,一路上他嘴里咕哝着,说老头儿太虚伪,明明家里没有烧茶,还再三让?
第二天早上,我又像往常一样,骑车路过老人家门口,一向热情有加的老人像换了一个人,木呆呆坐在门口,啥话也没有说。
不仅是这一次,后来我在那所学校又教了三年书,老人那句“拐家喝口茶吧”的温暖让人语,再也没有听到过一回。
02
让人礼
是区分乡下人和街面人的一道标尺
旧时河南乡间,有乡下人和街面人之分。所谓街面人,就是常年居住在镇上的农人,而乡下人,就是生活在偏远乡村的庄稼人。
昔日乡间,庄稼人土里刨食,以种地为生,单纯靠做小生意养家糊口的,几乎没有。偶尔会有老头老太太赶集赶会,粜个粮食,卖俩鸡蛋,换些日常开销的零用钱。
也有一些乡村匠人,趁农闲编几个罗头,扎几把扫帚,织几领箔,拉到集上会上,卖成现钱。
庄稼人干农活不怯力,也不惜力,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但是做买卖是外行,拉车自己种的白菜萝卜去集上买,直竖竖戳在哪儿,脸上不会笑,嘴里不会喊,还生怕遇到熟人,抹不开脸,嫌丑气。

街面人也种有地,不过不像乡下人以种地为生,往往还兼职做些买卖,故而见识多,眼界广,头脑也灵活,见啥人说啥话。
街面人和乡下人的差别多了去了,仅以让人礼中常见的让钱为例,就完全是两种腔调,两种风格,两种心态。
旧时,无论是街面人在集市上兜售日常用品,还是乡下人赶集赶会卖杈把扫帚牛笼嘴,买主付钱时,卖家总要推让一番,才欣然收下,此为让钱礼。
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上庄下邻,抬头不见低头见。人家给你付钱,你一句话没有,直接装进兜里,显得有些薄气。
你若是留心观察,那些善做买卖的街面人,和偶尔出来出售自家瓜果蔬菜的乡下人,同样是让钱,但细节是不一样的。
街面人见惯了南来的、北往的人,练就了嘴上的功夫,是名副其实的嘴子客,也是生意精儿,让起人来是一套接一套,嘴上说的可亲,像没出五服,眼里头却只盯着手中的钱。
看到买主欲从兜里掏钱,街面人往往是满脸堆笑,嘴上一个劲推让:“拿住吧,拿住吧,拿住吧”,说话时手已经习惯性地伸了过来。
买主一边忙不迭应声:“可不是,那会中”,一边把要付的钱递过去。卖方迅速接住钱,钱一到手,脸上的笑容立马弹簧般缩了回去,扭头又招呼别的顾客去了。

庄稼人就不同了,他们出门少,脸皮薄,老实巴交,不善算计,不会玩嘴。
那些握惯了锄把子的庄稼人,十里八猛出去卖趟东西,纯粹是赶鸭子上架,瞅见熟人脸发热,一掂秤杆手发抖。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买主,相中了货物,问咋卖哩,乡下人憋了一崩子才嗫嚅道,你看着撇吧。
待过完秤,买主付钱时,乡下人搓着手怯生生地说,装住吧。
一番推让后,终于接下了钱,僵硬地握在手中,也不急着拾掇起来,直到买主走远了才装进兜里。
03
让烟看似琐碎小事
却差点坏了一桩姻缘
乡谚说:雨不大淋湿衣裳,话不多恼人心上。
乡人看重让人礼,更在乎让人礼,该让的你没有让,他就认为是你看不起他,故意扮他难看,有的人能记恨大半辈子。
这里重点说说让烟的事儿。
关于让烟的礼仪,我听祖父说过很多,不少都忘了,记住的只是皮毛,譬如让纸烟,遇到人多时候,让烟前须摸摸自己兜里的烟,看够不够一人一根。
如果在座的都吸烟,一让又都接着了,让到最后盒里没烟了,剩下没让到的人恼死你,说你看不起他,既然烟少为啥不先从我这儿让?
还有,现场有四个人,你不能只给三个人让烟,毕竟“长短是根棍,好赖是个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关系近不近,就是这个人不吸烟,你也得上前让一让,这叫“芝麻杆喂驴---吃不吃让到”。
祖父在世时,熟稔乡间各种礼仪,尤其是作为老烟民,对让烟的规矩更是身体力行。听祖父说,有一年五爷的一个亲家就因为少给五爷让一根烟,差点把儿女婚事泡了汤。
一天,五爷正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和人下棋酣战,从大路上过来了一位干部摸样的中年人。行至村口,来人掏出一盒“大前门”烟,在人群里挨个让,五爷下棋的地方离人群稍微远了点,那位中年人懒了一下,没有上前给五爷和下棋的另外一个人让烟。

烟点着吸上,中年人开了口:“我是山北张庄的,早些时媒人给俺那老二孩儿寻个媒,俩孩子都怪愿意。闺女她爹叫广昌,今儿个我来就是到家里坐坐,说说孩子们的事儿。”他还没把话说完,就有眼尖的人搭了腔:“广昌伯才走,估摸着这会儿还没到家哩。”
这时又有人说:“你来的时候,他正在那边下棋哩。对了,你是不是没给他让烟?”中年人连忙点头称是,人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
等大伙把五爷的秉性给中年人一说,他也慌了神。
根成叔是个热心肠,赶忙站出来劝说中年人:“我看这样吧,一会儿你推着车子,咱俩去给五伯认个错,兴许他能原谅,再生气总不能亲家来了都不让进门吧。”
中年人跟着根成叔来到了五爷家,五爷开门一看,眼前站的是刚才没给自己让烟的那货,气不打一处来,把门关的铁桶一般,任凭根成叔好话说尽,五爷就是不开。最后还是五奶奶看不下去,开开门让客人进了屋。
吃晌午饭时,根成叔陪着客人猜枚,就着五奶奶炒的小葱鸡蛋儿,一盅盅喝着宝丰大曲酒,五爷始终没放脸,酒没喝,菜也没叨,只顾一根接一根吸烟。
当然了,吸的都是自己卷的“一头拧”,客人拿来的整条“大前门”烟,他看都没看一眼。
五爷后来对人说,当着恁多人的面不给我让烟,等于是扇我的脸。直到后来,两家正式结成亲戚后,五爷仍是解不开这个疙瘩,好长时间和亲家的关系都很僵。

因让烟引起的误会,在乡间还有不少,多年前,在近族的三伯身上,也发生过。
有一年秋罢,三伯把一车黄豆秆装好刹紧,蹲在地头,叼个旱烟袋过烟瘾。恰在这时,邻村的亲家路过黄豆地,三伯赶紧起身打招呼,把亲家往家里让。平日里亲家是个挺温和的人,这天却一反常态,脸一直阴沉着,三句话没说就起身走人。回到家里,三伯心里不踏实,把儿媳妇叫到跟前说,后半晌在西地碰见你爹了,我再三让,他就是不来,我心里老过意不去。
儿媳妇是个直性子,听了公爹这番话,扑哧一声笑了,连忙劝说道,兴许是俺爹有啥事急着走,您老哥俩还外气啥哩。
三伯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也没往心里搁,半月后儿媳妇回了趟娘家,回来后直接找到牛屋,一脸严肃地对三伯说,爹,我给您说个事儿。说吧,三伯心中一惊,脸上却装作没事人一样。
儿媳妇说,那一天俺爹在黄豆地碰见您,您是不是正在地头吸烟哩?是,三伯点了点头。俺爹说了,您又不是不知道他烟瘾大,咋一瞅见他过来,赶紧把烟锅里的烟捂灭了,连让也不让他一下?
三伯一听儿媳妇说这话,先是憋住气没吭声,许久才重重叹了口气说,孩子啊,你到咱家也十几年了,我是啥人你心里最清楚,我会不知道你爹比我的烟瘾还大?我会想不起来让你爹吸两口?我是怕在你爹面前丢人啊。
一脸憋屈的三伯说着,不时用袖子沾眼角。
最后,在儿媳妇的追问下,三伯才道出了实情:那天装完车子,他的烟瘾犯了,可是没钱买,烟叶已经断了十几天了。无奈之下,三伯从黄豆秆上拽了一把干黄豆叶,放手心里揉碎,装进烟锅里应应急。
刚点着,还没吸两口,就呛得两眼噙泪,一抬头瞅见亲家走过来,三伯心里那叫一个乱,让让亲家吧,怕知道自己穷的吸黄豆叶,往后这脸往哪儿搁哩。不让吧,亲家还认为自己是个老鳖一,连口旱烟也不舍得。
正想着,亲家站到了跟前,三伯最终还是嫌丢人,没让烟。
(图片来源于网络)
//////////
梁永刚
男,1977年生,河南平顶山人
出版有散文随笔集《爱到深处情自浓》
现供职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