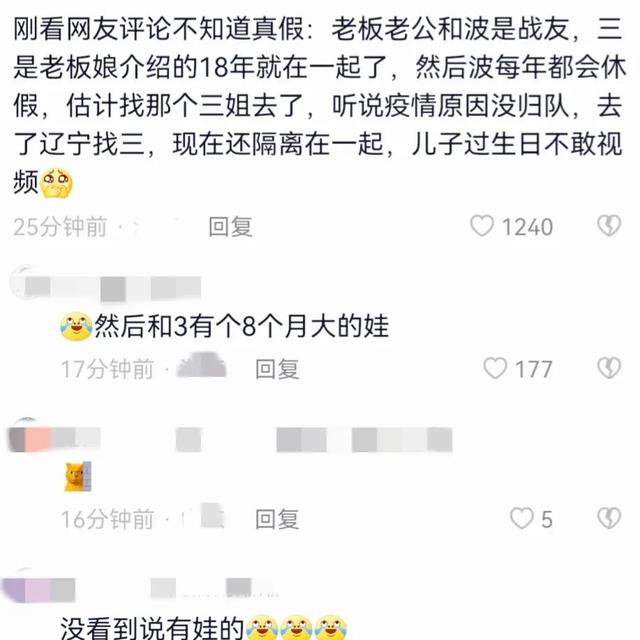《穿条纹睡衣的男孩》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故事片,讲述的是二战期间德国军官的儿子布鲁诺和犹太小孩什穆产生的一段"隔墙友谊"前后所发生的事情。十分讽刺又令人唏嘘的是,无情的命运和布鲁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的生命也在其父亲看管的集中营中就此划下了句号。
外媒多家报纸和影评为其冠以"美丽的悲剧"一词,根本原因是这部电影借由孩子的视角展现出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惨无人道和令人发指的种种行径——杀人,但不见血;诛心,但不暴力。

整部电影的场景调度颇具玩味,所有孩子视角下的镜头都集中在外景且用光大多是璀璨的自然光。但越天真,就越无情。电影的基调越"不置一词",那巨大反转的结尾就越令人感到彻骨的寒冷。
可以说,这是一部细思极恐的电影,也是一部看完不会哭得很凶但会非常堵心而且堵很久的电影。说它"细思极恐"是因为,直到现在我也不想知道什穆到底清不清楚把布鲁诺放进去后会发生什么?因为很明显的是。哪怕没预料到顷刻的死亡,至少他一定晓得布鲁诺会受到和他自己一样不公平且非人道的待遇;我也从来不敢在布鲁诺脱衣服的时候去定格那位老人的表情,所以也就不得而知他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这个没被剃头、外表干净的小男孩其实原本并不属于这里。
可谁生来就该属于这里呢?又有哪个犹太人注定要进集中营呢?没有——苍穹之下的黑烟背后,没有人真正幸免于难,哪怕在战争中占尽便宜的施暴者也不能。
另一方面,这部电影对人物关系和细节的处理也很有分寸。无论是电影中尚存人性但无能为力的两位女性的最后结局,还是从未露面的某个看似不相关的剧中人物——每一个角色都再将这个"小小的故事"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也将那颗原本很小的雪球滚成了一场无力回天的雪崩。

这部电影从多个角度完整地呈现出极权主义下的三种结局——只要身在其中,必将择一而行。接下来就从这三种结局入手,深入分析《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这部电影给世人带去的低声忠告和残酷现实,以及微弱却坚定的美好愿景。
这句出自《左传·宣公二年》的古语字面意思是一个人犯了错误后能够认识并加以改正,这是再好不过的了。但深究下去,要想实现"善莫大焉"其实是需要两个前提的:1,知错;2,能改。
也就是说,首先你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或认知是错误的,然后才有了改正的前提。有了这个先首条件之后,有改正的资本和能力并付诸行动,这才能实现后面那句"善莫大焉"。
但从电影反应的现实来看,对于当时二战中的纳粹及其家人来说来说,能满足第一个条件的人就屈指可数。人群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掌握一定生杀大权的军官到他手里的下属、从军官的父亲到他的子女、从施暴者到受害者,从根本上知道这件事"错"的人,寥寥无几。
少到什么程度呢?整部电影中站在纳粹对立面的只有三个半人:一位业已逃往瑞士的纳粹的父亲、一位死后仍"被迫"在其棺材上放置希特勒宣传册的纳粹的母亲、一位了解真相后日渐消瘦精神状况堪忧的纳粹的妻子以及那位终被犹太受难者"吞没"且生命永远定格在八岁的小男孩——《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也是那"半个知错者"。
为什么说他是半个?因为他本已通过母亲的变化和朋友什穆的遭遇察觉到端倪,但一部纳粹出品的"乌托邦宣传片"就打消了他大部分对父亲的质疑和对整件事的困惑,所以他才会不假思索地换上那件不知道被多少人穿过的条纹睡衣,义无反顾地爬进那座人间炼狱并最终成为这场惨无人道"战争"的牺牲品之一。

而其他人就没有了“知错”的幸运。像那位长相帅气的下属,在提到自己的"叛徒"父亲时会目光闪躲、无所遁形,甚至将自己打翻酒杯这件事反手就扣在一位老人的头上并将其活活打死。而布鲁诺的姐姐则更是在读过几部本国人编纂的"历史书"后,就笃定是犹太人害得德国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阻碍他们成为世界霸主,并对"犹太有毒"论深信不疑。甚至布鲁诺的爷爷会在自己妻子死后,不知是为了表忠心还是为了做最后无声的对峙,居然将一本希特勒宣传册放在自己那对纳粹深恶痛绝的妻子的棺材上,让人心生悲凉却又无能为力。
这就是极权主义下大多数拥护者的结局——执行。他们别无选择,也不想另谋出路,因为不曾产生怀疑。漫天盖地的理论洗脑以及主观相信的事实冰山一角,构成了他们全部的认知体系甚至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一旦一件事被深信不疑,就挣脱了是非对错的判定——只有成功和失败,再无其他结论可言。
所谓现实是什么?事实又是什么?很大程度上,它只是大多数人产生的一种共识,而这些共识连接到一起就形成了有限空间内的天和地甚至一呼一吸之间的空气,让接触到它的人忽略掉对它的探寻,只剩执行。

这也是《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从某种角度像观众展示出来的残忍,虽不见血,却刀刀戳心。当历史的车轮碾过那段往事并将其定性为"泯灭人性"的时候,全世界的目光才整齐划一地投向那里,那些曾参与到其中的人才意识到自己是时候低下头看看脚上的鞋子沾染了多少无辜者的鲜血。
私以为,这句古语用来诠释这部电影的时候,应该改为:知错、能改,方善莫大焉。
首先我要澄清,在鄙人的认知结构里这并非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话或带有性别歧视的结论。虽然大多权威会将这句出自《论语·》的话解释成: 女人和孩子都很难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难养身、心、性、命),所以与之相处要有分寸——太近了容易失礼并坏了规矩;太远又容易招致怨恨而不利于儒学的传承。
后面的解释以现代学者的臆测为主要成分,但"女人和孩子很难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这句话我却十分赞同。因为这两个群体都内心柔软、缺乏理性,或者说他们更以自己的感性体验为认知导向。

就像《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那位母亲,她会在知道家中的犹太"犯人"帮忙给孩子包扎伤口后,几经思考还是说出了那句"谢谢";她也会在知道那大烟囱里冒出的滚滚黑烟是焚烧尸体所产生这件事后几近失心疯。她生在德国、长在德国,也曾十分满意自己丈夫的高官厚禄,但当她知道这一切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或者说他的丈夫是在做了什么事得到这一切后,这个女人对自己的枕边人乃至自己的国家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样的人无异于麻烦。所以她的丈夫眼看着形容枯槁、行为怪异的妻子却不置一词甚至横加指责,就像他知道自己那反纳粹的母亲骤然历史后,第一反应居然是长舒一口气——仅仅因为她们是自己升官发财的绊脚石,更是日耳曼民族实现"伟大历史目标"的障碍。
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这样的人只能“躲避”:要么死去,躲避这个世界;要么逃离,躲避这种统治。所以那位宅心仁厚的老奶奶去世了,对这个世界充满幻想的布鲁诺去世了,布鲁诺母亲的最后一丝生气也在预测到儿子死讯后的嘶吼中消散在那充斥着罪恶的空气里。
"女子与小人"的确"难养",可正因为只有他们会在任何时候都听从自己的内心和直觉,并用自己柔软的心和不曾泯灭的良知给这个世界留下最后一丝希望,所以这苍穹之下的罪恶才不会大面积蔓延并世代延续不是吗?
对于极权主义来说,他们是无用甚至是多余的。但对于人性和文明来说,他们永远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十分重要且无可代替。

在人物内心变化和人物结局的处理上,《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处理方式堪称巧妙。它将无尽的悲凉、无力甚至绝望投过满屏幕的明亮和高光传递给观众并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给那些看似很轻实则很重的"女子和小人"都配上了变幻莫测的光线和扣人心弦的背景配乐,让人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更无法回避他们带来的视觉以及听觉上的冲击。
关于这句话的争议可以说从古至今都没有停止,但笔者更相信胡适老先生的解释倾向。因为结合《道德经》全本以及庄子本人的思想,这种解释似乎更合情合理:
天地本就无爱无憎、无欲无求,给予万物繁华并不是因为天地喜爱于它们,使万物萧条也并不是因为憎恨于它们。生命便如刍狗一样,当祭祀完毕之时,刍狗的使命也随之结束了。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在社会体系中充当不同的角色。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就像万物的枯荣、天地的运转,谁也没有办法将其破坏,最终还是要选择不加以干预的"无为"的态度。

那么放置在《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这部电影里,又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当布鲁诺最终化成自己曾经最讨厌其味道的黑烟一缕,看到这一幕的观众大多会潸然泪下。可在为这种结局悲恸之后不妨思考一下,这不正是"天地不仁"之处吗?布鲁诺用死亡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结局,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这属于"错误的巧合",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报应",但"天地"之间从来就没有占尽优势的一方,也没有长久的失败或胜利。
就像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一样,受难之人给世界留下的意义和犯罪之人给后人的警醒何尝不是处于同一水平?
所以对于历史和"天地"而言,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无情"的存在。历史负责记录、天地只做见证,苍穹之下的悲喜,说到底只是人类自己的事情。
这也是那些牺牲在极权主义之下的人最好的结局——归于虚无。可他们仍给这个世界留下温暖的痕迹。对于看电影的人们来说,用孩子的视角去呈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不正是一个带有"美丽悲剧"色彩的角度吗?当历史已然定型的同时,那份对过去的悲伤转化成对现世的悲悯正是这部电影最好的意义。

天地之下,人人都是"刍狗"。话虽如此,但这种定义仅限于对天地而言。毕竟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唯爱可万世长存。
在电影的第29秒出现了这样一句话:
Childhood is measured out by sounds and smells and sights, before the dark hour of reason grows.
从字面翻译过来大体如是:
在黑暗的理性到来之前,用以丈量童年的是听觉、嗅觉以及视觉。
换句话说,黑暗的理性存在于每个人体内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萌芽。

从这个角度出发,这样的结局于布鲁诺而言未偿不是一种美丽。毕竟他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秒,仍不知情,也仍然相信自己的父亲。他终究没有长出黑暗的理性,也用最纯真的眼睛走过“美好”的一生。这大概也是《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用光大多数时候都偏向明亮的原因吧。

无知者无畏。能成为一个无知者,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