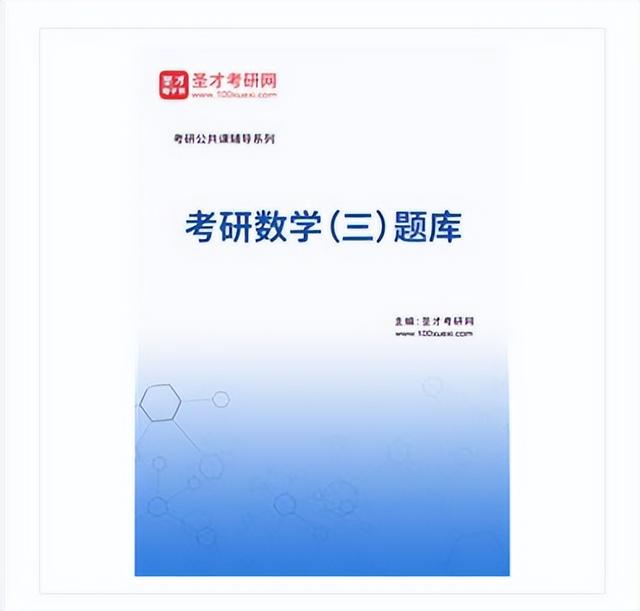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汴京。
北宋真宗皇帝开科取士,龙虎榜上很不起眼的角落,有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朱说,苏州吴县人,二十七岁,列乙榜第九十七名。
这个名次不算好,但总算是进士及第了。
这一年,宋辽檀渊之战中“左右天子,不动如山”的寇准刚刚被罢相,北宋政坛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和,但又暗流涌动的时期。不过这些和新晋进士暂时没什么关系。
不久,朱说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大概相当于省直管县的法院院长,官品也不算高,只是九品而已。
朱说的家庭条件并不好,拿到俸禄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接到身边供养。
司理参军掌管案件、刑狱,秉性刚直的朱说,工作很用心。常常因为案件的是非曲直、量刑轻重与太守争执,拍桌子瞪眼也是常事。
回家以后他便将太守和自己的言论记在屏风上,时时对照思考反省,力求没有冤假错案。
这期间,一次郊游,他写了一首《瀑布》诗,算是明志:
迥与众流异,发源高更孤。
下山犹直在,到海得清无。
势斗蛟龙恶,声吹雨雹粗。
晚来云一色,诗句自成图。
其孤高正直之气和浩然如海的胸怀,已经初现端倪。
等到生活和工作都慢慢走上了正轨,朱说与母亲商量一件大事——复姓改名。
原来,朱说两岁时生父去世,母亲无力抚养孩子,只好携子改嫁,并从继父姓朱。
待到朱说长大成人,得知真相后,一直都有复姓的想法,只是怕两边宗族有意见(涉及恩荫、族产等事),惹得母亲伤心,便耽搁了下来。
成家立业后,他与母亲商量好,又说服了两边宗族,终于向朝廷上表申请改姓归宗。
天禧元年(1017年),朱说经朝廷准奏,正式更名为范仲淹,字希文。
从那一年直到今天,这个名字足足光耀了一千年!
博通书易传大道
天圣五年(1027年),南京(宋南京在今河南商丘)。
此时真宗皇帝已经驾崩,十二岁登基的仁宗皇帝已经御宇五年了,朝政大权仍掌握在刘太后手中。
朝堂的雷霆雨露都没有照进范仲淹的现实,他刚刚从兴化知县任上辞官,为刚刚过世的母亲守丧。
十余年间,仕途不见多得意,但范仲淹一直秉持直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同时广交同好,磨炼学问,《易》、《春秋》、《中庸》等诸经大成,其继兴儒学的志向得到了广泛认同,声名日盛。
适逢“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太平宰相晏殊任南京留守,他对范仲淹的才学极为赏识,邀请赋闲的他主持府学教育。
这是范仲淹少年求学的地方,教书育人也是他的夙愿,遂欣然领命。
范仲淹一贯重视教育,而且不只是重视科举考试,更重视儒学传承和读书育人,认为只关心考试成绩的教育是“不务耕而求获”,这话放到今天的教育界也一点毛病没有……
主持府学期间,范仲淹严厉整顿教学秩序,使诸生肃然,学风为之一清。除了整顿纪律,他在府学主要干两件事:
一个是写“范文”,既是范先生之文,更是模范之文。
他每出一个题目,都自己先做一遍,把握题目难度的同时,也供学生参考。无论是赋、诗还是策论,都不在话下。
这下大家知道《岳阳楼记》的文笔是怎么磨炼来的了吧。放到现在,估计也没几个老师能做到……
另一个就是接济贫困学生。
范仲淹家境并不好,尤其是继父解甲归田之后,他甚至还在商铺当过一个月的小伙计,可他既奉承不了老板,又欺骗不了顾客,继父实在不忍心荒废他的向学之心,终于让他继续求学。
为了节省费用,范仲淹借宿寺庙(便于就近请教),每天只有一碗稀粥,冻成凝胶状,洒点咸菜,划成两半,早一块,晚一块,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
因此,看到那些饥寒交迫的士子仍一心向学,他完全感同身受,也竭尽所能去接济他们,一日,学院里来了一位年轻人,衣衫褴褛,面带菜色,求教学问,范仲淹指点学问的同时,自掏腰包,送给他一万钱(大概相当于5000块)。
一年以后,范仲淹又看到了这个年轻人,就问他怎么回事,年轻人羞愧难当:“实在是家有老母要奉养,但又不想放弃求学,只好厚颜至此”,范仲淹听了很难过,于是帮他在书院谋了一份工作。
年轻人从此师从范仲淹攻读《春秋》,直到范仲淹服丧期满复职离开南京,他才回到山东老家。
十年后,山东有一大儒开讲《春秋》,风靡京东,号称泰山先生。原来,他就是当年的那个年轻人,孙緮。
后世将其与石介,胡瑗,并称为“宋初三先生”,是开两宋理学的先驱。
其实,范仲淹传道授业、扶贫济困的例子很多,受他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就更多了。
后来在陕西戍边,他传授给一个纸上谈兵的愤青《中庸》,导其向学,终成一代宗师,开创关学,世称横渠先生张载,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流传千古。
后来,范仲淹又传授给一个年轻军官《左传》,使其文武兼资,后官至枢密副使(军委副主席?),在两宋,足以与岳飞并称,这就是“面涅将军”狄青。
从这个角度,范仲淹堪为天下师、万世师。
这期间范公诗文以各类赋论为主,颇为严整,望之不欲亲近。唯有与“梅妻鹤子”、“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林逋交好,遥寄七绝,清新俊逸,颇有昌龄遗风:
片心高与月徘徊,
岂为千钟下钓台。
犹笑白云多事在,
等闲为雨出山来。
赋罢灵乌奏履霜
天圣七年(1029年),汴京。
在外磨砺了十几年的范仲淹,刚刚因为《上执政书》得到宰相王曾的赏识,才除母丧即被召入京任秘阁校理。
这是一个品级不高,但是很重要的职位,算是皇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我们知道,干过图书馆管理员的都很厉害,比如老子,比如主席……
当时宰相和执政都很看重范仲淹,本以为他会厚积薄发,一展胸中抱负。结果才上任没几个月,就惹祸了。
这年冬至,百官大朝,当朝的刘太后想要仁宗皇帝和百官一起向她恭贺新年(宋代冬至是新年)。
这是什么意思呢?普遍认为,这是刘太后向武则天靠拢的一次试探。
刘太后也不是一般人,史称“有吕武(汉朝吕后和唐朝武则天)之才,无吕武之恶”。
她本来是四川一位银匠的妻子,生活所迫与丈夫一起进了王府打工,为避讳,她与丈夫改为兄妹相称,结果她被当时的襄王看中,可能也没办正经离婚手续,就这么稀里糊涂成了王爷的女人。
谁知后来襄王成了天子,她也顺势入宫,在武媚娘的光辉精神指引下,甄嬛附体,一步步成了皇后。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早着呢。
刘皇后一直无子,后来有一位宫女意外怀孕,生下一子,刘皇后把孩子抢过来自己养,这就是后来的仁宗皇帝了。
后世“狸猫换太子”的传说就来源于此。
由于仁宗皇帝即位时还小,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刘太后掌握了朝政大权,关键是国家治理得还不错,慢慢的可能就有了一些别的心思。
当时的情况是,朝中大臣基本都知道仁宗不是刘太后的亲儿子,但仁宗皇帝不知道,而且对刘太后很孝顺,于是大家谁都不想对抗刘太后,免得两边都不讨好。
这个时候天生铁骨的范仲淹站了出来,坚决维护天子权威:
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
在范仲淹的起头下,群臣也消极对抗,冬至朝贺的事总算不了了之。
结果范仲淹还不罢休,干脆又上了一道奏章,说皇帝已经二十岁了,太后应该还政于皇帝,看到太后没反应,他又连上奏章呼吁。
刘太后终于忍无可忍,将范仲淹贬为河中府通判。
可能有人说范仲淹当时是在搞政治投机,待皇帝亲政自然有回报。但看看接下来十年间他的行为和经历就知道了,他是天生冰心铁骨。
刘太后去世,范仲淹起复为右司谏,成了名副其实的谏官,结果不到一年,又因为谏阻仁宗皇帝废后,被贬睦州,后知苏州。
一年后回京,先是任判国子监,后晋升为权知开封府(相当于今年的北京市代理市长)。
有说法是说这次提升是时任宰相吕夷简的花招。
吕夷简是一个很有能力,但权力欲望也很强的一个人,干过不少拉帮结派、暗箱操作的事,实在不放心把范仲淹这样一个大杀器放在身边,于是给他找了一个特别繁杂的职位,本以为会消停一点,结果范仲淹毫不在意,把开封府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同时,一样没放过吕夷简,他按现在的调查统计方法,上了一幅《百官图》,将朝中官员与吕夷简的关系、交集及其升迁贬谪路径一一列示,说明吕夷简党同伐异、公器私用。
结果,他没想到(更可能是想到了也不在乎),这些官员,尤其是高品官员的任命都是皇帝决定的,虽然他说的是事实,但是这不是当面嘲讽皇帝的智商么,妥妥的打脸啊。
吕夷简利用皇帝恼羞成怒的心理,大进谗言,朝中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干正直大臣实在忍不住了,上书声援范仲淹。
结果正好被吕夷简抓住把柄,说范仲淹“结党”,这可是朝廷政争的撒手锏,历来大臣结党都是皇帝的逆鳞——东汉有党锢之祸,唐朝亡于牛李党争,当然,还有后来北宋的新旧党争,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之争。
关键时刻,欧阳修上了一篇《朋党论》,公开宣称:君子有朋,小人无朋。也就是承认了我们就是有朋党……
皇帝才不管你是君子朋还是小人党,但凡结党肯定会威胁君权啊。文章写得越有气势,皇帝越反感,所谓南辕北辙。
这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X一样的队友……为尊者讳,就不批评醉翁了,毕竟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老头,不过有的时候确实有点大嘴巴。
这下动静大了,范仲淹和他的朋友基本全部被贬斥出京,史称景祐党争。范仲淹还被抄家,贬到饶州,贬官途中妻子也不幸亡故。
他后悔了吗?完全没有!
在饶州,一位朋友写信安慰他,顺便也劝他明哲保身,不要学乌鸦,警告凶讯反“招唾骂于里闾”。
范仲淹回复了一篇《灵乌赋》:
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冰心初照关山月,铁骨堪磨柳叶钩
康定元年(1040年),延州。
刚刚举起叛旗成立西夏的李元昊,围困延州,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三川口大败宋军,大肆劫掠后扬长而去,朝野震惊。
仍在相位的吕夷简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
居然是范仲淹,应该说来自敌人的肯定是最大的赞美。
十年间的贬谪流放中,范仲淹从来没有怨天尤人、得过且过,无论在哪一个职位上,都尽心尽力抚民理政,成绩斐然。
关键时刻,仁宗皇帝对范仲淹坚韧的品格和卓越的才能也充分肯定,遂将其官复原职,随后擢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知州,这一年范仲淹已经52岁了。
到任之后心情复杂: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一阙《渔家傲·秋思》一向被认为是豪放派词作的源头,一洗五代以来花间习气,应该说对后来的苏东坡、辛弃疾都有一定的影响。
多说一句,范仲淹流传的诗近300首,但词很少,只有5阙,是他不通音律吗?
应该不是,按陆游的说法,范仲淹擅抚琴,一辈子尤好《履霜操》,以言高洁之气和自醒之心。
我觉得,他填词少主要是因为宋初文坛普遍认为“诗庄词媚”,这也限制了词作风格,与范仲淹同时代的填词高手晏殊、柳永、欧阳修、张先等均以秾艳纤巧或秀丽清新为主,私以为,不符合范公的人设,因而范词较少。
到任西北后,范仲淹经过深入调查,认清了西夏与宋朝的战略态势,与当时朝野普遍认为西夏只是“疥癣之患”的盲目乐观情绪不同,范仲淹清醒地认识到了西夏对宋朝西北乃至整个北方防御体系的威胁。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调整了战略,放弃速胜的想法,通过构筑堡、寨巩固防线,压缩西夏战略空间,同时大力练兵,改变军事管理体制,培养了一大批知兵的将领。
但是公平的讲,宋朝文臣统兵的传统,以及烂透了的所谓“八十万禁军”,真的不具备消灭西夏的实力,况且还有一个辽国在旁边虎视眈眈。
后来整顿好了防务之后,西夏见占不到便宜,于是就想议和。
这个节骨眼上,另一位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不听范仲淹的劝阻,领兵伐夏,在好水川中伏大败,韩琦本人也被战死士兵家属拦着马头洒纸钱羞辱。刚有好转的对夏局面全面崩坏。
等到李元昊占够便宜,终于肯谈判了,结果挟大胜之威,国书里极尽狂妄羞辱之能事,范仲淹一气之下烧掉了国书,遂以“破坏和谈”的罪名被贬为耀州知州(听着有一种莫名熟悉的感觉)。
惆怅的范仲淹填了一阙《苏幕遮》,伤怀不已:
碧云天,黄叶地,
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
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宦海浮沉君莫喜,江湖进退我先忧
庆历三年(1043年),汴京。
天章阁中,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考试。
此时西夏议和已达成,范仲淹刚刚被召回京,群臣推举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他反复向皇帝说明,西夏狼子野心,议和必不长久,还是请求回西北戍边,仁宗不许,仍宣麻拜相,擢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并在天章阁问对治国之道,由范仲淹书面作答。
范仲淹的答案中心思想就是社会在前进,事务在发展,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即《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并提出十条具体举措: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衣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仁宗皇帝认可了范仲淹的答案,并明发朝官讨论,欧阳修等人纷纷上书支持,遂定为法令,正式施行,史称“庆历新政”。
其实范仲淹不是不知道,改革的时机其实并不好,问题虽然已经显现,但体制内的绝大部分人并未察觉,调和阴阳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他心底也并不想当这个参知政事来主持改革,但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仍促使他站了出来。
此次新政,抑侥幸断了一大批高官子弟恩荫入仕的路子,精贡举又改变了诗赋取士的科举导向,修武备更是公开质疑京城禁军的战斗力,总之,文武官员和读书人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在有心人的煽动下,渐渐形成了抵制新政的狂流。
仅仅一年以后,朝廷分裂之势已经很明显了,互相攻讦不断,手段开始突破政争底线,甚至有人造谣范仲淹阴谋废立皇帝。
虽然仁宗皇帝并不见得相信这么幼稚的谣言,但仍不胜其烦,同时面对改革的困难,他退缩了。
终于,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又以“朋党”为由,贬斥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人,尽废新政。
范仲淹又回到了西北,出知邠州、兼领陕西四路缘边招讨使,这时他已是5 7岁了,身体已大不如前,很快病倒了,朝廷迁其到邓州养病。
就是在邓州,范仲淹接到了好友滕宗谅(字子京)的来信。
滕子京由于与范仲淹的关系,被诬贪污公使钱(公用经费),贬谪巴陵。所谓人以群分,滕子京贬谪之后虽然痛苦,但仍积极治理地方,还重修了岳阳楼。
他写信介绍了自己的近况,并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请范仲淹为岳阳楼写一篇记。
在从没有到过岳阳楼的情况下,范仲淹将自己辗转半生的经历、治国理政的理想、家国天下的情怀,融为一体,遂成千古雄文《岳阳楼记》:(开篇一幅画,内容全靠编)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挑灯夜读临终表,伯仲之间见武侯
皇祐四年(1052年),徐州。
庆历新政失败已经八年了,八年间,范仲淹虽然声望日隆,但当政诸公也更不放心他回到朝堂,于是不停迁任。
范仲淹八年间辗转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每到一地,必尽心抚民理政,政绩卓越,但同时,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越是深入地方,他对盛世之下掩盖的危机就越清醒。杭州任上游西湖的时候,他写下了:
湖边多少游湖者,半在断桥烟雨间。
尽逐春风看歌舞,几人着眼到青山。
我相信,林升的“西湖歌舞几时休”灵感一定源于此。
可惜老天并没有给这个清醒的老头更多的时间。
他的最后一任官职是颍州知州,结果没能坚持到任,半路上在徐州病倒,并最终不治,当年五月二十病逝于徐州,归葬洛阳伊川,谥文正,按司马光的说法,这个谥号“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史称范文正公。
范仲淹临终所上的遗表,全无一字涉及自己和子孙,全部是殷殷劝诲:
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彰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民于未乱,纳民于大中。
让人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武侯诸葛亮的《出师表》,陆游问: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我觉得范仲淹完全当得起。
虽然范仲淹算不上天才,但却是儒家极为罕有的全才和典范:
作为宰相,他主导的庆历新政为后世的王安石变法打下了基础。
作为统帅,他打造的西军直到北宋灭亡仍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作为官吏,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不胜枚举。
作为孝子,他供养范朱两族,培养了一个宰相儿子,开创了范氏传承千年的家风。
作为儒士,他将陷入解经和训诂泥沼的儒学拉了出来,开理学风气之先。
作为诗人,他以文入诗,一扫西昆陋习。
作为词人,他开创了豪放一派。
……
最后,借用范仲淹评价东汉隐士严子陵的话来评价他自己吧: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PS:范仲淹作为儒家典范,他的生平并不算有趣,写他的评述,笔触难免沉重,最开始其实还填了一阙《鹧鸪天》作为章节标题,稍微活泼一点,作为最后的余韵吧:
本是姑苏田舍郎,天生铁骨谏君王。
博通书易传大道,赋罢灵乌奏履霜。
迁塞北,远潇湘。世间忧苦我先尝。
斯人不见心安在,散入春风满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