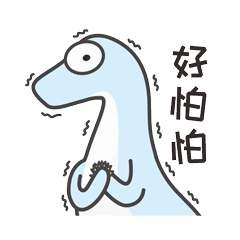□文、图 王晓峰
在我印象中,没有比木里的五月更好的季节了。
五月的木里像一幅尚未涂彩的油画,天是湛蓝湛蓝的,云是雪白雪白的,地上呢,是一片一片的金黄,一切都是那么清纯,那么原始。
五月的木里,不冷不热,气候宜人,阳光格外明媚,此时你走出大门,会觉得天是那样的低,白云就像在你头顶飘荡,好像你一伸手就能扯下一块来。迎面吹来的高原的风已经没有那种刺骨的寒,看脚下,泥土酥软着,草地酥软着,就像处子的肌肤,散发出一种芬芳。不远处的布哈河蜿蜒西去,一边是半米厚的冰凌,一边是清澈见底的春水,半河冰凌半河春,那该是怎样一种美丽啊。在河边站上一会儿,顿觉心旷神怡,感觉肌肤也好像酥软了。
下午的时候,起风了,天阴了下来,不一会儿就飘起了雪花,初下时,是星星点点的,如雾似烟,若有若无,随风飘荡,渐渐地,雪大了起来,一片一片的,就像仙女在向地上扯着棉絮,不一会儿,矿区的草坪上、屋顶上,就连那露天的矿坑,都成白色的了,刚刚还枯黄的山坡顿时像披上了一层白纱,一时间,天是白的,地是白的,一切都笼罩在这茫茫的白色中。
夜幕降临了,雪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吃过晚饭,邀三五好友,端坐窗前,开一瓶青稞酒,烫一壶铁观音,围炉夜话,对斟赏雪,以唐诗为媒,以莫言佐酒,前八百年,后五百年,国事家事天下事,宋词元曲清小说,尽在其中。是谁说红袖添香好读书?在海拔4200多米的青藏高原,没有红袖,有的只是室外飘洒的白雪和兄弟们的雅趣。
五月的天亮得格外早,不知哪个冒失鬼揉着惺忪的睡眼,掀开走廊上的门帘,原以为室外还是昨天的颜色,一不留神却“呼哧”一下摔了个四仰八叉,抬眼四处时,整个人竟跌倒在雪地里,像盖了一床雪白的被子,他揉揉摔疼了的屁股,惊叫了一声“好大的雪!”随着吱扭吱扭的开门声,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室外,踩在及膝的雪地上,伸个懒腰,踢踢腿,突然有一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意兴,想在雪地上撒点野。这时,不知从哪个开着的窗户里传出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的古老歌谣,又不知是谁说了句:“雪下一层被,枕着馍馍睡,这样的好雪,如果在老家,不知该有怎样的好收成呢!”又有人接了过来:“可惜这里不是中原,但这样的好雪,当地的虫草、大黄、雪莲肯定要比往年好,这个绝对跑不了。”
快中午的时候,太阳出来了,但稀稀疏疏的雪却一点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仍在飘飘洒洒着,在高原阳光的照射下,分外晶莹,好似到了另一个世界。
不知什么时候,雪停了,太阳从云层中钻了出来,羞羞的,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小草脱去金黄柔软的冬装,从雪地里偷偷钻了出来,嫩嫩的,绿绿的,眨巴眨巴眼睛,一副很新奇的样子。
这个季节,风是常有的,雪也是常有的,但这个季节的风,这个季节的雪,已经没有了寒冬的料峭,柔柔的,绵绵的,悄悄的,就像母亲的手抚摸着大地。
天晴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熟悉的号子响起来了,那乡音,那韵味,是那样的亲切。
木里的春天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