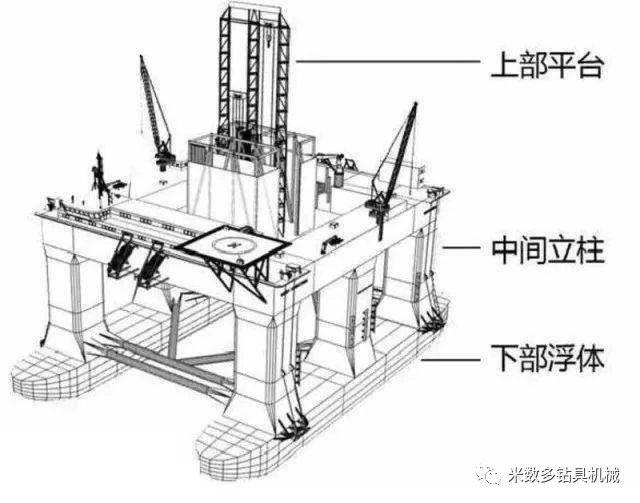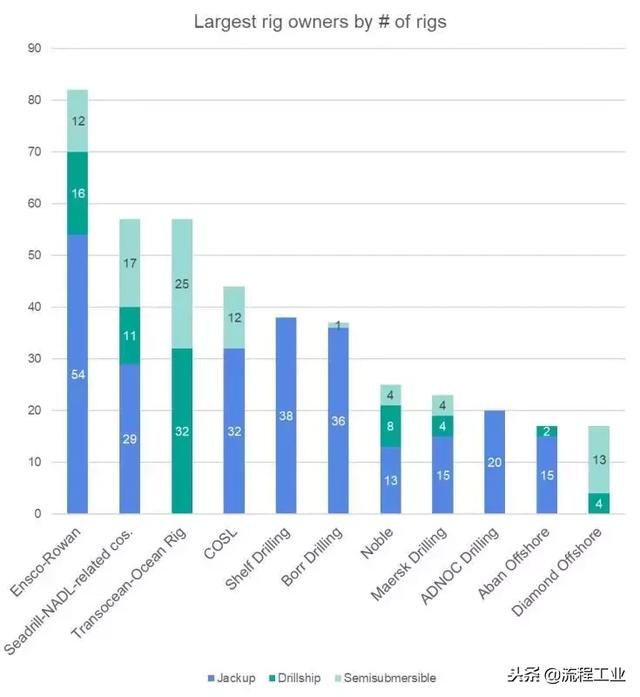一
我径直穿过客厅。维斯特小姐说:“他正在开会。”我没有停步,也没有敲门。他们正在说话,他停下话题,从桌子的另一端看着我。
“我离职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告诉你?”我问。
“离职?”他问。
“我不想干了。”我说,“一天够了吧?”
他望着我,瞪大着眼睛,跟青蛙似的。“难道你觉得我们的飞机让你表演还不够好?”他问道。他手夹着雪茄,放在桌子上。他手上戴着一枚后车灯般大的红宝石戒指。“你跟我们一起只干了三周,”他说,“时间太短,还不足以理解门上那个字的含义。”
他不明白,但三周时间已够长了。比纪录还少两天。如果三周对他来说是纪录的话,他完全可以不动身子便与新冠军握手。
问题是,我什么都不会做。你知道当时的情况,连大学校园里都是身着英国和法国军装的士兵,而我们都担心还没来得及参战,还没来得及驾驶飞机上天,战争就结束了。你知道,参加战斗,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停战后我留在军队里当了几年的试飞员。我就是在那时候爱上了在机翼上行走,为了不让生活太枯燥。一个名叫沃尔德里普的家伙和我一起驾驶耐恩飞机飞到三千英尺的高空,我在飞机外边吃力地行走。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枯燥无味:除了到处闲逛,白天酣睡,晚上通宵打牌外,无所事事。孤独无聊对牌运不利。输了便赊账,越赊陷得越深。
有一个名叫怀特的家伙一晚上就输了一千。
他一输就没完没了,我不想再玩了,但我是赢家,他还想再玩,越陷越深,每局都输。他给我开了一张支票,但我告诉他不用着急,别太认真,因为他在加利福尼亚还有妻子。但第二天晚上他又想玩了。我竭力劝他别再玩了,但他却发火了。骂我是胆小鬼。那晚上他又输了一千五百。
然后我说我来切牌,要不加倍下赌要不就算了,最后再赌一把,就最后一次。他抽到一张Q。我说:“啊,我输定了。我牌都不用抽了。”我把他抽的牌翻到下面,很快洗完牌后,我们看见很多张K、Q、J和三张A牌。但他还是坚持要玩。
我说:“还有什么用?即使整副牌都给我,我也输定了。”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要玩。我真的抽到那张A牌。我倒宁愿掏钱也要输掉这一局。我再次提议他把支票撕了,但他仍旧坐着,诅咒我。我走了,只留下他一人,穿着衬衫,衣领敞着,坐在桌子旁,眼睛望着那张A牌。
第二天,我们有活干,试飞高速飞行。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我不可能再把支票还给他了。我会让一个痴迷不悟的家伙诅咒我一次,但我不会让他再一次诅咒我。就这样,我们有活干,试飞高速飞行。我不肯碰那飞机。他把飞机拉高到五千英尺,然后加大油门全速俯冲,到两千英尺时飞机两翼折断了。
四年后我退伍了,又成了一个普通公民。我漂泊不定时——就是我第一次尝试推销汽车时——遇上了杰克,他告诉我有一个家伙的巡回特技飞行表演团想雇一个特技飞行员。就这样我认识了她。
二
杰克——他给我一张他写给罗杰斯的便条——告诉我罗杰斯是个非常出色的飞行员,还跟我提起过她,说有人议论她对他不满意。
“你的老朋友对她也不满意呀。”我说。
“大家都这么说。”杰克说。我见到罗杰斯,把条子递给他——他属于那种清瘦、少言寡语的类型——我心想他就是那种娶了在战争中追到的、轻浮、易冲动、漂亮的女人的人,而且让她们一有机会便抛弃他们。所以我感到安全。我知道她是不会为像我这样的人而等待三年的。
我以为她是那种细长、黑糊糊、像蛇一样的女人,浑身裹满鸵鸟羽毛、洒满窝尔窝斯牌香水、躺在长沙发上叼着香烟,让罗杰斯跑到街角熟食店去买装在纸盘里的火腿片和土豆沙拉。但我错了。
她进来时,有点褪色的柔软衣服上围着围裙,手臂上沾着面粉或像面粉一样的东西,她没有道歉,也没有慌乱应酬,什么也没有。
她说霍华德——就是罗杰斯——跟她提起过我,我问:“他跟你说什么了?”但她只是说:“我猜晚上你会觉得挺无聊的,你得帮着做晚饭。我猜你倒宁愿出去喝几瓶杜松子酒和跳舞。”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问,“难道我看上去别的什么都不会做?”
“啊,不是吗?”她反问道。
我们已把盘碟洗刷完毕,关了灯坐在炉光中,她坐在地板上的一个坐垫上,背靠着罗杰斯的膝,边抽烟边聊天,她说:“我知道你觉得枯燥乏味。霍华德曾建议我们到餐馆里去吃晚饭,然后找个地方跳舞。但我跟他说我们平时是啥样就该是啥样,开头是这样,以后也这样。你后悔了吗?”
她看起来好像只有十六岁左右,尤其是围着围裙。她给我也买了一条围裙,我们三人都得一起下厨房做晚饭。“我们以为你跟我们一样不喜欢做饭。”她说,“只是我们太穷了。我们只是飞行员。”
“嗯,霍华德飞行挣钱,足足可以养活两个人呀,”我说,“这已很不错了。”
“他告诉我说你也是一个飞行员时,我说:‘天啊,一个特技飞行员?你在选择家庭朋友时,’我说,‘你干吗不选一个我们可以提前一周邀请他出去吃晚饭的人,我们不但可以指望他光临,还可以指望他带我们出去把他的钱花在我们身上。’但他只选了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穷光棍。”
有一次她跟罗杰斯说:“我们也得给光棍找个女人呀。总有一天他会连我们也厌倦的。”你知道这样的话她们是怎样说的:那些话听起来似乎颇有深意,但你去看看她们,就会发现她们目光茫然,你就会怀疑她们是否想到过你,更别提谈起过你。
也许我真的应该请他们出去吃晚饭,然后看戏。“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不是暗示要你带我们出去。”
“你说给我找一个女人也不是真的啦?”我问道。
她睁大眼睛望着我,神色茫然、天真。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去喝鸡尾酒——罗杰斯不喝酒,就他一人不喝——那天晚上回来后我发现我的梳妆台上有一些化妆粉,或许还有她的手绢或别的什么东西,我上了床,满屋子散发着一股气味,好像她还在屋子里似的。
她问我:“你真的想要我们给你找一个?”
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个话题,过了一段时间,当有某种亲近或男人为女人做的那些小事,即抚摸她们时,她都会转身对着我,好像是我而不是他是她丈夫似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市区遇上了暴雨,我们去了我的住处,她和罗杰斯睡我的床,我则睡在客厅的椅子上。
一天晚上我正在穿衣准备去他们那儿,电话铃响了。电话是罗杰斯打来的。“我——”他刚开口就被打断了。好像有人用手堵住了他的嘴,我能听见他们在说话、低语,更确切地说,是她。“嗯,什么——”罗杰斯说。接着话筒里传来她的呼吸声,她呼唤着我的名字。
“千万别忘了今晚你得来。”她说。
“我没忘,”我回答道,“我是不是把日子搞错了?如果不是今天晚上——”
“你快来呀,”她说,“再见。”
我赶到那里时,他正等着我。他的脸色跟平时一样,我没有进去。“进来吧。”他说。
“我也许把日子搞错了,”我说,“如果你们——”
他把门往后一推。“快进来呀。”他说。
她躺在沙发上,抽泣着。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关于钱的事。“我没法再这样下去了,”她说,“我已尽力了,但我无法忍受。”
“你知道我的保险金是多少?”他问,“要是出了事,你怎么办?”
“我究竟算什么?哪个住公寓的女人不比我富有?”她没有抬头,脸朝下躺着,围裙乱七八糟地压在身下。“你干吗不辞掉这份差事,像别的男人那样找一份保险金高一点的工作呢?”
“我得走了。”我说。我待在那里真是自讨没趣。我走了出去。他跟着我一起走到大门前,我们俩不约而同地转身往楼梯口的那扇门望去,她脸朝下躺在门边的沙发上。
“我手里还有一点赌金,”我说,“我看我白吃你们那么多,还没来得及花掉这些钱。所以如果有急用的话……”我们站在那儿,他让大门开着。“当然,与我不相干的事我绝不掺和……”
“要是我是你的话,我也不会掺和。”他说。他开了门。“明天机场见。”
“再见,”我说,“机场见。”
我差不多一个星期没见到她,也没有她的消息。我倒是天天都见到他,终于我问:“米尔德里德近来怎样?”
“她出去玩去了,”他回答说,“去娘家了。”
随后的两个星期我天天都和他在一起。每当我在飞机上边我都会转眼瞅瞅他那张被眼镜遮着的脸。我们压根儿没有提到她的名字,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她又回家了,邀请我晚上去吃饭。
当时是下午。他一整天都忙着搭载乘客,我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盼着夜晚早点来临,思念着她,偶尔也想想别的事,但更多的时间想的是她终于又回家了,又和我呼吸着同样的烟雾和尘埃,我一时心血来潮,决定去她那儿。
事情很简单,就好像有个声音在呼唤:“去那里。现在就去,马上就去。”我去了。我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她独自一人在炉火前看书。那正像是破裂的油管里迸发出来的汽油在你周围燃烧。
三
真有趣。每当我在飞机上边,我都要转眼瞅瞅挡风玻璃后面他的脸,心想他知道些什么。他一定很快就知道了。唉,比如说,她为什么一点儿都不回避。你知道,她说话做事毫不遮掩:
她坚持挨着我坐;用那种不同于你给她们打伞或披雨衣时的方式触摸我,那方式任何人一眼都能看出来,她还以为他没有看见:不是她知道他不可能看见的时候,而是当她以为他也许不会看见的时候。每当我解开安全带爬出机舱时,我都要转眼看看他的脸,琢磨他在想什么,他知道多少或怀疑多少。
下午他忙碌的时候我常去她那儿。我常常在一旁等着,直到看到他接的活够他忙一天,然后就找个借口溜之大吉。有一天下午,我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他起飞后就走,他却关掉油门,伸出身子,示意我过去。“别走,”他说,“我想跟你谈谈。”
我顿时明白他已经知道了。我一直等到他做完最后一次飞行,在办公室里换飞行服。他望着我,我望着他。“一块儿吃晚饭吧。”他说。
我进门时他们正等着。她穿着一件柔软的衣服,走过来把手搭在我身上,当着他的面吻我。
“我跟你走,”她说,“我们谈过了,我们都认为发生那种事情以后我们不可能再彼此相爱,这是唯一理智的事。以后他可以重新找一个他爱的女人,一个不像我这样坏的女人。”
他望着我,她抚摸着我的脸,在我的脖子上发出低沉的呻吟,我像一块石头似的。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压根儿没有在想她。我在想,他和我在天上时,我爬上机翼,会发现他丢开操纵杆,让飞机自动飞行,他知道我明白他丢开了操纵杆,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没事的。我们就像一块木板靠着另一块木板,她缩了回去,望着我的脸。
“你不再爱我了?”她望着我的脸说,“你要是爱我就直说吧。我把什么都跟他说了。”
我很想离开。我想跑开。我不是怕。而是因为那里又热又脏。我想远离她一会儿,让罗杰斯和我出去,到一块又冷又硬又安静的地方去解决问题。
“你想怎么办?”我问,“你会跟她离婚吗?”
她紧紧盯着我的脸,她放开我,冲到壁炉前,头放在手腕上大哭起来。
“你骗我,”她说,“你没有说实话。啊,天啊,我干了些什么呀?”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如同任何事情都有个恰当的时候。如同没有任何人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如同一个女人,即使你爱她,对你来说也只是部分时间是女人,而其他时间则只是一个与男人看法不同的人。她对什么是高雅,什么是庸俗,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我走过去,用胳臂环抱着她的身子,心想:“见鬼,你能不能不哭!我们俩都在尽力照顾你,因此你不会受到伤害的。”
因为我爱她,你知道。在世人的眼中,没有什么比共同的罪孽更能使两人更加亲密。他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是我先认识她、娶了她,他就该是我了,我也就有了我的机会。但是是他有了那个机会,因此当她说:“那么你把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所说的话再说一遍。我说了我把事情全都跟他说了。”我说:
“全都说了?你说把事情全都跟他说了?”他望着我们。“她把什么都跟你讲了?”我问。
“讲没讲倒没关系,”他说,“你想要她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说:“你爱她吗?你会好好待她吗?”
他脸色灰青,如同遇到一个久别重逢的故人,你说:“天啊,这是罗杰斯吗?”我最后离开时,离婚的事全定下了。
四
第二天早晨我到机场时,飞行表演团的主人哈里斯告诉我那份工作的特殊性;我猜我是忘了。他说他曾告诉过我。最后我说我不愿和罗杰斯一块儿飞。
“为什么不?”哈里斯问。
“问他好了。”我回答道。
“他要是同意搭你,你愿意上天吗?”
我说我愿意。这时罗杰斯走了出来;他说他愿意搭我。所以我认为他一直都熟悉这份差事,一直都在套我,在骗我。我们一直等到哈里斯出去后才说话。“难怪昨晚你总是转弯抹角的。”我说。我诅咒他。“这下你赢了,不是吗?”
“那你自己来驾驶吧,”他说,“我来干你的那份苦差事。”
“你以前干过类似的工作吗?”
“没有。不过,我可以干,只要你能好好驾驶。”
我诅咒他。“你倒感觉良好,”我说,“算你抓到我了。来吧,你倒是笑呀。来吧!”他转身朝那架破飞机走去,然后往前排座位里钻。我冲过去抓住他的肩膀,使劲往回拉。我们面面相觑。
“如果你想挨揍的话,”他说,“我现在不想揍你。我们返回地面再说。”
“不,”我说,“因为我也想还一下手。”
我们俩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哈里斯从办公室里望着我们。
“好吧,”罗杰斯说,“把你的鞋给我,行吗?我这里没有胶底鞋。”
“坐下吧,”我说,“这究竟有什么关系?要是处在你的位置上我看我也会这样做的。”
飞行表演在一家正在举行狂欢活动的游乐场上空进行。地面肯定有两万五千人,像一群五颜六色的蚂蚁。我那天冒了一生从未冒过的风险,而这些冒险从地面是无法看见的。
但是每次冒险时,飞机总在我身下保持平衡,使我不受侧面压力或其他压力的影响,好像他都知道我想法似的。你知道,我觉得他在耍我。我回头盯着他的脸,朝他叫道:“来啊,你把我抓在手心里了。你的胆子到哪儿去了?”
我猜我是有点失去理智。不管怎样,我想起我们俩在天上,互相叫骂,下面小虫子般的人群望着我们,等着看翻筋斗的好戏。他能听见我,而我却听不见他;我只能看见他的嘴唇在动。“来吧,”我叫道,“抖抖翅膀吧;我很容易掉下去的,明白吗?”
我有点失去理智了。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一种你一定要干某件事的感觉,不管是什么,但你知道肯定要发生的事情。我猜恋爱中的人或自杀者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朝他叫:“你想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吧,嗯?想把我从水平着的飞机上抖掉,不那么正常吧?好吧,”我叫道,“开始吧。”我回到中间部位,把绳子抖开,把它来回绕在前面的应急支柱上,我紧贴着应急支柱站好身子,我回过头看着他并发出了信号。我有点失去理智。我还在朝他尖叫;我也不明白我在叫些什么。
我想我也许已经掉下去死了,而自己却不知道。绳子发出呜呜的叫声,我往地面望去,全是五颜六色的小斑点。钢绳发出呜呜的叫声,他加大油门,地面在机头下滑了过去。我等着,直到看不见地面,地平线也滑了过去,我眼前只有天空。然后,飞机正要陡直上升翻筋斗时,我放开绳子的一端,猛地把绳子往回朝着他的脑袋扔了过去,把胳臂伸了出去。
我不是想自杀。我想的不是自己。我想的是他。我是想竭力让他出丑就像他曾让我出过丑一样。我要让他干一些他无能为力的事情,就像他曾让我干过我无能为力的事一样。我想努力打败他。
飞机翻筋斗翻到底朝天时他摔掉了我。我又看见地面以及地面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小斑点,我脚底没有了压力,我正在往下掉。我刚翻了半个筋斗,正准备倒着做第一个平螺旋时,背上突然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这一下几乎要了我的命,我顿时失去了知觉。等我睁开眼睛时,我仰天躺在机翼上,头悬挂在后缘上。
我滑到了机翼斜面的底部,无法在机翼的前缘弯下我的膝盖,我能感到机翼在我身下滑动。我不敢动弹。我知道我如果试图迎着滑流坐起来的话,将会从后面掉下去。根据机尾和地平线我知道我们现在正在浅俯冲倒飞,我看见罗杰斯在座舱里站了起来,解开安全带,我轻轻转了转头,发现我要是掉下去的话,要么整个儿掉下去,要么肩膀撞在机身上。
我躺在那儿,机翼在我下边蠕动,我感到肩膀开始慢慢悬空,脊背滑下去时我一根根数着脊骨,看见罗杰斯沿着机身朝前座爬来。我久久地望着他顶着压力慢慢往前移,裤管被吹得啪啪作响。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的双腿伸进了前座舱,接着我感到他的手抓住了我。
我们中队有一个家伙。我对他没有好感,他对我也恨之入骨。嗯,有一天我因阀门漏气被困在十英里高的线上,他救了我。我们着陆后他说:“别以为我只是救了你。我是在抓一个德国丘八,我捉到他了。”
他诅咒我,眼镜架在额头上,手摸着屁股,诅咒我时像是在笑。不过没关系。你们每人驾驶的都是骆驼牌飞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的战斗机)。你要是出事,就太糟了;要是他出事,也同样太糟了。不像你在飞机的中间部位,他在驾驶,只需稍稍减速或在翻筋斗时稍稍改变方向就行了。
但我那时还年轻。天啦,我曾年轻过!我记得一九一八年停战纪念日的那天晚上,我正在亚眠(法国北部一城市)到处乱窜,带着一个那天早上我们从信天翁飞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飞机)上打下的该死的囚犯,以免他落到法国宪兵的手里。
他人不错,可那些混账步兵想把他关在一间写满S.O.S(呼救信号)和全是喝得醉醺醺的厨子之类的棚子里。他远离家乡又吃了败仗,我真替那家伙难过。我当年真的年轻过。
我们都曾年轻过。我记得一个印度人——他是王子,牛津大学学生,头上裹着头巾,戴着伪造的证明他是少校的肩章——说我们参加过战斗的人全都死了。“你们不会知道的,”他说,“但你们全都死了。有一点不同:那边的那些人——”他手用力朝前线的方向指了指——“并不在乎而你们并不知道。”
他还说了一些别的什么,还得呼吸很长一段时间啦,是某种在行走的葬礼,等等;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日子)便已经去世,但不知道自己已经去世的人的灵车、坟墓和墓碑,他说。他是一个怪人、一个怪诞的人。也是一个小个子的好人。
但是,我躺在标准牌飞机上,一根根数着像一群蚂蚁似的爬过机翼边缘的脊骨时,直到罗杰斯抓住我时,我并没有完全死去。那天晚上,他到基地来跟我告别,捎来一封她给我的信,我第一次得到的她的信。
她字如其人;我几乎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感觉到她抚摸我的双手。我没拆开便把信撕成两半,扔在地上。但他把碎片捡起来,重新递给我。“别犯傻了。”他说。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他们现在已有小孩,一个六岁的男孩。罗杰斯给我来信,大约六个月后我才收到信。我做了他的教父。一个从未见过你而你也永远不会见到的教父,真有趣,不是吗?
五
我对莱因哈特说:“提前一天够吗?”
“一分钟就够了。”他说。他按了一下蜂音器。维斯特小姐走了进来。她是个好人。偶尔我不得不吐吐怨气时,我和她便到街对面的乳品店去共进午餐,我给她讲她们,讲女人的故事。她们是最糟的。
你知道;假如叫你去表演,她们就会挤得满满的一车等在门口,我们会挤进去,全部去逛商店。我在车流里东躲西闪,寻找一个泊车的位子,她说:“约翰坚持要我试试这辆车。但我告诉他,买一辆像这样难找到泊车位的车真是蠢极了。”
她们用那种警惕、锐利和怀疑的眼神望着我的后脑。天知道她们以为我们有什么;也许是一件可以像折叠椅一样折起来靠着灭火栓放好的东西。见鬼,我连卖直发器给一个因铁路事故而失去丈夫的黑人遗孀都不行。
维斯特小姐走了进来;她是一个好人,只是有人跟她说我一年就换了三四个工作,都没干多久,还跟她说我曾经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她一直缠着问我为什么不做飞行员,为什么不重操旧业,既然飞机更受欢迎,既然我既不善于推销汽车,也不善于干别的,这些只有女人才会干。
你知道,着急也好,同情也好,你不能像对男人那样叫她们闭嘴;她走了进来,莱因哈特说:“我们准备不再雇莫纳汉先生了。带他到出纳那里去。”
“不用麻烦了,”我说,“钱留着给自己买一枚戒指好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