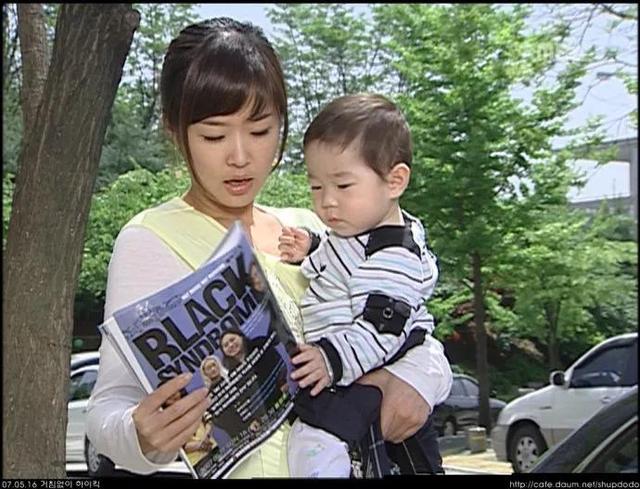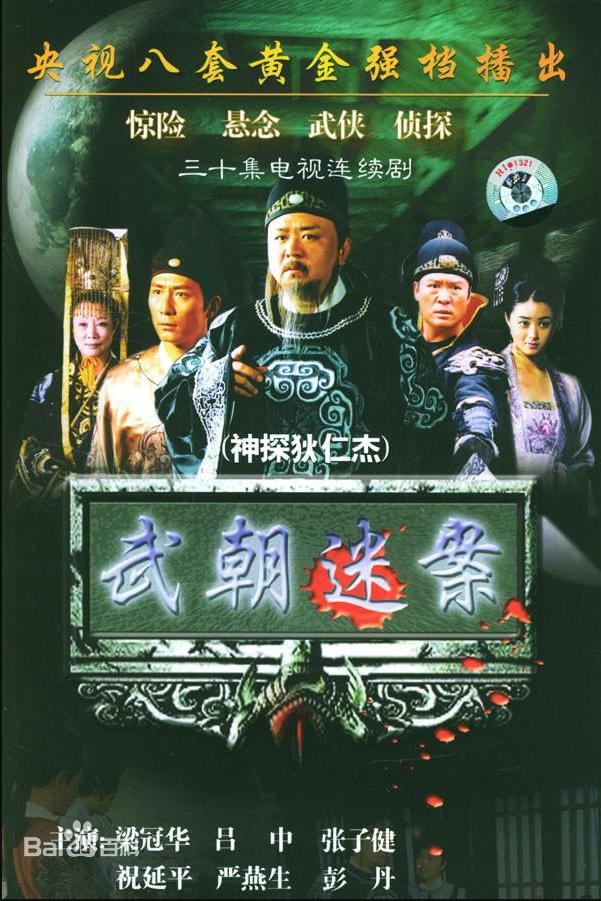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美国总统给中国人提了一个大胆的游戏,让中国人和美国人互相交换国土!你会不会同意?
这里的交换国土,指的是只交换人口,国土上的建筑、文化古籍、军事装备、科技公司等一切附带的东西都交给对手。
我想,光是这个大胆的假设本身,就足以调动所有人的讨论欲,有多少人认为换了是占了大便宜就会有多少人觉得换了是吃大亏,支持和反对双方都能找出无数的理由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这个点子,其实是刘慈欣在自己的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里面写到的。
大家好我是南瓜,之前咱们介绍了《球状闪电》,《球状闪电》里的诸多细节在《三体》里都有后续,所以被粉丝们称为《三体》前传。
而这篇《超新星纪元》,在某种意义上,是《三体》的后传。
《超新星纪元》创作时间是2000年前后,大刘的原稿改过好几版。
但是,到2022年了,小说里诸多细节,都在当代人身上得到了应验。比如为什么当代年轻人会普遍感到迷茫?为什么“精神内耗”、躺平会流行?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在长期和平之后,走向各种思潮群魔乱舞的今天?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本小说是对当代人类社会集体性的现代性危机的一个精准的预言。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刘慈欣的这部很有意思的小说《超新星纪元》。
1
故事的背景是一个标准的灾难片:
一天,银河系之外的大麦哲伦星云出现了一次超新星爆发。
超新星的一种未知高能射线彻底破坏了人体细胞中的染色体,这种未知射线穿透力极强,就算在矿井中的人类也不能避开。
换言之,全人类集体经历了一次切尔诺贝利,大家的染色体都被损伤了,无人幸免。
根据科学家的判断,这种染色体损伤可以修复,13岁的孩子97%可以修复,12岁和12岁以下的孩子百分之百可以修复,但其他年龄段的人就没办法了。
也就是说,这场超新星爆发之后,13岁以上的人类会在十个多月到一年的时间里逐渐死亡。
一年以后,地球将成为一个只有孩子的世界,整个人类社会的秩序都要经历大洗牌!
为了让自己的国家不在未来的竞争中落败,各个国家都通过不同的方法,用最短的时间选拔、培养出了国家的下一代接班人。
与此同时,全世界有核国家纷纷宣布销毁核武器,集体把核弹送入太空引爆了,说要把一个干净的世界留给孩子们,以孩子们爱好和平的天性,战争以后肯定会从人类世界消失。
主角们是中国的孩子们,中国的领导层用让孩子们玩战争游戏的方式,迅速选出了最有政治能力的几个孩子——晓梦、华华和眼镜等人,强行在一年之内把管理一个国家需要掌握的知识全部灌输给选中的孩子们。
但显然,很多知识超出了这个年纪孩子的理解能力,持续一年的大学习只能是让孩子们勉强掌握了一个大概。
以防万一,国家还给孩子们留下了五个特殊孩子组成的特别观察小组,这五个人肩负一个神秘的使命,平时他们不干涉其他人的指挥,但需要了解战时的一切机密,在必要时刻履行职责。
时间不等人,大人们在做完了一切能做的之后,默默去往终聚之地迎接自己的死亡。
人类文明被拦腰截断,全世界的孩子们都被迫被丢到了冰冷的世界里。
虽然之前进行过试运行,但是超新星纪元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孩子们还是慌乱了一阵子。
全国的孩子们都在找爸爸妈妈,有的饿了不知道去哪里找吃的,有的地方着火了没有消防队出动,有的医院没有人照顾一两岁的婴儿,有的地方发大水了没有人救灾……
晓梦、华华和眼镜等人在超级计算机“大量子”的帮助下,勉强控制住了局势,没有让国家陷入混乱。
稳定以后,几个孩子们抓紧时间到全国各地进行视察,结果他们却发现,孩子们对于新世界的看法出奇得一致,他们都觉得累、无聊、失望。
一开始的新鲜劲过去以后,孩子们很快就发现,代替大人们工作是一种折磨。
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多数孩子最终选择了旷课、旷工,去往网络世界逃避,逃跑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国家陷入了瘫痪。
大人们担心孩子们的未来,所以在临走之前竭尽全力生产了大量的物资,加上人口突然大量减少了,全世界一下子物质极大丰富了,怎么用都用不完。
于是,孩子们罢工之后,就走到大街上,冲进了商店里,疯抢各种玩具、牛奶、糖果巧克力,开party,吃各种宴席,开始酗酒,然后陷入漫长的沉睡。
因为涉及的人太多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已经无法维持,晓梦、华华和眼镜怕大家出事,好心地隔一段时间就问问小朋友们怎么样了,但小朋友们嫌他们烦,叫华华班长,叫眼镜学习委员,叫晓梦生活委员,还是过着吃喝享乐,完事在大街上倒头就睡的日子。
这个时代被称为“糖城时代”。
一开始,孩子们以为这是中国孩子特有的问题,但到了小说后面才发现,全世界孩子都一样,只是醉生梦死的方式不同罢了。
小说截止到这里的故事,乍一看像是一个童话故事,其实,如果我们把小孩看成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把大人们看成经历过世界大战、冷战的那一代老人们,这个故事的主题一下子就变成了现代社会人类的精神问题了。
整个20世纪,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富足,但与此同时,两次世界大战把人类折腾了个够,战后还经历了漫长的冷战时期,人类的精神一直高度紧张,像一个紧绷的弦。
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是不少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处于一个相对被压抑的状态。
所以,随着新一代的人进入社会以后,人类的精神又集体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传统的国家、民族等等宏大叙事在一段时间里逐渐崩塌,个体开始成为大家关心的主体,对过去羞于提起的个体利益,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和主张了。
客观来说,这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因为追求每一个人的独立和解放,就是共产主义者的终极目标。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阶段人类社会对个体利益的关注过了度,把自由变成了自私,把不负责任变成了追求个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话可以公开地喊,两头要好处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可以脸不红心不跳,集体的意义被忽略乃至被否认,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这种情况下,虚无主义、现代性危机应运而生。
所谓的虚无主义,就是在哲学上认为世界,特别是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没有真相,没有本质价值。
说人话就是虚无主义者就像是杠精,你跟他说任何你觉得有价值的、高尚的、精彩的、让你感动的东西,他都会反问你一句:“那有什么意义呢?”然后开始解构。
你跟他说某某历史人物英雄盖世,他就跟你说他不过是一个小丑,没什么值得称赞的。
你跟他说你关心新闻里说不惜一切代价打赢和美国的斗争,他就说你有什么好关心的?你是那个“我们”吗?你是那个“代价”啊!
你跟他说国家发展越来越好,他就说“我不关心大国崛起,我只关心小民尊严”。
甚至,就连你纯粹是在为一个小人物的不屈精神而感动,他都要跳出来怼你一句:“不要歌颂苦难”。
人类是自然界最喜欢给自己的生命找意义的动物,这种对一切崇高事物的解构,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家、民族等大量“想象的共同体”都虚无化了,只剩下个体看得到摸得着的“小确幸”有意义。
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很多人像小说里一下子失去了大人们的孩子一样,在这个时代失去了方向感,陷入了“精神内耗”,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化艺术,《一无所有》、《大话西游》等等,出现了很多去别的思潮中找归宿的人,宗教思想、白左思想等等等等。
在国家培训晓梦、华华和眼镜怎么当一个国家的领袖时,带他们去看了盐和味精的生产线,三个小孩子看完之后,晓梦说,原来要管理国家首先得保证这些东西供应充足,每天都要给国家的公民提供一列车的味精、十列车的盐、一个大池塘的油、几座小山的米面,有一天供应不上国家就会混乱,十天供应不上国家就完蛋了。
眼镜附和着说:“这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华华说,看到这长长的列车,傻瓜也该明白这道理了。
这时候,国家领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可是孩子,有许多十分聪明的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现实中不就有很多人是如此吗?脱离了物质匮乏之后,很多人下意识地以为,民主、自由、环保、爱与和平这些东西是天生就应该有的,甚至要求许多饭都吃不饱的发展中国家放弃经济发展,直接去追求这些东西。
越是物质条件好的发达国家的人,越是容易得这种白左病。
小说里,孩子们为了逃避无聊,整天泡在网上,为了决定干什么,大家给国家发展提意见,举行互联网公投,可结果一看,提出来的都是一些小孩子气的提议:
什么要天天过年,每人每天发十包小炮、一百块压岁钱。
什么国家给每个班配50台游戏机,一上课就玩儿,游戏积分不够就退学。
什么怕拍一部一万集的动画片,永远放不完。
你问他没有人生产,大家没粮食吃了怎么办呢?他就说“生产生产,烦死了,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
一到投票做计划的时候,越是迎合大众的支持率越高,而不管现实是否执行得了,反正在网络世界里写小作文又不犯法。
仔细想想,这说的不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吗?
小说里糖城时代不是个例,而是所有现代化国家共同的现代性危机。
它表现为自我定位的丧失、创造力的日渐衰竭、对英雄主义的否定、核心价值观的丧失、道德框架的四分五裂。
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历史不同,现代性危机在细节上有一些不同。
在小说里,中国的孩子们集体罢工之后是进入集体享乐。
但是美国邀请中国孩子去开会的时候中国孩子才发现,美国孩子不吃糖不酗酒,而是把军火库里的装备拿出来天天在街头打仗,装甲车对战,RPG对轰,四亿人的枪战梦想,自由美利坚,枪战每一天,在美国出门不带枪,就像出门不穿裤子一样。
小说里这段描述,可以说是很有美国特色了。

当然,“躺平”享受和集体性的“精神内耗”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束,物极必反,在经历了“糖城时代”以后,孩子们的世界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2
没过多久,美国小总统戴维牵头办了孩子们的第一次联合国大会,决定要去南极洲办奥运会,只是所有奥运项目全部换成战争游戏,以奥运会的名义打仗玩儿。
一开始其他国家不同意,但仔细想想,南极洲有丰富的资源,自己不占,等于就是拱手送给了敌人,思忖再三,还是跟着美国一起加入了游戏。
在确定游戏项目的时候,美国提议玩航母游戏,但因为没几个国家有航母,不得不改成驱逐舰游戏。
俄罗斯提议玩坦克游戏,中国提议玩扔手榴弹游戏。
有些小国家别出心裁,比如越南提出玩游击战游戏,美国代表当场拍桌子暴跳如雷,强烈抗议。
还有日本代表拿出武士刀提议进行冷兵器游戏。
很快,南极洲的这场特殊的奥运会,就变成了孩子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游戏很快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拉都拉不住了。
因为和大人不同,小孩子们普遍是游戏思维,还没有经历过太多人情世故,不太理解生命的宝贵。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相比恐惧,孩子们更多感受到的是玩游戏的乐趣。
孩子们把躲在工事里互相扔手榴弹的游戏称为“手榴弹排球”,把互相冲锋人扔手榴弹的游戏称为“手榴弹橄榄球”。
某种意义上,孩子比成年人更有承受力更冷酷。
在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的冷兵器对战游戏里,日本孩子出其不意放成群的军犬咬人,中国孩子被迫用手榴弹反击,最后被判输,因为双方都违规了,只不过情节严重的程度不一样,中国的手榴弹是热兵器,日本的顶多是温兵器。
因为各个国家在游戏中的表现,直接决定了游戏之后南极洲要怎么瓜分,所以大家都不断增兵,打得越来越激烈。
美国孩子作为游戏的发起者,原本的科技优势在这种比赛中发挥不出来,美国孩子急了,率先打破游戏中不互相袭击对方指挥中心的原则,用洲际导弹给俄罗斯基地打了一发装满巧克力和雪茄的导弹以示威胁,俄罗斯还了美国一发伏特加和俄罗斯套娃。
在这次试探中,由于双方的反导系统太复杂,孩子们操作不过来,导弹都击中了。
眼看有效果,美国孩子直接朝中国孩子丢了一颗核弹,摧毁了中国孩子的基地。
原来,之前美国跟着销毁核武器都是作秀给世界看的,实际上是裤裆藏雷,给美国孩子们留了战略核武器。
中国孩子因为临时换了指挥中心逃过一劫,但在核爆中,三个集团军有一个丧失了战斗力,港口被毁,部队供给出现了严重问题,眼看要输了。
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中国领袖给孩子们留下的五人特别观察组行动了,因为中国的领袖们也给中国孩子们留下了一个顶级玩具——东风!
中国的孩子们向美国孩子发射了一枚四百万吨级的洲际核导弹,直接把战争游戏拖回了起点。
由于僵持不下,再加上气候变化,南极洲再次冷了下来,大家不得不放弃瓜分南极洲的想法,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在看南极洲奥运会这段剧情的时候,大家肯定会有一种强烈的熟悉感,之前孩子们刚掌握世界的时候,故事的进程一度会让你以为这小说是郑渊洁老师写的,郑老师快把笔还给大刘!
但在南极洲长期的斗争中,孩子们的思维方式越来越像公元时代的成年人了,他们开始从集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开始从底线思维、冷战思维看待国与国的斗争。故事的进展越来越像是《全频带阻塞干扰》、《三体》。
换言之,原本在新时代被遗忘,甚至被否认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又回来了。
这轨迹和中国人这几年思想的转变如出一辙——当代年轻人越来越理解共和国最早一批的缔造者们的思想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现代性危机的产生,也有着它的经济基础。
有人也许会说,虚无主义、现代性危机,都是个人精神层面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
小说里晓梦、华华和眼镜去巡视发电厂的时候,一个孩子说: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控制台前,盯着这些仪表和屏幕,不时把走偏的参数调整过来,我觉得自己都快成这部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了。唉,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呀?”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尤其是捷克的斯维塔克认为,现代性危机,就是因为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失去了平衡导致的,原本以人的自由为最终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沦为了以推动消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现代工业社会了。
捷克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把人的劳动异化。没有人愿意当一个无知的螺丝钉,自然就加剧了社会矛盾和个体的无意义感,出现了存在危机。
一旦这个基础发生了转变,人们的思潮当然也会随着转变。
现实中,当代中国人的思潮就是这样来回转变的。
大家说当代年轻人的时候,有一个观点是说,当代年轻人在国家大事上表现出极端的乐观,但在自己的未来上又表现出极端的悲观。
但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00年前后,许多人是既对自己未来悲观,也对国家未来悲观,觉得我们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失败的民族,很容易被公知的历史虚无主义欺骗,否定自己的文化、否定自己的民族、进而彻底否定自己的存在。
那个时候许多人眼里政府是不值得相信的,宏大叙事都是假的,历史上的英雄们是宣传出来的。
个体意义被无限拔高,爱情剧、职场剧是主流。
可等到川普宝宝上台,给全体中国人无故施加了生存威胁之后,许多人就像小说里被美国核弹炸了的孩子一样,一夜之间长大了。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大家终于理解了当初革命前辈们的拼搏奉献,不是一种无聊的宣传,而是集体主义和个人理想的结合。
那一个个创造了历史的猛男们,在闹革命的初期,很多时候都只是为了糊口饭吃,但在革命的路上,他们既实现了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又成功保家卫国,实现了集体理想。
被资本压榨的大家终于意识到,集体主义和个体的自由、解放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所以中国的年轻人还可以从英雄主义的传奇里,从民族崛起的叙事里,从小人物奋斗的故事里感受到力量,从现代性危机里摆脱出来,而不是像日本年轻人一样彻底躺平。
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说的:
因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
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从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最终走向改造世界,这是共产主义者们必然会走的一条路。
只不过,这种思想回潮还没有在世界上变成普遍现象,西方国家反而是越走越远,因为比起宗教催眠,马克思主义的入场券太贵了,当然会拥有更少的信徒。
3
从南极洲回来以后,美国小总统戴维就被国会弹劾了,新上任的是一个小姑娘贝纳。
因为美国在南极洲的行动失败了,美国人颓废起来了,美国国内又开始了自由美利坚,枪战每一天。
新上任的贝纳迫切地需要解决美国孩子们情绪低落的问题。
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沃恩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认为,美国的孩子们这样,是因为失去了美国的力量,很没有精神。
美国的力量是什么呢?
贝纳说,难道不是我们的航母和宇宙飞船吗?
但是沃恩说,不对,美国的力量不在这里,美国人真正的力量是西部大开发时期形成的,那时候美国西部远不是电影里描绘得那么浪漫,时时刻刻有饿死、病死、被强盗杀死的风险。
但那一代美国人依然大笑着走进严酷的西部世界,谱写了美国的史诗,探索新世界,争霸新世界的欲望才是美国人力量的源泉,那些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但是,自从买下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之后,美国人就不再想要去开拓新的疆界了,变得越来越迟钝、软弱,嬉皮士和朋克成了新时代美国的象征,新时代到来以后,孩子们都迷失了方向,只能在街头暴力中麻醉自己。
小说里沃恩说的这段话,其实就是美国人陷入现代性危机的通俗描述。
黄金时代的美国人精神是昂扬向上的,美国人痴迷的《星球大战》、《星际迷航》,就是在文艺作品里一次次展现自己对世界的探索欲和征服欲,一次次地回味西方世界的殖民史。
当年斯诺根据自己在延安的经历写下《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出版之后,引起了轰动,吸引了一大批的美国人,其中有不少后来还来到延安参观。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对与自己价值观完全不同的文明充满了探索欲。
但到了今天,你在当代的美国人身上再也看不到这种精神了,他们变得狭隘无知、不思进取,沉浸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对中国,对世界的其他地方充满了刻板的认知,不愿意看清真相。

为了改变这一切,沃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游戏:
和中国孩子们交换国土!
这里的交换,仅仅只交换中美的孩子们,国土上附带的其他一切东西都不动。
这个游戏石破天惊,对双方而言都是有利有弊。
就算现在把这个问题拿给弹幕同志们讨论,大家肯定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支持交换的人可以说美国毕竟科技高超,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以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拿到美国这块土地只会觉得咱老李八辈子也没打过这样的富裕仗,这还不直接起飞?
不支持交换的人可以说中国人的精神力量来自我们这片土地上传承几千年的文化,一旦失去了这些东西,中国孩子们会迅速变得比美国孩子们还要堕落,到时候会被变得更强的美国孩子轻松击败。
刘慈欣没有直接描写交换国土之后发生了什么,而是描写了交换国土多年以后的场景,间接暗示了交换的结果。
那时候已经是超新星纪元三十多年了,在描述中,主角已经携家带口,定居到了另一个星球,从短短三十多年人类就掌握了在外太空定居的技术水平看,交换国土的结果显然是成功的,人类社会摆脱了现代性危机,进入了一个创造力爆发,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
在这一段里,大刘还写了一个小段子。
主角作为历史研究者,怒喷了另一个把历史当小说写的史学研究者刘静,说她治学态度极不严谨,还标榜自己的学术思想是受了自己父亲的影响。结果他一查,刘静那个公元世纪的父亲是个写科幻小说的,他找来其中一篇一看,简直就是垃圾,小说里的鲸鱼居然长着牙齿(出自刘慈欣的《鲸歌》),有这种父亲,难怪刘静做学问是这种态度。
好家伙,我讽刺我自己。
这里交换国土以后,人类怎么摆脱现代性危机,找到了精神上的解药,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都是还没发生的历史,就算我们想要凭借对现代社会的理解进行推测,结果也很可能是南辕北辙,因为这个问题太宏大太复杂了。
就算是现实中的哲学家们,也无法给出这个问题的确切回答。
我们可以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有周期性的,我们会在精神上反复进入“儿童时代”和“成年人时代”,船到桥头自然直。
也可以认为,人类在群体性的迷茫之后,最终还是投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怀抱,走向了从实践出发改造世界的过程,通过改变世界的经济基础,解决了现代性危机。
在现实的故事中,没有让世界彻底洗牌的超新星爆发,解决当代人的“精神内耗”,只能靠我们自己。
小说里,大人们和孩子们最后道别的时候,刘慈欣写道:
“最后的分别是平静的,在同孩子们默默地握手后,大人们互相搀扶着走出大厅,主席走在最后,出门前,他转身对新的国家领导集体说:
‘孩子们,世界是你们的了!’”
是的,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