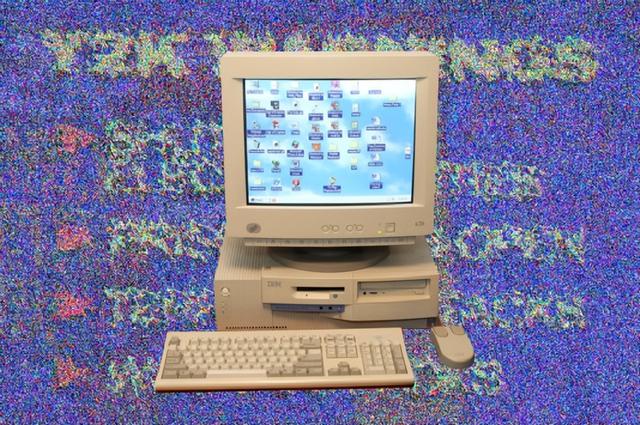“战国”一词,在当时就已有了,但还没有作为特定的专用名词。例如,《成国策•秦策四》载顿弱说:“山东战国有六”。《楚策二》载昭常对楚襄王说:“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赵策三》载赵奢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燕策一》载苏代又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到了汉代初年,“战国”这个词义还没有变化。《史记•平准书》:“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便是其证。历史上把秦统一前的“七雄”称为“战国时代”,应该是从西汉末年刘向编定《战国策》一书后开始的。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大变革的时期。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崩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到战国中期山东半岛的邹国仍有前社会的残霞余辉。公元前七六世纪之交,旧社会开始加速溃散解体,新的社会也在这时发出曙光,到了秦的统一,中国才大体上告一段落。
这个转变就各诸侯国来说,虽然变革的时间有先有后,变革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其变革,都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看直接关系。
铁器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的发展

战国时代,由于冶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铁矿的开发,铁制工具已经在当时的各种生产领域中普遍使用。据《管子》所记,当时必须有铁制工具,“然后成为农”,“然后成为车”,“然后成为女”(《轻重乙篇》),“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战国中期,孟子曾以社会分工为必然而反对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许行,并问其弟予陈相说:“许予以釜甑爨,以铁耕乎?”(《膝文公上》)可知当时中原地区“铁耕”已经非常普遍,许行不用“铁耕”已成了出乎常情的事。从有关文献记载和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铁制农具有耒、耜、犁、铫、耨、锄等;铁制手工业工具有刀、斧、凿、锯、锥、锤等;铁制兵器有仗、矛、剑、甲胄等;在人们的装饰品中,如带钩也有用铁制造的。

铁器的普遍使用,有助于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铁制农具的推广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便于深耕、发土、平田、除草和收割,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耕作技术的进步

战国时代,耕牛的使用虽然还不很普遍,但也已开始推广。在牛拉铁犁的发明与使用以前,翻地要靠人力,即所谓“耦耕”。使用牛耕比耦耕提高效率很多,不过当时所用的犁铧比后世的要笨钝窄小得多。从山西浑源出土的牛尊来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都已穿有鼻环,说明牛已被牵引从事生产劳动。战国时称牛鼻环为“三棬”,《吕氏春秋•重已》《尚书•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与)厥疆土。”
《尚书.尧典》云:“蛮夷滑夏”,又云:“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姿所以之,顺也。”春秋晚期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到齐国,其子孙变为农民“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福》),即把养在宗庙祭祀用的牺牲放到田亩里耕作,说明当时的牛耕情状。战国时代,牛耕的进一步普遍和技术的进步,从河南辉县固围村和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犁铧皆为V形,前端尖锐,后端宽阔,锐端有直棱,能加强刺土力,便可证明。
耕作技术的进步,主要出现了“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

易是快速的意思,“易耨”或称为“疾耨”。《管子•度地》说:“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耨”。“疾耨”也或称为“熟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表明深耕已经普遍推行。《吕氏春秋•任地》说:“上田弃亩,下用弃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这里所说的“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就是说深耕一定要达到表土下层水墒部分,才能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他们已认识到通过深耕可以收到消灭杂草和虫害的效果。《吕氏春秋•辩土》又说:“故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然后咸生。”这里所说的“下得阴”是指农作物从地下吸收水分和肥分;所谓“上得阳”,是指农作物从天上得到阳光。深耕不仅能提高田亩产量,而且还可减轻虫旱之害,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