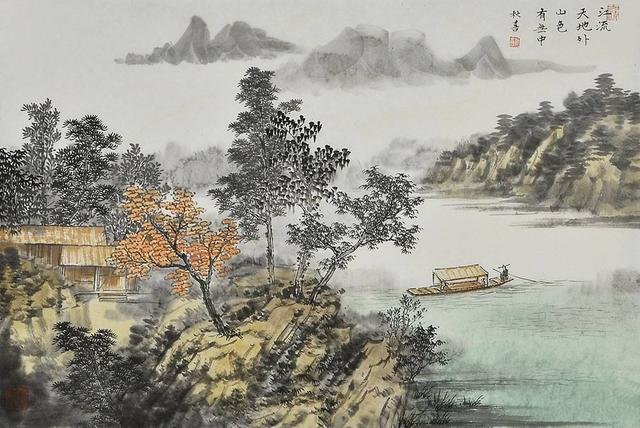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必删
去上声的使用
上去二声,其音决然不同,上声清而高,去声重浊而远,而在曲调中反是。
词的领字或者一字豆都有很多是用去声。
调之高者,宜用去声字;
调之低者,宜用上声字。
故词中逢上、去二声连用之处,用去上者必佳,用上去者次之,最好不要用相同的两仄声,如“上上”“去去”。
如
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对潇潇暮雨(上去)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上去)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周邦彦《花犯·梅花》
粉墙低,梅花照眼(去上),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去上)铅华,无限佳丽。去年胜赏(去上)曾孤倚。冰盘同燕喜(去上)。更可(去上)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去上)。
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去上),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丸荐酒(去上),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但梦想(去上)、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去上)。
犯调由周邦彦创造
张炎《解连环·孤雁》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去上)、却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去上),残毡拥雪,故人心眼。 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去上)。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去上)。
词的总论
词以空灵为主,而不入以粗豪;以婉约为宗,而不流于柔曼。音旨绵邈音节和谐,乐府之正规也。不善学之则循其声调,袭其皮毛。笔不能转,则意浅,浅则薄;句不能炼,则意卑,卑则靡。
词要放得开,最忌步步相逢;又要收得回,最忌行行愈远。必如天上人间,去来无迹方妙。
词之章法,不外相摩相荡。如奇正实空、抑扬开合、工易宽紧之类是也。词之承接转换,大抵不外舒徐斗健,交相为用。所贵融会章法,按脉理节拍而出之。
空中荡漾,是词家妙诀。
上意本可接入下意,却偏不入而于其间传神写照,乃愈使下意栩栩欲动。
词要不亢不卑,不触不悖,蓦然而来,悠然而逝。立意贵新,设色贵雅,构局贵变。言情贵含蓄,如骄马弄衔而欲行,灿女窥帘而未出,则得之矣。
白描之句,不可近俗(庸俗、低俗、媚俗);
修饰之句,不可太文;
生香活色,当在即离之间;
近雅而不远俗(通俗)。
僻词作者少,宜浑脱乃近自然;常调作者多,宜生新斯能振动。
小令要言短意长,忌尖弱;
中调要骨肉停匀,忌平板;
常调要操纵自如,忌粗率。
能与豪爽中著一二精致语,绵婉中著一二激励语,尤见错综之妙。
词有叠字,三字者易,两字者难,要安顿生动;
词有对句,四字者易,七字者难,要流转圆惬。
词中吞吐之妙,全在换头、煞尾。换头多偷声,须和缓,和缓则句长节短,可容攒簇;煞尾多减字,须劲峭,劲峭则字过音留,可供摇曳。
词的押韵,不必尽有出处,但不可杜撰。
若只用出处押韵却恐窒塞。
词之句语,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七八字者,若一味堆垛实字,势必读之不通,合用虚字呼唤。单字如正、但、甚、任之类,两字如莫是、却又、那堪之类,三字如莫不是、最无端、又早是之类,此等虚字皆要用得其当。若一词之中,两三次用之,便觉不好,谓之空头字,不若径用一静字,顶上道下来,句法又健,然也不可多用。
凡人无论作何文字,欲其姿态生动、转折达意,皆不可不知虚字之用法,而填词为尤要也。长调之词,曼声大幅,苟无虚字以衬逗之,读且不能成文,安能望通体之灵活乎?惟用于小令中,则宜加以审慎。衬逗之字,有一字、二字、三字等类。
一字类的虚字:
正、但、待、甚、任、只、漫、奈、纵、便、又况、恰、乍、早、更、莫、似、念、记、问、想、算、料、怕、看、尽、应;
二字类的虚字:
试问、莫问、莫是、好是、可是、正是、更是、又是、不是、却是、却喜、可怜、无奈、但见、何曾、恰忆、恰似、却又、绝似、又还、忘却、纵把、拼把、哪知、那番、那堪、堪羡、何处、何奈、谁料、漫道、怎禁、遥想、记曾、闻到、况值、无端、独有、回念、乍向、只今、不须、多少;
三字类的虚字:
莫不是、都应是、又早是、又况是、又何妨、又匆匆、最无端、最难禁、更何堪、更不堪、更那堪、那更知、谁知道、君知否、君不见、君不闻、再休提等等。
填词必先选料,大约用古人之事,则取其新僻,而去其陈因;用古人之语,则取其清隽,而去其平;用古人之字,则取其鲜丽,而去其浅俗。
用典有两种,一种是用事典,一种是用语典。用事典就是用古人的事迹;用语典就是用有出处的语言文字。
填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立于二者之中,致空疏者填词,无意肖曲而不觉仿佛乎曲。有学问人填词,尽力避诗而究竟不离于诗。一则迫于舍此实无,一则苦于习久难变。欲去此二弊,当于浅深高下之间悉心研究也。
选择词调
词之题意,不外言情、写景、纪事、咏物四种。题意与音调相辅以成,故作者拈得题目最宜选择调名,选调得当则其音节之抑扬高下,可处处助发其意趣。
词之唐宋遗谱,在元明之后,几乎全部失传。敦煌发现的唐写本琵琶谱中还保存了若干曲调,而且标明急曲子的有《胡相问》一曲,标明慢曲子的有《西江月》、《心事子》二曲,标明慢曲子和急曲子交替使用的有《倾杯乐》、《伊州》二曲。大抵《倾杯乐》和《伊州》是属于成套的大曲,所以一段慢调,一段急调,更替者演奏,借以表达疾徐变化的不同情感。
一般词调内,遇到连用长短相同的句子作对偶形式的,有相当地位的字调,如果是平仄相反,就会显示和婉的声容,相同就构成拗怒,就容易阴阳不调和而演为激越的情调。这关键有显示在句子中间的,也有显示在句末一字的。单就《破阵子》和《满江红》两个曲调,可以窥探出这里面的一些消息。
至于苏辛派词人所常使用的《水龙吟》、《念奴娇》、《贺新郎》、《桂枝香》等曲调,所构成拗怒音节,适宜于表现豪放一类的思想感情,它的关键在于几乎每句都用仄声收脚,而且除《水龙吟》例用上去声韵,声情较为郁勃外,余如《满江红》、《念奴娇》、《贺新郎》、《桂枝香》等,如果用来抒写激壮情感,就必须选用短促的入声韵,才能情与声会,取得“读之使人慷慨”的效果。
短调小令,那些声韵安排大致接近近体律、绝诗而例用平韵的,有如《忆江南》、《浣溪沙》、《鹧鸪天》、《临江仙》、《浪淘沙》之类音节都是相当谐婉的,可以用来表达各种忧乐不同的思想感情,差别只爱韵部的适当选用。
适宜表达轻柔婉转、往复缠绵情绪的长调的,有如《满庭芳》。
短调小令类似上面这种适宜抒写幽咽情调的,有《蝶恋花》、《青玉案》等,也都得选用上去声韵部,列入欧阳修的《蝶恋花》。
各个词调都有它特定的声情——音乐所表达的感情,初学填词者要懂得如何选择它,如何掌握它。如《满江红》、《水调歌头》一类词调,声情都是激越雄壮的,一般不用它写婉约柔情;《小重山》、《一剪梅》等是细腻清扬的,一般不宜写豪放感情,词调声情必须和作品所要表达的感情相配合,这首作品才能够达到它的音乐效果,才能达到超于五、七言诗的效果。
自从词和音乐逐渐脱离之后,一般词人不复为应歌而填词,以为抒情达意,词同于诗,可以不顾它的音乐性,因之并忽略词调的声情。这种情形早在宋代就已经产生,如《千秋岁》这个调子,欧阳修、秦观、李之仪诸人的作品都带有凄凉幽怨的声情(秦观填这个调,甚至有“落红万点愁如海”的名句)。
宋代的周紫芝、黄公度等人因调名《千秋岁》却用它来填祝寿之词,那就大大不合它的声情了。《寿楼春》调声情凄怨,有人拿它来填作寿词也是不对的。这都是只取调名而不顾调的声情的错误。所谓“填词”必须“词调”,原是选调的声情而不是选调的名字。
在词和音乐还不曾脱离的时候,有些轮词的书籍,记载过某些词调的声情,最著名的是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它对《雨霖铃》、《何满子》、《念奴娇》等调,都有详细的著录,这是介绍词调声情最宝贵的材料,可惜这类材料保存下来的不多。
1、从声韵方面探索,就包括字声平拗和韵脚疏密等等。
2、从形式结构方面探索,包括分片的比勘和章句的安排等等;
3、排比前人许多同调的作品(《御选历代诗余》),看他们用这个调子写那种感情的最多,怎样写得最好。
这样琢磨推敲,也许会对运用某些词调声情的规律十得七八。
如:
1、满江红、念奴娇、水调歌头
宜为慷慨激昂之词;小令浪淘沙,音调尤为激越,用之怀古抚今最为适当;
2、浣溪沙、蝶恋花
音节和婉,作者最多,宜写情,也宜写景;
3、临江仙、凄清道上
最宜用于写情,对句两两作结,句法更见挺拔;
4、洞仙歌
婉转缠绵,可以写情,可以纪事,一叠不足,作若干叠者更妙;
5、祝英台近
顿挫得神,用以记事,亦甚佳妙;
6、七天了
音调高隽,宜用于写秋景之词,姜夔用以咏物;
7、金缕曲
宜用以写抑郁之情。此调变体甚多,别名《贺新郎》。可赋本意,用以贺婚;
8、沁园春
多四字对句,宜于咏物。别名《寿星明》可赋本意,用以祝寿;
9、高阳台
跌宕生姿,为写情佳调;
10、金菊对芙蓉
有回鸾舞凤之姿,用以纪事、咏物,皆流利可爱。
名家对写词的建议
周济云:学词先以用心为主,遇一事,见一物,即能沉思独往,晏然终日,出手自然不凡。次则将片段,此则讲离合。成片段而无离合,一览索然矣。此则讲色泽、音节。
唐圭璋云:作词非用心不可,用心则精,不用心则粗,精则虽少无妨,粗则虽多无益。欲作一词,首须用心选调、选韵。其次布局,铸词,无一不须用心。
若须依四声之调,必字字尽依四声,决不可畏守律之严,辄自放于律外,或托前人未尽善之作以自解。若有字复、意复之处,更须用心琢磨,决不可苟简从事,为识者所讥。吾人若存苟完、苟美之念,而惮于用心结撰,则罅漏更不待言。其实凡为诗文,皆须用心,不独作词。特词法细密,词律严谨,词旨婉曲,更非处处用心,不能佳胜也。
(改词)作词时须用心,词作成后,尤须痛改。往往一词初成,尚觉当意,待越数日观之,即觉平淡,若越数月或数年观之,更觉浅薄。故有人常焚毁少作之稿,即以此故。宋张炎《词源》亦尝论改词之要。其言曰:“词既成,试思前后之意不相应,或有重叠句意,又恐字面粗疏,即为修改。改毕,净写一本,展之几案间,或贴之壁。少顷再观,必有未稳处,又须修改。至来日再观,恐又有未尽善者。如此改之又 改,方成无瑕之玉。”
而近日临桂况蕙风更论及改词之法,其所撰《词话》云:“改词之法,如一句之中,有两字未协,试改两字。仍不惬意,便须换意,通改全句,系连上下,常有改至四五句者,不可守住原来句意,愈改愈滞也。”又云:“改词须知挪移法,常有一两句语意未协,或嫌浅率。试将上下互易,便有韵致。或两意缩成一意,再添一意,更显厚。”此皆金针度人之语,作词者所当深体实践也。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