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之后大众电影的重心逐渐从制造并保持“故事”,部分地转向了制造并保持“兴趣与悬念”;从“讲什么”部分地转向了“怎么讲”,非线性叙事电影从早期的艺术实验领域向大众电影领域的转向与此息息相关。在那些旗开得胜的年轻电影人的再接再厉及鼓舞下,种种非线性的电影叙述方法在大众影像领域勃发生机、发扬光大,成为卖座的大众影像的重要部分和近二十年电影界的弄潮儿。在这个过程中,非线性叙事电影逐渐完成大众化演进,同时其也在大众化转向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审慎的妥协。
1990年之前的主流大众电影,往往追求透明流畅的线性叙事,而此后,《低俗小说》(1994)、《罗拉快跑》(1998)、《巴别塔》(2006)、《盗梦空间》(2010)等诸多叙事复杂、不透明的非线性叙事电影[1],却赢得了全球范围内观众的普遍欢迎,成为新的大众电影的重要形态。易言之,1990年之后大众电影的重心逐渐从制造并保持“故事”,部分地转向了制造并保持“兴趣与悬念”;从“讲什么”部分地转向了“怎么讲”。非线性叙事电影从早期的艺术实验领域向大众电影领域的转向与此息息相关,且有待阐明。
自电影诞生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电影人与观众多将故事片中脱离时间先后序列的镜头跳转视为一种耻辱,后来这种耻辱渐移到了“无动机的跳转”身上,今天的电影人和观众多会对此一笑。
早期的电影规范之所以要求实现电影的形式性时间(电影放映的时间)进程和内容性时间(被叙述的时间)进程相统一的线性叙事法则,皆因其有较固定的形态构想。这种构想中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是根深蒂固的“摹仿”观念和对电影本性的特别认识,既然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和“物质现实的还原”,那么,电影自然被要求展示与日常经验相似的先后序列中的“当下”,于是,电影成了时间进程中的一连串因果相连的行动。作为20世纪电影的主流,这个电影形态的实现,是以剔除偶然性和非线性为叙事前提的。
然而反驳这种形态构想的也不乏其人,从布努埃尔经阿伦·雷乃、费里尼再到罗伯特·阿尔特曼、昆汀·塔伦蒂诺、泰伦斯·马力克,对传统电影中“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式环环相接的因果序列形式提出质疑的力量不断发出时强时弱的声音。这些质疑的力量也逐渐将在主流电影中表现为同一的时间与事件进程,分裂为形式性时间进程和内容性时间进程。电影随之获得了将“非当下”的东西展示为“当下”的权利。同时,电影也摆脱了纯粹客观展示的目的,进入个人的主观世界。既然主观路径代替了客观世界展示,影片中的时间一致性与情节连续性就出现了问题。
《党同伐异》(1916)用碎块式的时间、《去年在马里昂巴德》(1961)、《八部半》(1963)式的电影用主观时间,《罗生门》(1950)式的电影用重复时间代替时间先后进程……这样,在一些非线性叙事电影中,过程和过去取得了与当下和结局同样重要、甚或更重要的地位。这些电影叙事的过程,即叙述本身(故事如何被讲述),成了电影的布局形式和主体构成。于是,就有了非线性叙事电影(NonlinearNarrative Film)。
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历史可远溯到1916年的《党同伐异》,此后,《一条安德鲁狗》(1929)、《公民凯恩》(1941)、《罗生门》、《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非线性叙事影片,都在突破线性叙事电影的模式化思维,在一种更复杂、自由、内在化的思维影像表达上,进行了居功厥伟的艺术实验。
但这些电影在深刻与模糊之间的巨大摇摆中潜藏着一个威胁。这些为当时的时代寻找电影形式的电影,主要是作为小众电影而存在的,没能进入主流和大众的视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因种种原因,这种艺术探索式的非线性叙事电影整体日步暮途。若是不想步入死路,就得走另一条路,它确实也走了另一条路(部分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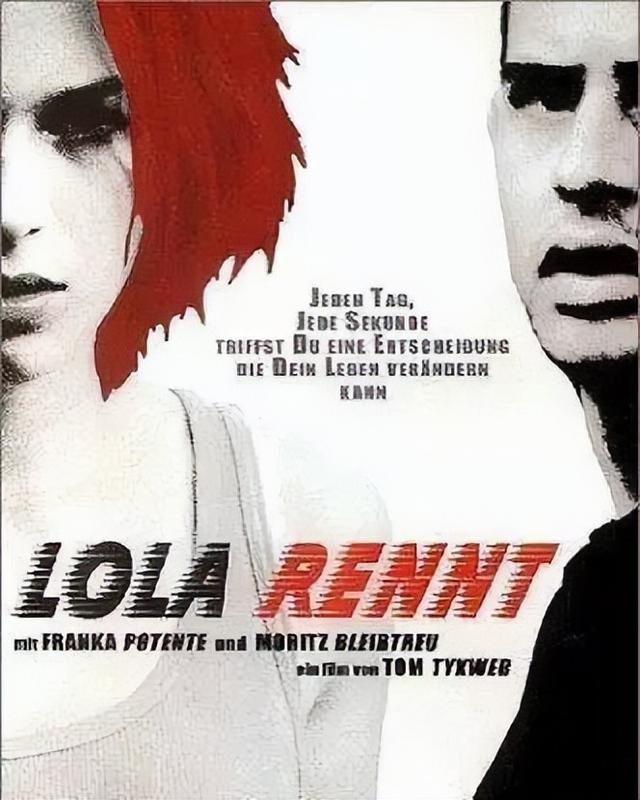
《罗拉快跑》
图片来源:网络
到了90年代,一大批饱尝欧洲艺术电影乳汁的新一代电影制作者,站在了电影界的前沿阵地,在新时代新社会的鼓舞下,他们用《低俗小说》《罗拉快跑》等非线性叙事影片,在离星光闪耀的演员表非常远的地方,仅依靠独有匠心的叙事惊奇,就创造了一系列破纪录的票房成功与舆论欢呼,非线性叙事开始成功进入大众电影领域。
在那些旗开得胜的年轻电影人的再接再厉及鼓舞下,种种非线性的电影叙述方法在大众影像领域勃发生机、发扬光大,成为卖座的大众影像的重要部分和近二十年电影界的弄潮儿。
在这场全球性的电影浪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连续对电影的非线性叙事倾注心力与才华的电影人。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美国的昆汀·塔伦蒂诺、伍迪·艾伦、史蒂文·索德伯格、大卫·林奇、格斯·范·桑特,加拿大的阿托姆·伊戈扬、大卫·柯南伯格,墨西哥的冈萨雷斯·伊纳里多,巴西的费尔南多·梅里尔斯,法籍智利人拉乌·鲁兹,英国的盖·里奇、彼得·休伊特、迈克·菲吉斯、克里斯托弗·诺兰,法国的克劳德·勒鲁什、让-皮埃尔·热内,德国的汤姆·提克威、迈克尔·哈内克,西班牙的阿尔莫多瓦,爱尔兰的麦克唐纳,日本的萨布、清水崇、内田贤治,韩国的朴赞郁、洪尚秀,中国香港的王家卫、韦家辉、彭浩翔,中国大陆的宁浩、娄烨、陆川、李玉、张杨、程耳等。
经这些电影人之手,非线性叙事手法在电影界广为传播,这种叙事惊奇甚至为一些枯朽多年抑或声名扫地的电影类型赋予了新的生命,同时越来越多在票房上极为成功的大众电影欢欣鼓舞地投入到了非线性叙事的怀抱,如《非常嫌疑犯》(1995)、《记忆碎片》(2000)、《时时刻刻》(2002)、《咒怨》(2002)、《杀死比尔》(2003)、《真爱至上》(2003)、《撞车》(2004)、《蝴蝶效应》(2004)、《特务风云》(2006)、《巴别塔》(2006)、《疯狂的石头》(2006)、《赎罪》(2007)、《刺杀据点》(2008)、《姐姐的守护者》(2009)、《社交网络》(2010)、《盗梦空间》(2010)、《源代码》(2011)等。1990年之后,非线性叙事电影的主流从艺术实验转向了大众电影。
与此相关的是,交互式的非线性叙事在电视、电子游戏、互联网方面也日益流行。
一
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大众化演进
托马斯·沙茨在其名著《好莱坞类型电影》中有如下论述不乏洞见:“在它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类型倾向于把电影媒介作为一种媒介来利用,如果类型是社会集体地对它自身的言说,那么,任何风格的华丽和形式的自觉都将只会妨碍信息的传达。”[2]把沙茨这一观点的使用范围放大到整个大众电影,大体来看,仍然没有什么不适用之处。用这个观点可以解释格里菲斯20世纪10年代最为名垂后世的两部电影遭遇不同命运[《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凭曲折透明的线性叙事大获票房成功,而采取晦涩的非线性叙事的《党同伐异》却票房大败]的大部分原因。这也是早期大众电影往往追求透明流畅的线性叙事的主要原因。
而伴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和观众观影经验的逐渐增长,电影单纯、透明、线性的早期叙事惯例就逐渐被改良、甚至被部分颠覆,这时电影的“透明性就让位于不透明性……从坦率的故事讲述到自觉的形式主义”[3]。这个转变时期,大约发生在“二战”之后。
从40年代后期开始,“早期有声时期的,主题单纯、形式上一目了然的直线叙事,正稳步地让位于更复杂的、盘根错节的、形式上自觉的电影”[4]。全球艺术电影的主潮也逐渐从讲“什么(What)”演化到了“怎样(How)”讲,叙述性(Narrativity),即讲故事的过程,成为艺术电影(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非线性叙事电影)的自觉追求,在20世纪中期的艺术电影中,某些内容逐渐凝固为形式,形式变得与内容互为表里。只需说说那些名垂后世的电影便足以为证:《罗生门》、《公民凯恩》用形式的不确定性表达主题的不确定性;《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用混沌的形式表现混沌的世界观;《八部半》中现实与幻想的一体两面。
在这些电影中,其形式常常就是所要表达的内容,而内容与形式也常常是一体两面。这种基于内容表达的形式主义,其代表人物有阿伦·雷乃、戈达尔、费里尼、黑泽明、奥逊·威尔斯。以阿伦·雷乃为例,此人视电影形式为内容,“不同于旧好莱坞片厂式的环环相扣的严密编织,即他不以单线性叙事,而是尽可能保留记忆的松散特征、多层面内容以及马赛克式的形式”[5]。阿伦·雷乃的电影中的“时间关系”[6]就既是其形式构造,亦是其内容表达。这样,这种电影既是真诚的艺术探索,又以其晦涩模糊远离大众电影的接受范畴。在20世纪50、60年代那个让雷乃声名鹊起的的电影名单中,除了《广岛之恋》(1959)有些大众影像潜力,其他那些晦涩的个人风格化作品,不能指望受到普通市民观众的普遍欢迎。
20世纪中期的非线性叙事电影是以艺术探索作为主要目的的。当这样的电影冒险向大众寻求证明时,往往铩羽而归,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例子莫过于《公民凯恩》的票房失败。
无法否认,虽然《公民凯恩》《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八部半》这样的电影中的艺术探索令人叫绝,但不大可能用“享受”来形容其观看体验。如果无法克服这类几成定势的沉闷风格,这种看上去略显老态龙钟的形式之衰落也将在所难免。同时,因为种种社会与文艺气象的变化,比如政治现代主义电影潮流至70年代中后期的偃旗息鼓[7],70年代之后,非线性叙事电影的艺术实验潮流逐渐退潮,只剩下一些支流的赓续。

《美国往事》
图片来源:网络
纵观20世纪70和80年代,有两个新趋势始终凸显于世界影坛:“对于一些电影工作者而言,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通过对类型电影的更新和对他们崇拜的导演表达敬意来延续好莱坞的传统。另一些导演则试图创造一种更具个人色彩的电影,他们力求把艺术电影的创作惯例带入大众化生产和流行类型之中。”[8]《美国往事》(1984)无疑代表着“力求把艺术电影的创作惯例带入大众化生产和流行类型之中”这一种方向。《美国往事》的遭遇也历史地成了非线性叙事电影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前奏。不少人出于对这部杰作的喜爱,将这部电影的票房失败完全归因于其上映时被删减的不幸遭遇。其实,原因似乎并非这么简单,即便看这部电影长达四个小时的完整版本,今天观影经验或耐心不够的观众也会云里雾里,兴味索然,更不用说1984年的观众了。
20世纪70、80年代,东亚的大岛渚、欧洲的特伦斯·戴维斯、美国的伍迪·艾伦等人,时常重返由布努艾尔、费里尼、阿伦·雷乃等前辈导演所开创的那种复杂的时空流转、影像断裂与间离、叙事非线性的电影风格中寻求资源。
这个时期非线性叙事电影的代表作品还有安德烈•塔科夫斯基的《飞向太空》(1972),布努埃尔的《自由的幻影》(1974),克劳德·勒鲁什的《如今我的爱》(1974)、《战火浮生录》(1981),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1977)、《我心深处》(1978)、《星尘往事》(1980)、《丹尼玫瑰》(1984),比尔·诺顿的《美国风情画续集》(1979),尼古拉斯·罗伊格的《坏时机》(1980),祖拉夫斯基的《着魔》(1981),艾伦·帕克的《迷墙》(1982)等。从整体来看,这些风格化的标新立异之作虽还未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但其中也逐渐增加了一些大众影像所要求的清晰性,以及悬疑、恐怖、犯罪、战争等类型元素。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往事》虽借助与类型电影题材的连接尝试迈向大众,但因其长镜头之多、时间提示之缺乏,以及更致命的,节奏风格之沉闷缓慢,大众并未回以热情的欢迎,而对这种沉闷的节奏风格的改造,恰是《低俗小说》《罗拉快跑》这样的非线性叙事电影成功大众化的最重要的起点。
《低俗小说》《罗拉快跑》降低了之前诸多艺术电影自命不凡的歧义与象征,将其模糊晦涩的影像风格逻辑化、明晰化,而其有意与动作、犯罪等类型电影题材和元素的连接,则为它们添加了引人入胜的活力,为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大众化开启了新的充满潜力的生长空间。
在20世纪90年代那个纯粹艺术电影和高概念电影[9]同时有所失落的时期,诸多先前主要作为艺术表达的非线性叙事形式在尝试进入大众化电影时,历史地摇摆在了艺术实验和大众影像之间,这些电影在题材和节奏上通常是大众的,表达姿态上仍然是先锋和反叛的。这就是《低俗小说》、《英国病人》(1996)、《罗拉快跑》、《木兰花》(1999)、《JSA共同警备区》(2000)乃至《记忆碎片》、《穆赫兰道》(2001)这样的电影既被看作艺术电影,又被看作大众电影的深层原因之一。而这些电影主动寻求与类型片元素的结合也标志着非线性叙事电影寻求大众化的自觉。
1990年之后,非线性叙事电影大规模地得到主流电影界的鼓励和认可。从侧重电影商业和大众价值的奥斯卡奖到侧重电影艺术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在任何一个重要的褒奖电影成就的凯旋门上,非线性叙事电影都明显占据重要位置,甚至执其牛耳[如《低俗小说》、《生命之树》(2011)获金棕榈大奖]。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非线性叙事电影在奥斯卡奖的榜单上只是零星闪现,而90年代至今的二十余年间,《短片集》(1993)、《非常嫌疑犯》、《英国病人》、《细细的红线》(1999)、《毒品网络》(2000)、《高斯福德庄园》(2001)、《穆赫兰道》、《时时刻刻》、《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2004)、《撞车》、《巴别塔》、《赎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2008)、《社交网络》、《盗梦空间》、《生命之树》……几乎每一年都有非线性叙事电影提名或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改编剧本这几个与叙事艺术相关的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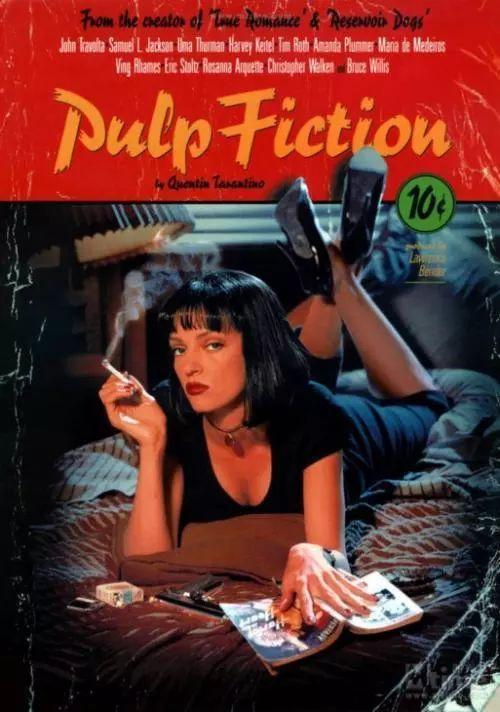
《低俗小说》
图片来源:网络
同时,非线性叙事电影也在与大众的观影博弈中逐渐改变为大部分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电影形态。标新立异的《低俗小说》仅赢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两年之后,《英国病人》便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这部电影褪去了前者的反叛姿态,并选取了更严肃的主题;而到《真爱至上》《巴别塔》《撞车》这一时期,这种电影形态已完全获得大众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独立制片电影在非线性叙事电影大众化中的作用,不少非线性叙事的高票房电影,如《非常嫌疑犯》、《记忆碎片》、《上帝之城》(2002)、《与莎莫的500天》(2009)都是独立制作电影。《记忆碎片》初映时仅有11家影院,两个半月后放映该片的影院已超过500家。最终这部900万美元投资的影片收获了4000万美元的票房。诺兰、冈萨雷斯等人常借助匠心独运的非线性叙事使其低成本制作脱颖而出,并将这种非线性叙事风格带入主流电影。独立电影的冲击和票房效果,鼓舞了一些主流电影投身更反常规的叙事,不过其冒险行为还是被尽量限制在保险的范围内。
在非线性叙事电影主流化的过程中,非线性叙事电影的观看协议也逐渐生成。《低俗小说》《杀死比尔》等电影中毫无动机的跳转能被逐渐普遍接受,有赖于观众更成熟的观影经验和更具包容性、更多样化的观看协议的逐渐养成,也归功于电影作者对“看”电影的方式的潜移默化——当无法从类型解读一部电影时,观众尝试从导演的惯用风格(或与其相似的早先的电影)中寻求解读方式。
若说《低俗小说》《罗拉快跑》在艺术与商业之间还有所游移,那么不久就规模性地出现了纯粹为票房而生的非线性叙事电影,譬如《一个字头的诞生》(1997)、《咒怨》、《真爱至上》、《11:14》(2003)、《刺杀据点》、《情人节》(2010)、……
伴随着非线性叙事电影的逐渐大众化,非线性叙事电影的诸多早期技法所带有的内容性表述也逐渐与形式发生了分离。众所周知,线性叙事与其背后的确定性的世界观是相联系的,正是因为观众相信世界是确定的,所以因果联系的、确定性的线性叙事才能大行其道;而非线性叙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反映了确定性的世界观的崩塌和怀疑的、不确定性的世界观的出现。
举例来说,黑泽明、奥逊·威尔斯之所以在《罗生门》、《公民凯恩》中使用了不确定性的多视角叙事,正是因为他们是怀疑主义者,他们对所谓的“真相”可追回持怀疑态度;换句话说,他们是用不确定性的形式表达着不确定性的主题。而在后来的《前进洛城》(1999)、《重回越战》(2001)、《基地疑云》(2003)、《何处知真相》(2005)、《遇人不熟》(2005)、《刺杀据点》、《听说桐岛要退部》(2012)等电影中,多视角叙事所带有的不确定性的主题被清除了。
以《遇人不熟》为例,该片大体上分四个部分,分别从失恋女子桑田真纪、公司职员宫武田、侦探神田勇介、黑社会老大浅井志信四个人的视角来将一桩“2000万”日元失窃事件拼完整。但在第一部分桑田真纪的视角中,观众只看到一个被男友抛弃的失恋女子,还不知道有失窃事件;在第二部分宫武田的视角中,观众只看到宫武田、神田勇介和桑田真纪在餐厅偶遇,宫武田喜欢上了桑田真纪并打算留其住宿;直到第三部分神田勇介的视角中,我们才知道发生了日元失窃案,这时影片已经放映了40多分钟;在第四部分浅井志信的视角中,我们才知道,原来失窃的巨款不过是黑社会老大装面子的假币。这种多视角叙事不表达不确定性的主题,而是一种悬疑策略。

《何处知真相》
图片来源:网络
甚至连《何处知真相》这样从片名便透露“真相不可知”的强烈气息的电影,其故事世界最终也确定化了,这部电影安排了一个类似《非常嫌疑犯》的突转式真相(之前几乎不被怀疑的鲁本才是当年的杀人凶手)。《罗生门》式的“真相不可知”变成了《何处知真相》式的“真相只在最后揭示”。因为大众电影对悬疑和明晰同时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而多视角叙事原本就有悬疑的巨大潜力,如此,问题就成了:如何尽可能利用多视角叙事的悬疑潜力而又让其获得可被理解的明晰化的表达?解决方式之一就是:用多视角叙事的悬疑方式讲寻找重重迷雾后面的完整真相——这个真相是确定的。这样,偏主观化的多视角重述的方法就必然经常会被整合进偏客观化的多视角拼合叙事的框架之中——而不是相反。
另一方面,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大众化也加速着其与类型电影元素、风格的有效连接,《低俗小说》《非常嫌疑犯》借助惊悚、悬疑的类型题材与风格为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大众化开启了一个路径,《杀死比尔》、《真爱至上》、《咒怨》、《蝙蝠侠诞生》(2005)在动作、爱情、恐怖、科幻等类型层级的顶端附近找到了安身之所,而《盗梦空间》则融动作、科幻、悬疑、冒险于一身,将非线性叙事带到了全球顶级票房的大众电影中。
正是基于全球各地区社会发展和电影市场发展的不同,非线性叙事电影在大众电影中的规模性兴起在全球也呈现出了地域性的差异。最先在大众电影中规模性出现复杂的非线性叙事的是社会发展程度高、观影经验深厚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中国香港;随后是韩国等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及观影经验较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而在中国大陆、印度、巴西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非线性叙事较晚在大众电影中成规模地出现。
以中国大陆为例。2000年以前,非线性叙事在电影中只是零星出现,并且几乎都采取这种叙事方式最原始的形态,比如套层结构叙事(如《小街》,1981)、板块并置式叙事(如《城南旧事》,1983)。
伴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开始出现李欣的《谈情说爱》(1995)和张杨的《爱情麻辣烫》(1997)这样的非线性叙事电影;而非线性叙事规模地出现始于2000年之后,其中的重要影片有《苏州河》(2000)、《周渔的火车》(2002)、《花眼》(2002)、《寻枪》(2002)、《茉莉花开》(2004)、《自娱自乐》(2004)、《疯狂的石头》、《太阳照常升起》(2007)、《疯狂的赛车》(2009)、《无人驾驶》(2010)、《刀见笑》(2011)、《万有引力》(2011)、《将爱情进行到底》(2011)、《边境风云》(2012)、《二次曝光》(2012)、《王的盛宴》(2012)、《北京爱情故事》(2014)、《催眠大师》(2014)等。
二
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大众化变化
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大众化转向中存在如下问题:这些“反常规”的非线性叙事电影是如何能被大众接受和喜爱的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是这些非线性叙事电影是如何能被大众接受的?换句话说,这些电影如何在其“创新”和观众“看得懂”之间找到平衡,以包容尽可能多的观众?本文认为,这有赖于一系列审慎的妥协:
其一是将影片中的故事世界确定化、客观化,并将其故事高度逻辑化。《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模糊的故事世界。而所谓的故事世界确定化,即影片在故事世界建构上排斥《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这样模糊混沌的可能,排斥不确定的、不可解释的、非逻辑的因素。无论是《低俗小说》《记忆碎片》还是《致命魔术》(2006)、《盗梦空间》,对看懂了的观众来说,这些电影故事所存身的故事世界是确定的,观众头脑中“整合”出的整个故事与电影预置的整个故事也是相一致的。
大众化的非线性叙事电影允许不可靠成分存在的前提多是这种不确定、不可靠是假装的,最终要被确定化,而将故事世界确定化的方式是为之寻找客观的理由——最终影片中那些离奇、歧义、混沌的讲述会被证实多是人物受到心理伤害后的幻想、虚构抑或谎言。
大众化的非线性叙事电影中常有双层逻辑。一层是与古典电影一样的故事本身的逻辑;另一层,是观者解读电影时的逻辑,这与电影建构的逻辑是反向同构的。在大众化的非线性叙事电影中,“看不懂”恰恰是为了“看得懂”——只要多看几遍。这种“断裂”叙事是能被拼合回去的、有潜在的观众的位置的。
艺术探索时期的非线性叙事电影倾向于表现人物的主观,而大众化的非线性叙事电影则将这种心理主观性加以客观化和逻辑化。在大部分的情形下,大众化的非线性叙事电影,利用了非线性叙事打破顺序的节奏潜能、设置悬念与延时揭示的特长,从而强化了其因果逻辑更严密、形式更复杂的框架。进而言之,其将电影自由思维的可能置换成了引人注目的叙事技法可能和商业的逻辑性的娱人修辞。正如本文前面对从《罗生门》到《遇人不熟》之间转变的分析所表现的那样。
诸多面向大众的非线性叙事电影在其确定性和清晰性方面多有审慎的考虑。理查·考夫曼之所以要为《美丽心灵的永恒时光》屡改其稿,唯因制片人担心剧情过于晦涩:“总是跟制片方艰难地讨论,在观众离去前,能让他们迷惑多久?似乎在此方面也有精确之公式,若不能将其掌握,则似乎将失去观众”[10]。

《蝴蝶效应》
图片来源:网络
对强化的因果逻辑隐喻式的例子出现在法国电影《蝴蝶振翅》(2000),美国电影《连锁反应》(2003)、《蝴蝶效应》系列中,这些非线性叙事电影甚至特意将因果的连锁性提升到了作为电影主题的地步。《连锁反应》的主题恰如其中文译名“连锁反应”,影片从一个小男孩踩死路上的一只虫子开始,一个好心人华莱士停下来去教育小孩不该杀死虫子,这导致华莱士被交警开了罚单,华莱士愤怒地撕碎了罚单并扔在下水道口,这又导致另一家店的下水道堵塞……凡此种种,可谓连锁反应;而《蝴蝶振翅》和《蝴蝶效应》明显是从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的“蝴蝶效应”理论——一个微小的变化也将引发重要的连锁变化——汲取了灵感并将其作为影片的主题。
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趣事,人的梦境、幻觉、想象、回忆,本来是最脱离逻辑性、确定性、客观性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八部半》这些电影正是以此来反抗线性叙事的逻辑性和确定性的,但在大众化的非线性叙事电影中,比如在《盗梦空间》中,连最不可能逻辑化的“梦”也被确定化、客观化、逻辑化了。
其二是影像呈现上的规律化与其他诸多补偿性措施,比如重复与改造先前的成功案例[如《罗生门》的追随者《前进洛城》、《刺杀据点》、《听说桐岛要退部》;《两杆大烟枪》(1998)的追随者《偷抢拐骗》(2000)、《中场休息》(2003)、《疯狂的石头》等],或建立与重复同一个故事模型(如《盗梦空间》中的建立梦境和复制下一层梦境),或让不同影像规律性交替(如《记忆碎片》中的影像规律性交替),或使用诸多标记提示等补偿技法(如《杀死比尔》中的标题提示字幕)。

《疯狂的石头》
图片来源:网络
而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最受大众欢迎的非线性叙事电影,几乎都选择了非线性叙事激进形式的保守版本。为了能在“叙事惊奇”和“看得懂”之间找到平衡地带,《将爱情进行到底》采用了几段相对完整的爱情小故事相连缀的方式;《寻枪》采取了“目标驱动”的简便策略;《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将其网状叙事限定在某一两个主要场所中;《二次曝光》则采用了广受追捧的《穆赫兰道》的简化版本。
这些广受欢迎的非线性叙事电影的票房成功,也显示出很多中国观众对惯用的简单透明的情节处理手法的厌倦,以及对创造性结构与叙事惊奇的普遍需求。当然,对普通观众来说,这种“叙事惊奇”要寻找到适可而止的平衡,不然则“过犹不及”。那些显得过于复杂、沉闷、晦涩的影片,如《太阳照常升起》《无人驾驶》《王的盛宴》,则规模性地在这场非线性叙事电影与观众接受的博弈中败走麦城。
不过,中国观众对复杂的非线性叙事电影的接受能力也在逐步提高,这种电影与普通观众之间的观看协议也在一步步建立之中,十多年前的观众只能接受《爱情麻辣烫》这样简单的大段落式非线性叙事形态,而到了近几年,《疯狂的石头》《二次曝光》《边境风云》《催眠大师》这样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叙事电影也逐渐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历史地看,中国当代大众电影已经逐渐摆脱“线性叙事”一统天下的格局。
正是大众化的非线性叙事电影在“叙事惊奇”与“看得懂”之间审慎的平衡,使得大众化的非线性叙事电影与布努埃尔、雷乃那些艰涩难懂的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影片区别开来,也与从《一个国家的诞生》到《阿凡达》(2009)这样情节透明的电影区分开来,并使其创新既是新奇的又是可被理解的。这种平衡的艺术也使得《低俗小说》《记忆碎片》《真爱至上》《杀死比尔》《盗梦空间》这样的电影既是创造性的,又是大众化的,因而同时成为被电影人和观众所竞相追逐的电影潮流风向标。
大体说来,上述原则仅能保证非线性叙事电影是可被“看懂”的。如何让观众“爱看”这种电影呢?这有赖于这些电影惯用的三种策略:内容上,采取去日常化策略,专注于刺激感官的影像制造;形式上,采取强化节奏的策略,以及让观众对电影进行互动式体验的策略(比如观看《罗拉快跑》时的通关游戏体验,观看《记忆碎片》时的拼图游戏体验,《盗梦空间》中的有限开放性结局),以此来吸引观众对这种电影“持续关注”。在此三种策略之中,前两者是大众电影的一般性策略,互动参与策略的介入则更多地与非线性叙事本身的特点有关。
余论
非线性叙事在大众电影中兴起的原因自然一言难尽,但时代经验的影响、观众口味的变化、电影技术的革新则是其主要原因。
大众化的叙事必与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紧密相关。正是城市生活和网络经验催发了网状叙事电影;游戏心态和电子游戏经验鼓舞了分岔路径叙事电影;时代的分裂感体验鼓励了多时空并置式叙事电影和重组式叙事电影;丰富的内心生活和主观体验为不可靠叙事提供了根基;网络经验和电脑等其他电子化经验中萌发了检索式电影和链接式电影的苗头。用丹纳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把特征印在艺术家身上,艺术家把特征印在作品上”[11]。
20世纪的主流大众电影钟爱清晰的线性叙事,而随着百年电影史的演进,诸多观众期待看到更复杂、更具创新性的大众电影,于是,《真爱至上》《巴别塔》《盗梦空间》《社交网络》这样叙事复杂的大众电影便应运而生。正像李奥·布劳迪所指出的那样:“电影问观众,‘你还相信这个吗?’影片受欢迎就是观众在回答:‘是的。’当观众说‘我们看到的形式太幼稚了,给我们看一些更复杂的东西’时,类型就会发生改变。”[12]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电影技术和媒介方面的变化对非线性叙事电影兴起的影响。其一,数字剪辑(非线性剪辑)开始流行(到1996年,80%的好莱坞影片均使用数字剪辑)。其二,家庭录像带、DVD、互联网视频开始盛行。较之电影荧幕,这些新媒介最具创造性的优势在于其可重复观看、定格观看,可以使电影采取更复杂、非线性的叙事和进行更多的细节修饰。
而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大众化转向也带来了近二十年大众电影形态的复杂化:其重心从“讲什么故事”部分转到了“怎样讲故事”。其中的重要命题是使对传统电影形态产生厌倦感的观众面对“熟悉的新奇”,将电影从侧重“故事”转向了侧重“兴趣和悬念”。同时,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大众化,也让犯罪、悬疑、惊悚等电影类型东山再起或者发扬光大。与上面所说的变化相关的其他微观些的变化还有,大众电影中占主导的“单一故事”和“单主人公”逐渐为“多故事”和“多主人公”腾出了部分空间。基于此,有西班牙学者甚至写出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多主角电影》[14]。
而就总体而言,大众化的非线性叙事电影同先前作为艺术实验的非线性叙事电影相比,发生了这么几个不太乐观的变化:场面调度的弱化和构图的简化、“静思”韵味的减弱、歧义和不确定性的消散、日常性和批判性的弱化、同质化趋势的增强。从《纳什维尔》(1975)到《疯狂的石头》,《盲打误撞》(1987)到《源代码》,《罗生门》到《刺杀据点》,前者与后者之间,盘亘的不仅是尘埃点染的历史,更兼电影形态及思维之差别。同是非线性叙事的爱情片,《安妮·霍尔》思考爱情的本质,而《真爱至上》已经丝毫不触及爱情本质的思考;《盲打误撞》中隐含对政治和现实的指涉,而到《源代码》中,这种形式成了火爆场面和叙事惊奇的由头。
当然,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大众化转型并不意味着20世纪90年代后非线性叙事电影的非大众实践就后继无人了。事实上,执着于这种电影艺术探索的导演仍不乏其人。曼彻夫斯基、迈克尔·哈内克、阿伦·雷乃、泰伦斯·马力克等人仍带着《暴雨将至》(1994)、《巴黎浮世绘》(2000)、《野草》(2009)、《生命之树》等作品继续行走于严肃艺术探索之路,并徘徊在主流的边缘。
但如果接着追问一个问题: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大众化转型完成了吗?答案仍有待历史的证明。依我的粗浅观察,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这一转型已经基本成型,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这一转型仍处在如火如荼的发展时期。
要对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大众化转型这一新千年世界范围内的电影潮流作出公允的评价,仍需很长的时间。就今天而言,当代大众电影的形态新变和非线性叙事电影的未来走向中还有诸多悬而未决的可能;而对非线性叙事电影及其大众化形态诸多方面的研究,也仅是一项刚刚开头的工作。
注释
[1]本文所说的“非线性叙事电影”,是指就一部电影的整体布局、整体结构而言,其主要结构方式是以非线性方式呈现的,这种电影中规模性地出现了非先后顺序的时空,以网状叙事、分岔路径叙事、套层结构叙事、环形叙事、不可靠叙事、多时空并置式叙事、乱序叙事、反向叙事、检索式叙事、链接式叙事、反线性叙事等形态取代了服从时间先后顺序的“线条”,并以这种有意制造的非线性形式作为影片的主体结构风格、叙事形式甚至思维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