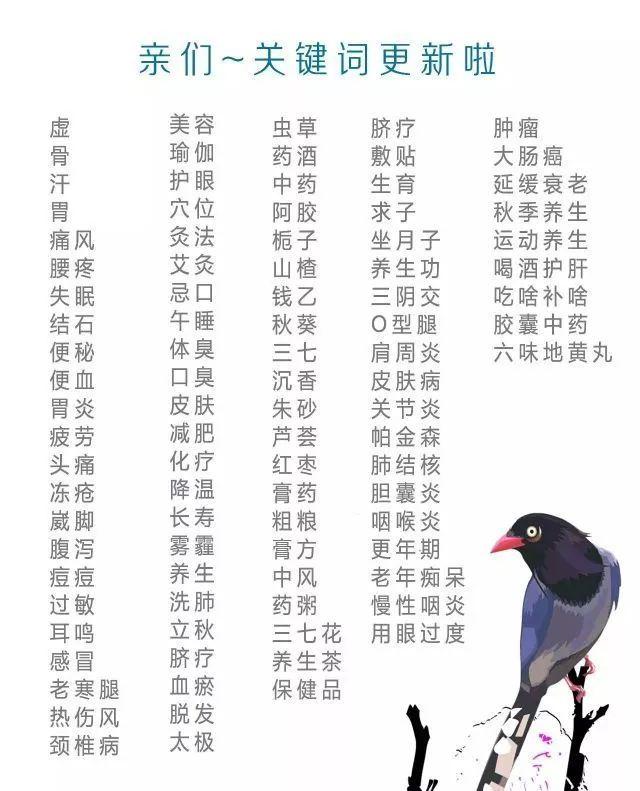□杨新元 中国作协会员、浙江日报高级记者
人在一生中,会碰到无数的人,会走过无数的地方。碰到的人,除了极少部分走进自己的生活之外,绝大部分是一面之缘,遇见了,认识了,时间一长就忘记了。而走过的地方呢,除了极少数地方以其不凡的特色让你记住了,极大部分也是一面之缘,走过了,看过了,忘记了。苏州的沧浪亭,可能就是那种有不凡特色的地方。它让我走过了,看过了,记住了。

视觉中国 供图
一
“去之前还以为是一个亭子,去了才知道是一个园子。”这是许多人看了沧浪亭以后的感叹。
当然,苏州本地人或者对沧浪亭的历史比较了解的,就不会闹这种误会。确实,以一个亭子来命名一处园林,这种事情在全国也比较少见,容易让人产生误会。
我最早知道沧浪亭,还是读明代文学家归有光的《沧浪亭记》。文章一开头:“浮图文瑛居大云庵,环水,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说文瑛和尚居住在大云庵,那里四面环水,从前是苏子美创建沧浪亭的地方。
可以说,沧浪亭是苏州园林中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得名于北宋文人苏舜钦,现在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据记载,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集贤院校理苏舜钦在汴京遭贬谪,翌年流寓吴中。见孙氏弃地约六十寻,以四万钱买入。在北面靠水筑亭,命名“沧浪亭”。后苏舜钦常驾舟游玩,自号沧浪翁,作《沧浪亭记》。他常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作诗唱酬往还,从此沧浪亭之名传开。
去年1月,我去苏州旅游,安排的主要观景点是拙政园、网师园、留园、狮子林等。
这几个地方都走过后,再去哪里看看?
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孟子·离娄》中的《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我想,我应该去看看沧浪亭,去看看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曾经流连忘返的地方。
二
沧浪亭确实不同凡响。
走进园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浅蓝色的石碑,周身用花岗石镶边。
这是2000年由国家文物局、建设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全国委员联合颁发的,告诉人们,沧浪亭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的杰作,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沧浪亭园占地约1.1公顷,整个园林的布局开畅自然,“草树郁然,崇阜广水”。入园即是一座横亘东西的土丘。土石相间,古木森郁,极富山林野趣,是典型的“城市山林”。
我缓缓走上山坡,只见闻名遐迩的沧浪亭正默默地屹立在山岗上,石柱飞檐,古朴典雅。由晚清学者俞樾写的“沧浪亭”三个字遒劲有力。楹联学开山之祖梁章钜重修沧浪亭时,集苏舜钦、欧阳修诗句而成石柱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别有韵味。
我知道,上联“清风明月本无价”,出自欧阳修所作的七言古体诗《沧浪亭》:“初寻一径入蒙密,豁目异境无穷边。风高月白最宜夜,一片莹净铺琼田。清光不辨水与月,但见空碧涵漪涟。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意思是,清风明月本没有价目,可惜卖给你才四万铜钱。
下联“近水远山皆有情”,是从苏舜钦《过苏州》一诗中觅得。“东出盘门刮眼明,萧萧疏雨更阴晴。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意思是,近处的水远处的山,一处处隐含着深情。两句出自不同诗人的诗句联在一起,竟然天衣无缝,十分贴切。
三
山上静悄悄。古木森森,青翠欲滴。走到亭心放眼四望,全园景色尽收眼底。
在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园林位于湖中央,湖的内侧由山石、复廊和亭榭绕围一周。山水之间以曲折的复廊相连。
山石四周环列建筑物。建园者通过复廊上的漏窗渗透作用,沟通了园内、外的山与水,形成了苏州古典园林独一无二的开放性格局。因此,沧浪亭的这条复廊,不仅被视为造景的一大特色,也被人们誉为苏州古典园林的三大名廊之一。
沧浪亭中最显气派的是瑶华境界和与之北面相对的明道堂。两边的廊屋连贯相通。院中,几株柏树和玉兰树苍翠欲滴,生机勃勃,更突显了庭院的宽广气派。
我走入瑶华境界,迎面屏风上镶刻着苏子美的《沧浪亭记》。黄色的屏风绿色的字,既显眼又不招摇:“予以罪废,无所归。扁舟吴中,始僦舍以处。”文章一开头,苏舜钦就点明自己因获罪而被贬为庶人,没有可去的地方,乘船在吴地旅行,起初租房子住。
不管苏舜钦是否感到冤屈,反正我是为他感到不平的。充其量,他不过是朝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已。苏舜钦获罪的原由,在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清平乐》中有完整呈现。这个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颜值担当,因为用卖废纸的钱宴客,被贬为庶人。
因为仕途失意,苏舜钦一直郁郁寡欢。对于一个30多岁就当过县令、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等官职的年轻人,他对走仕途报国是抱有远大理想的。但是,因为他支持范仲淹的改革,遭到反对派的诬陷,以致流落民间。结果,沧浪亭建好不过二年多,沧浪翁就撒手人寰。
四
归有光的《沧浪亭记》,全文不到三百字,却记述了沧浪亭的历史变迁,并通过古今对比,抒发了自己对世事变化的感慨。
而苏舜钦写《沧浪亭记》,是在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是他遭贬谪流寓吴中后。
对比两篇《沧浪亭记》,可以明显看出,归文比较大气。
归有光的文章中,作者在抒发自己因园亭变化而产生的感慨时,强调钱氏“宫馆苑圃,极一时之盛”,而今渐然而尽,未给后人留下任何印象。而苏舜钦建造一个亭子,却让后人“钦重如此”。于是,他得出结论:“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他强调,一个文人的人格魅力,远胜过帝王将相的权力和身世显赫,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确实,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有多少帝王将相,显赫一时。死后黄土一抔,有几个人会记得他们?
而苏舜钦写《沧浪亭记》,仍局限于小我的喜怒哀乐,沉浸在因罪废之,无所归的哀怨之中。虽然他想借造沧浪亭而转移哀思,但也是以酒浇愁愁更愁。他人在江湖,心系庙堂,空怀报国之心,每天强颜欢笑,终日郁郁寡欢。结果,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我想,苏舜钦被贬,朝堂少了一个颇有文才的官类,而民间却多了一座流芳千古的沧浪亭。这件事,对苏舜钦本人来说,是一件伤心欲绝的苦事,而对园林文化而言,却是一件延续文脉的好事、幸事。
这是我观沧浪亭后的感想,诸君以为然否?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