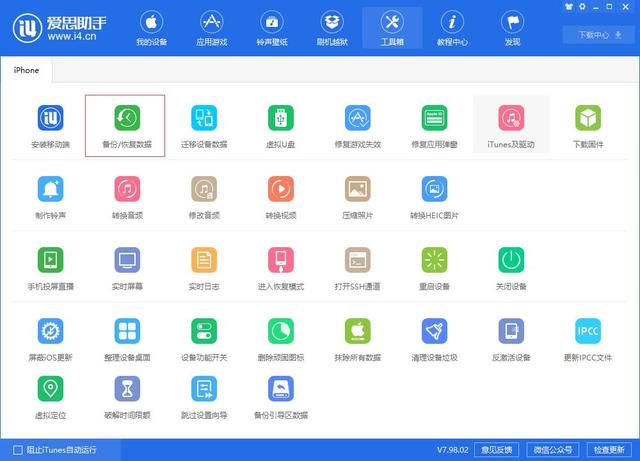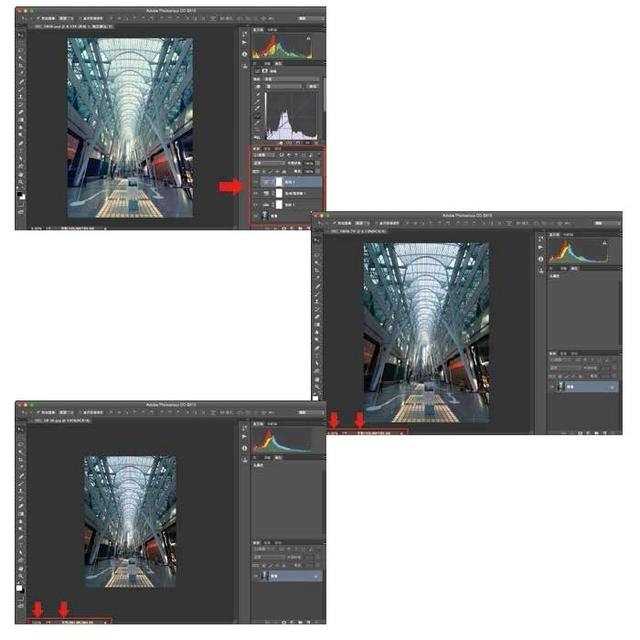父亲的歌声
祖母活的时候,说父亲唱歌跟哭哩一样。她所说的哭,或许指的是父亲歌声里与众不同的颤音。也或许,祖母最早从父亲的歌声里,闻到了里面所预伏着的巨大危机和潜在的不幸。
母亲活的时候,听她不止一次地说过,父亲一个姓马的学生,在考上大学离开一中之后,在她上学的那个城市,一天傍晚在马路上正走时,忽然听到从悬挂在电线杆上的喇叭里传出了极像父亲嗓音的歌声。那时,她便驻足聆听,并开始自己无声地啜泣。后来,她把她的感受在给父亲的信里予以表达。
还有父亲现在的学生们,在与我们相处时,他们不无炫耀地向人们描述着他们杨老师的歌声,他们说:“俺杨老师唱的《祝酒歌》,一点都不比广播里的差。”那是父亲间隔20年,重新走上讲台后所唱出的歌声。那时父亲已经50多岁了。
父亲武汉音乐学院毕业后,当上了武汉市工人文工团的导演。那时他才20来岁,可谓春风得意,前途无量。是祖父把他叫回来的。因为年迈的祖父和祖母身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男孩都相继夭折了,只剩下父亲一个孩子。父亲不肯回来,但是祖父用苍老的眼泪,终于打动了父亲。让他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舍弃了他正全身心投入的事业,来到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开始了他人生的漫漫坎坷旅程。
父亲曾动情地向我描述过他和大家告别时的场面。他说,文工团的全体同志站在楼梯两边,从楼上排到楼下,一个挨一个地和他握手。他们说,老杨你可一定回来啊,我们都在等着你。父亲说,你看我的行李都没带,还能不回来吗?在这之前,父亲决定瞒天过海,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和书籍都丢在那里,只身离去,以表示自己回来的决心。然而,当他回到老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以致后来,他几次向文工团要一张自己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证明,团里都没有回音。父亲补充说,假如他说了真话,他就回不来了,就不能照顾祖父祖母了。正因为父亲的这一举措,不但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方向,同时也使他失去了年老时享受离休待遇的机会。
父亲来到老家,在那个盛行宣传的年代里,他组织腰鼓队、合唱团、管乐队,没日没夜排练、演出。在大街小巷,在田间地头,在工厂,在学校,父亲尽情地展示着他的青春和才华。他的歌声传遍了县里的角角落落,成为人们的享受,也成为人们的美谈。
父亲可谓红极一时。进入人们视线的,不仅是他那动人的歌声,还有他非同凡响的气质和装束。在父亲的一张照片里,我看到他的衣着全是白色的。白色的衣裤,白色的鞋袜,连腕上的手表带,也是白色的。他留着三七开的分头,微笑着,显得英俊潇洒,气度非凡。母亲说过,我们弟兄们都没有当年父亲的气质。一个人的气质,一方面来自天赋,另一方面是来自后天的养成。我想,父亲的气质除了先天的成分,也许就是在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展示和人们的追捧中逐渐养成的吧。
父亲跟我说过,他在文艺学院学习时,他的老师是这样形容生活与音乐之间的关系的:“生活里要是没有音乐,就好比春天没有花朵。”是啊!父亲那么爱唱歌,他走到哪里就把歌声带到哪里。他要让自己的歌声,像美丽的花儿一样盛开在生活的每个角落,让这个世界永远都是明媚的春天。父亲非常喜爱唱的一首歌,是前苏联歌曲《在遥远的地方》。在难得的悠闲时候,或是生活里出现了与歌曲里相似的意境时候,他就很自然地哼唱起来:“在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荡漾。微风轻轻吹来,掀起一层麦浪……”
记得有一次,父亲带我去一个在地里看守庄稼的朋友那里。我那时七八岁吧,我扯着父亲的手,走出村庄,走过村边的河流,踏上田野上的小道。天上的月亮在云缝里出没,大地一片洁白,轻风徐徐吹来,路上树影婆娑。这时,父亲哼唱起了那首歌曲,唱得深情而专注。在那一刻,父亲或许想到了曾经培育自己的母校,想到了尊敬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也或许还有别的什么美好的往事出现在他的心头。父亲唱得如痴如醉,也把我带到了那诗样的意境里——广袤的大森林里,蜿蜒着一条弯弯的河流,一个战士手持着钢枪,踏着松软的落叶,一边警惕地守望着边境,一边哼唱着这首抒情的歌曲,沉浸在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中。
在父亲被打为右派的岁月里,很少听到他的歌声。的确,生活那样艰难,哪还有心情唱歌呢。但偶尔也听父亲唱过,那是在地里干活,半晌休息的时候。那时,乡亲们坐在地头,他们不无调侃地说:“让吉祥来一段吧。”父亲不愿唱,可耐不住乡亲们的磨缠,最终还是清了清嗓子唱了一段。那时父亲唱得最多的是黄梅戏《天仙配》里的选段:“家住丹阳姓董名永,父母双亡孤单一人。只因爹死无棺木,卖身为奴葬父亲。满腹忧愁叹不尽,三年长工受苦情。有劳大姐让我走,你看红日快西沉……”
“扭个秧歌呗。”有人提要求说。父亲吸了袋烟,磕净了烟灰,犹豫了犹豫,还是起来,拍打拍打屁股上的土,找了根绳子勒到腰上,又问房东胡大娘借了条毛巾系到头上,然后唱起了那首秧歌剧《兄妹开荒》里的一段:“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睡在热炕上作懒虫。扛起镢头上呀么上山冈,山呀么山冈上,好呀么好风光。我站得高来看得远来么,咱们的边区到如今成了一个好呀地方……”父亲边唱,边双手捏着两根绳头,向两边奋力甩着,随着节奏摆着头,扭起了大秧歌。他的带点夸张的表演,引起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受那些热爱文艺的年轻人邀请,为村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指导节目。他指挥各种合唱,导演移植革命样板戏。排好了戏,还和他们一起到水库工地,到外村演出。每逢演出,父亲就为演员化妆。他一个一个地化,一丝不苟,有时一直干到深更半夜才回家。
在老家时,我曾跟父亲学过一段声乐。父亲教我呼吸运气,教我寻找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的共鸣,教我如何唱好高潮,教我怎样咬字吐字,怎样用具有表现力、感染力的颤音去征服听众。父亲说发声的时候,要面带微笑,感情真挚充沛,同时要表现出应有的气度来。
父亲被平反之后,又回到原来工作的县一中,担任音乐老师。那时候,学校上音乐课,用的是脚踏风琴。那个风琴,就放在父亲的连住带办公的屋子里。到了上课的时候,学生们把风琴抬到教室。那时,“四人帮”被粉碎了,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生,他们被压抑了多年的才情得以展示,一首《祝酒歌》响彻了大江南北。父亲给他的学生们教了这首歌:“美酒啊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来来来……十月里响春雷,亿万人民举金杯,舒心的酒啊实在美,千杯万盏也不醉……”父亲还爱唱的一首歌是电影《共和国之恋》的主题歌《苦恋》:“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纵然是凄风苦雨,我也不会离你而去。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那时我已上师范学校,放假回家时,经常听到父亲在他的屋子里唱歌,自己弹着风琴伴奏。啊!父亲的歌声是那样饱满而辉煌,他对歌曲的理解,他的共鸣,他对高潮的处理,他的颤音,都是那么到位。或许是因为那些歌曲与他的心情相契合,他唱得激情四射,神采飞扬。那才是我的父亲,那个才华横溢,富于激情,富于创造的父亲。
父亲一生最崇拜的人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他唱得最多也是最钟爱的歌是《黄河大合唱》里的《黄水谣》《黄河颂》等。我上小学时,因受父母影响,具备了一些音乐知识,担任班里的音乐委员。在参加学校的歌咏比赛时,父亲为我们排练的其中一个节目是二部轮唱《保卫黄河》。父亲教我指挥,教我排合唱队形。由于准备充分,加上父亲的指导,我们班取得了优异成绩。
回顾父亲的一生,他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他的歌也和政治息息相关。他有意或无意地,终其一生都在为祖国为时代为人民而歌。他把自己一生的才情和忠诚都贡献给了祖国,贡献给了人民,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父亲晚年喜爱唱的一首歌是《最美不过夕阳红》:“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
父亲一生虽然坎坷,但在晚年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地歌唱。父亲在他81岁时,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他带着自己优美的歌声,到了等待已久的我的母亲身边。
我爱父亲,更爱他的歌声。
部分内容和图片转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
原创文章版权属《焦作日报》(JZRBWX)官方微信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
版权所有:焦作日报社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4112018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