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期《绘本应该怎样读?从1939年凯迪克金奖绘本Mei Li说起》从中文译本与英文原文的比较出发,说明了读绘本需要从整体上把握作品意图,才能领会到文本中的丰富意蕴。今天的第2期,我们将翻开1941年第4届凯迪克金奖绘本They Were Strong and Good(《他们坚强而善良》)。
这本图画书由罗伯特·劳森(Robert Lawson,1892-1957)创作,讲述了他的六位长辈如何从不同的地方走到一起组成了庞大的家庭,从中折射了美国的发展历史。六位长辈分别是他的母亲的父亲,母亲的母亲,母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母亲和他的父亲。每一个长辈是一个独立的“章节”。

在《他们坚强而善良》中,劳森画的六位长辈。
目前也能找到两个中文译本,书名略有不同,分别是2015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他们坚强而善良》和2019年由童书品牌森林鱼出版的《他们坚强又善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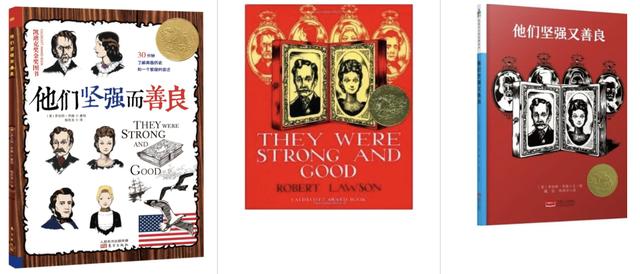
左为东方出版社的中文译本。中间为英文原版。右为森林鱼的中文译本。
罗伯特·劳森创作的绘本不仅获得过凯迪克金奖,他的儿童短篇小说《兔子山》还获得过1945年的纽伯瑞奖,使他成为同时拥有这两个大奖作品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家。然而获得大奖并不能保证作品就会备受赞誉,相反,80年后重读《他们坚强而善良》这本带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绘本时,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在阅读文学时我们该如何理解“真实”的概念?
撰文丨王帅乃
当我读完1941年的这部金奖作品《他们坚强而善良》时,就知道必须要聊一聊这个文学阅读和批评中的著名难题了(我原以为不会在第二篇文章中就与这个令人头痛的命题狭路相逢):“文学和‘真实’究竟是什么关系?”
由于这个文本直接涉及到“政治正确”,讨论可能会变得有些艰难。实事求是地说,当前整体的文学阅读氛围并不好,不论是秉持“政治正确在当下应矫枉过正”的一方,抑或是厌恶“政治正确无限扩大”的一方,都变得非常容易“愤怒”。当义愤冲击文学阅读,我们就很难再发现那些作品内部与整体异质的声音、复杂的交鸣。
回想我们儿时,第一次读到一部好小说、一首好诗的感觉是怎样的呢?或许我们到了垂垂老矣、炉火将烬时才能再次体会到,那些被称为“文学”的东西带给我们最大的教益是叫人“生与希望”而不叫人“死和绝望”,教人善良而不教人傲慢,教人智慧通透而不教人片面武断,教人觉得世界美好人间值得来这一遭,也值得你用心把它变得更美好。
以后我们还会不断地遇到与“政治正确”有涉的文本,不仅是凯奖,甚至也不仅是文学文本,借此机会讨论如何阅读这样的作品应当能提供些参考意义。至少在这个专栏内,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都尝试不那么着急,并且,尝试把这根看起来难啃的骨头重新纳入到文学的框架中,用文学的语言、逻辑和智慧给予它们公正的评价——如果你还相信小时候遇见过的神奇而美妙的“文学”。
关于“真实历史”的经典辩护
《他们坚强而善良》是罗伯特·劳森为自己的(外)祖父母、父母和自己三代人建立起的“家族故事树”,从小家庭的建立和繁衍折射出美国的建国与发展百年史。

Goodreads上这本书的评分为3.5分。
开门见山地说,这部书被许多读者怀疑和谴责为“种族歧视的遗留物”。Goodreads等提供大众书评的网站上读者们都承认白人对印第安民族的殖民历史,将之视为丑陋的过去、应该忏悔的“祖先的黑历史”,但在如何对待文学文本的呈现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在支持本书表现方式的声音里,最鲜明的观点如下:
“请记住,作者只是在重复他从祖父母那里听到的话,早期定居者确实歧视当时居住在那里的美洲原住民。这就是历史事实。我们可能不喜欢它,但这种不喜欢不会让历史消失。当时的黑人小孩不可能西装革履,文过饰非的文学才是有罪的。”
也就是说,一部分读者认为这部作品只是“真实地”陈述了历史,毫无问题。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对“文学写实性”的辩护。
然而,这却是一种对文学“写实”和“现实主义写作”的普遍误读。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文本来看。

故事的开头,我们就能读到一则大部分图画书不会设置的前言:“……它们(注:指故事)可能有很多错误。也许我已经忘记和混淆了一些事件和人物,但是这真的无关紧要……他们中没有一个是伟大而著名的,但他们坚强而善良。他们辛勤劳作,养育了很多的孩子。他们所有的人帮助美国成为了现今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从头至尾读过这个故事后,基本能确定它走的是“写实/现实主义”路线。我曾在《儿童文学,除了想象力,还需要点“现实主义”》中简单地追溯整理过世界文学范围内“现实主义”写作理念的诞生和发展,其在几百年的变化之中始终保持不变的有两大内核:
在价值倾向层面,“现实主义”写作包含着尤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社会现实责任感,突出表现为对挣扎的平民乃至贫民的密切注意,对“不合时宜的人物心态和行为”的关注和同情;在风格形式层面,则倚重叙述、较连贯的情节演进和设置具体的人、时、地、物概念/专有名词等“细节”,以增强“真实感和生活感”。
哪怕许多现实主义作家都承认“真实”只是一种根植于作家个体的幻觉,却仍坚持认为作家应该有意识地选择和安排材料、动用一切手段以书写一个真实的幻觉。
而劳森的这番前言竟让我想起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首次提出的“典型人物”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就是“抓住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即可,事件张冠李戴、记错对象也并不一定有误“生活的本质”。
既如此,我们不妨就以现实主义写作的语法来衡量《他们坚强而善良》。然后读者会发现,其得其失均在于此。
首先必须要指出,很多指责本作的读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内容。

在绘本中图片对应的文字为:外祖父(我母亲的父亲)常常给他的朋友们带回来各种礼物:猴子和鹦鹉,甘蔗,有时还有巴拿巴草帽。

在绘本中图片对应的文字为:……(我父亲的父亲)常常骑着那头骡子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与撒旦进行战斗。
在介绍我母亲的父亲和我父亲的父亲的文字部分叙述他们的体面生活和英勇事迹时,其画面却“背叛”了文字。前者黑奴男孩和仆人负重前行,甚至被祖父携带的动物们折磨得狼狈不堪,后者将中景给了黑人男孩仰视的背影,远景给了高高在上路过的祖父,读者在此处的观察视角和心理显然是更接近于男孩的。
仔细看这两个画面里的男性主角都显得趾高气昂,后一画面里男人还显得有些面容丑陋,自负又滑稽,假如不看文字,恐怕没有人会认为作者对画中男人持欣赏赞美态度;比如陈述印第安人拿走家里食物的画面,也是印第安人被放置在前景和中景里距离读者更近,其面容表情并不比身后握着扫帚赶人的黑人女仆更“穷凶极恶”;又如在讲述我的母亲的内容中,文字叙述母亲害怕伐木工人,因为他们整天大声喧哗还打架斗殴,但画面内工人的形象却并不可怕,相反其笑容温暖可亲,如此等等。

在绘本中图片对应的文字为:……那里还有一些伐木工人。他们每个周六晚上都会拥进城里,制造出大量的噪音,而且有时候还发生各种打架斗殴。他们简单吓坏了我的母亲。
但另一方面,殖民者的视角又确实存在。

在绘本中图片对应的文字为:他有一个黑奴和两条狗……
1994年,本书出过一次修订版。新版对两处细节作了改动,一是将作者用以形容印第安人的“tame(被驯化的、驯服的)”一词(常用于形容动物或物品)删去;二是上图这段话,原版是这样的:“他有两条狗和一个有色人种男孩。狗的名字叫塞克斯图斯·霍斯蒂利乌斯和努马·庞皮利乌斯。那个有色人种男孩和我父亲年纪差不多。他是个奴隶,但他们没有那样叫他。他们只是叫他迪克。(When my father was very young he had two dogs and a colored boy. The dogs were named Sextus Hostilius and NumaPompilius. The colored boy was just my father’s age. He was a slave, but they didn’t call him that. They just called him Dick.)”改成了“他有一个黑奴和两条狗。那两条狗名叫塞克斯图斯·霍斯蒂利乌斯和努马·庞皮利乌斯。那个黑奴男孩和我父亲年纪一样大,名字叫做迪克。”
显然,编者认为这两处表达将对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的物化、矮化和早已被科学抛弃的“人种分类法”自然化、合法化了,因此作出了删改。
此外,涉及祖母的内容只有两页,且无关个人成长,只写了她嫁给祖父生了很多孩子,以及那句不断重复的话“他们辛勤劳作,他们坚强而善良”;本书写到六位长辈,其中三分之一篇幅给了参加南方军的父亲。可见这部书在性别维度的表现上也很值得打个问号。

在绘本中图片对应的文字为:当我母亲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有一些印第安人也在明尼苏达州。我的母亲并不喜欢他们。他们连门都不敲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厨房,坐到地板上。然后,他们就会揉着他们的肚子,指着他们的嘴巴,表示他们饿了。他们会赖在那里不走,直到我的母亲的母亲给了他们一些吃的。
另有一段更有趣的,虽然文字说年少的母亲厌恶印第安人,但画面中却由女性黑奴举着扫帚赶走土著,白人女孩远远望着他们,双手干干净净如同她的道德一般“无暇”;下一页里她又被喧闹粗鲁的工人“吓坏了”。
作品数次重复母亲是“安静而温文尔雅”的,她被送到修道院,她喜欢修女们的“温和、从不大声说话”,她跟着修女学习画画、四门外语、美丽的刺绣和管风琴,她还有时间学习养花和照顾动物……如此对比之下,叙述母亲的“干净文雅”很难不让读者感觉微妙复杂——当作者的直接判断(往往是十分确信的样子)与文本呈现乃至历史信息之间的裂隙太大时,读者很有可能会陷入“一时之间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在反讽”的困惑之中。
当我们注意到黑人男孩身上的补丁和手里的大包小包,了解印第安人和奴隶贸易的相关历史,我们真的很难断言作者是真的无视了这些他自己画下的凄惨对比,仅仅将之作为一种呈现而毫不同情,还是感情复杂、内心矛盾,只是被一种国家主义和家族感情戴上了偏心的眼镜。

《爱花的牛》,[美]曼罗·里夫 著,[美]罗伯特·劳森 绘,蒲蒲兰绘本馆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
尤其是当你知道绘本的创作者罗伯特·劳森正是著名反战绘本《爱花的牛》的插画作者时,会奇怪于当他看到父亲因为战争失去的健全双腿时为什么没有多去追问一句“这场为亲人带来巨大痛苦的战争究竟是为什么?北方军为什么会胜利?”亦如有读者对印第安人取食一节所质疑的:作者“坚强而善良”的祖先们为什么从来没有提问或解释过“嗯,我们繁荣文雅,而同一空间的其他人却在挨饿。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作者就反复指称祖先们是“善良”的,且又花费大笔墨书写了南北战争中的父亲如何英勇、战后如何受伤,但既然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是民主、自由、包容、多元,那么祖先们究竟是如作者所说的‘创立了这个伟大的国家’还是背叛了这个国家的精神?
在这些地方,作品背离了现实主义写作(乃至所有优秀“文学”)的根本精神,即尽管存在一些复杂、自相博弈之处,但作者仍未能充分说服读者这些先人是“善良”的,这个文本是“人道主义”的。
而这些原本是可以通过“技术处理”做到的。
如果作者不认同祖先们的看法,他可以用直接引语等方式表示某些观点并非自己持有而是祖先原话,与它们保持距离乃至表达否定态度。作者应该做的是,动用各种写作方法告诉孩子哪些部分是旧的认知,如今我们形成了新的共识,而非不作处理。
如果说这些故事是“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可以作为辩护理由,那么那些旁逸斜出的、同情弱势民族的画面和裂隙过大到如同反讽的前后文字也是老人的意思吗?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这没有任何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应该对这些关键态度的矛盾变异给出一个前后逻辑通顺的、符合创作语法的交代,不能随心所欲地这里“是”、那里又“不是”。

在绘本中图片对应的文字为:……有一天傍晚,有消息说“扬基人”就要来了,我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说他愿意骑着艾玛·G到安全的地方去。
另外,在形式层面上,细节对现实主义写作至关重要,该文本却没有交代到位。比如主人加入南方军反对解放黑奴,家中的黑奴男孩却和主人们一起哭泣;比如北方军要来了,画面里的黑奴看起来不像文字说的那样在逃跑,倒像是在通知白人们快作警戒或者逃命。这些画面连当代的美国读者都很困惑,在书评中频频发问,何况缺乏背景了解的外国读者。
这些今日看来有悖常理的现象,当年的确曾经存在过,然而时代毕竟变化了——本书隐含作者的局限正在于此,他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只是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有限共识,他不具备下文我们要提到的卓越作家所具备的跨越时空局限的感受力、爱和自我背反性。没有任何前情铺垫交代,就要读者接受黑奴“可能是因为主人善良或惰性而想维持现状所以不站在北方军一边”(这只是我推测的理由,考虑到部分美国南方文学乐于写奴隶主与奴隶其乐融融的通例,没有在本作内得到足够充分的印证。与此同时,文字还在讲述解放奴隶的北方军的胜利),是不合文学规则的。
出现了这样偷懒不负责的处理,读者即使出于为文学生产生态的长远计,也当拒绝完成与作者的信任契约。事实上,该作品中流露出的某些观念被文化研究者认为即使在作品诞生的1940年代里也显出“不可思议的保守”。可作处理而不作,这也就难怪今天的美国读者面对这份前言时并不将它当作创作理念的申述,而是不无尖锐地批评它简直是一份“免责声明”。
文学写作的“真实”与卓越作家的“真诚”
什么是真实?作家们关于现实主义的说法无法统一,读者对“真实”的认识也并不一致。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比美国更多了一份作为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的文艺批评价值尺度,可以说,文学应当尊重现实、模仿现实的观念在国内有着更深厚的土壤。
2016年我在拙文《曹文轩儿童文学中的“性别观”落后国际社会多少年?》的评论区亦曾看到过类似的留言:中国农村/中国女性就是这样的,他只是如实地反映了彼时彼地的“实际情况”而已。
那天的留言区很踊跃,但我认为有一条评论值得被我们更深地记住,现将这段回复全部摘录如下:
“农村女孩子勇敢的其实很多。我以前一个同事,父母不让读书,她就找亲戚借钱上学,承诺工作后还。
所以,评论中所谓的:‘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写照,只能这样写’的论调可以休矣。”
这段话值得我们多念几遍,因为这位读者其实是在“申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见过并非如此的生活”。
是的,生活并非仅是如此而已。这是一个多么重要而又总是被忽视的简单事实。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谁能为“真实生活”代言?假如出现了一群这样的代言人,我们该信其中的哪一些?
并不是每一个作家和读者都具有细心观察生活的天赋,很多时候,人们口中的“真实生活”只是大多数人印象中的生活。而文学艺术,就像贡布里希说的,召唤的正是那些从未被大多数人正视过的却真实存在的经验(可能是你未经历过但其他人经历过的,也可能是你经历过却不知何故被“忘记”的)——我们借文学以重新辨认、理解和开拓“现实”。
再傲慢的人也隐隐知道,自己所认识的世界并非完整的世界,而这就是我们想要“读书”的原因。我们读书、读内容丰富的好书,行万里路、认识更多不一样的人,才会真正明白那些“新认识的现实”原本就是构成我们外部世界的真实部分。如若没有这个不断发现“完整的世界真相”的过程,我们的意义世界将成为整齐僵硬的一块铁板。
文学不只是陈述反映,用詹姆斯·伍德的话说,文学并不是要求我们在哲学意义上去“相信”什么,而是具备想象某个世界存在的可能性,简言之,是同“不可信”作斗争。这一堪称“伟大”的斗争既提升读者在艺术层面上的建立想象体验的能力,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层面的进步——因为不容易想象和相信的,往往是被主流认知、意见和价值所排挤、不敢承认的,可能是自身内心不敢言说的欲望,也可能是边缘势弱者的声音。正如上文读者所说的他记得的“农村真实生活的另一面”。
难道那些活泼的、发奋学习走出大山的少女不是真实的吗?难道那些性格意志强硬、雷厉风行当家做主的成年农村女性不是真实的吗?难道我们没有意识到当我们轻巧地说“真实世界就是如此”的时刻,其实是无比蛮横地把她们努力生存的物理真实和艰难挣扎的意志真实从片面定义的“现实世界”“真实农村”里抹除了吗?
同理,被殖民者的真实、下层阶级的真实也是如此。“真实世界”层层叠叠,何尝简单?作家要看得到生活万花筒中的层叠世界,又要长怀悲悯之心。是的,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好的文学作品,叫人“生”而不叫人“死”,叫人于绝望中看到不妥协的希望,教人善良而不教人傲慢,教人智慧通透而不教人片面武断,叫人觉得世界美好人间值得来这一遭,也值得你用心把它变得更美好——举凡我们此刻想得起来的卓越作品,无一不如是。
我不认为《他们坚强而善良》是优秀之作,是因为我认为它基本上没有做到真正卓越文学做到了的“情不自禁的自我纠正”。

《安娜·卡列尼娜》,[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草婴 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4月版。
比如《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本意甚至是希望安娜这样的女人获得教训,作家本人又很有些自恋,于是我们能看到文本中大篇幅文字给了带有不少托翁本人印记的列文的生活和心声,60万字、以“她”为名的大长篇里,安娜真正分到的文字不多。
然而奇异的是,叙述者越是赞美列文这段正统合规的婚姻是多么健康、为双方带去滋养,安娜的光芒就越动人。这部作品仿佛有两个隐含作者,他们不停地相互排挤斗争,最后同情和欣赏安娜的那个胜出(谢天谢地!),于是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的那个“托尔斯泰”带领着一代代的读者前赴后继地拜倒在安娜的足下,“列文的啰啰嗦嗦自以为是的哲思比不上安娜裙裾荡起的一片波纹,甚至比不上她挤火车时提的那个美丽的小手包和车窗外的雪让人印象深刻、心驰神往”——这是文学对世界的评估和保护。托尔斯泰到底不愧为真正的好作家,他不但将初版大纲中愚蠢的女主改头换面成如今的样子,更将题目直接改为他理性上并不欣赏的女主人公的名字。
且待来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说好的作家是能超越自身所在时代所限的。即使创作之时整个社会都没有准备好接受某些美好,甚至哪怕作家本人都没有准备好完全接受它,他也会忠于某种“更高价值”(哪怕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但只要他感觉到了,他就预备忠实于它),把作品留待来日。这样看来,好的作家对人类的向美与向善属性有着不可思议的信心,或许他们自己都不曾发现他们一定是相信未来的。
也因此,“未来”总是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从这个角度看,政治正确的理念推行,对文学是存在积极意义的。它促进人们去观察、认识和理解生活的另一面,而拥有一群被打开了宽广的认知之门的读者,对文学在该社会的传播(特别是特殊题材和写法的包容)一定是裨益良多的,真正卓越的作品也更有可能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中。
最后说说我们可以拿这些“不够未来”的文本怎么办。
有读者提议“凯迪克奖组委会应该从他们的记录中删除它。”我想这不是个好的做法。不必删除,恰恰应该保留,我们对待不够好的价值观的作品的思路应该转变了,不要总是一刀切下架删除,长远来看真的非常不利于良好的写作生态的维护。
有一些处理方式可供参考:它们可以被拿来当作中学生的辅助学习材料,如果有可能的话,放在批判性思维课程或社会正义/公民课程中。考虑到实践操作中很难真正避免年幼的孩子读到它们,如今的出版者应该为这类作品附上导读手册,对其中的视角问题加以说明和引导,如此既尊重创作本来面貌、保留了历史/文献原来的样子,也可有机会看到其中作者矛盾的表达和情感的微妙,更可以将之当作一份教导孩子认识“历史文献”之伪饰性和叙述者话语权的“天然教材”。
用文学的方式解决文学的难题,何乐而不为呢?
撰文|王帅乃
编辑|申婵
校对|李世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