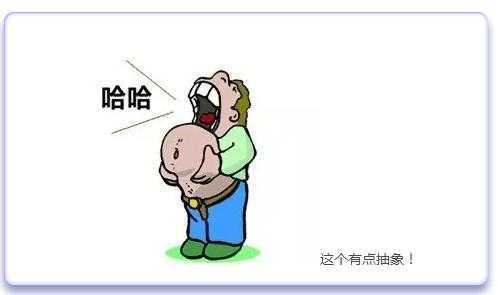栏目:文棚
捉泥鳅(散文)

生于美丽乡村的我,对捉泥鳅、捕野味,这样的趣事甚是喜好。在我童年到少年时代,故乡那肥美的水田里,清澈的溪流中,总有滑溜的泥鳅、灰青的鲫鱼诱惑着我,它们喝山泉水长大,属于纯野生的鱼类。儿时,我经常会提一个小桶,或者拿一只箢箕,在故乡的阡陌间、小溪边来回勘查,去寻找心中的那份企望。记得每次出捕必有所获,永不落空。久而久之,我变得热衷此行,渐渐地,将此作为一项寻找快乐的方式。捉泥鳅、寻野鲜,温暖了我那段懵懂的岁月。
在那些年代里我无忧无虑。百花争妍的春天花香满径,内心却早已盼望着夏日的荷风拂面。那时,在一个个晴朗上午,去村口水田里捉泥鳅成了我最乐意的趣事。而教会我捉泥鳅的是当日捕鱼高手——四哥。那时少不更事的我,每次见到满载而归的四哥,对他由衷的佩服。童年里,总喜欢跟在四哥后面,与他一道去捕获那种乡间独特的快乐。
出村口不到百步之遥,有一块四方形的水田,似极了一个“四”字,那是我村里的一块秧苗田,不大,一亩见方。不知为何,此田的泥鳅特别的多,先一天捉完第二天去,准不会让你扫兴而归。经常捕鱼的四哥早已熟记于心,这块肥沃的烂泥田,在他眼中俨如一座“聚宝盆。”

儿时的仲夏,新麦磨成的面在这个季节飘着诱人的香,水田里的小泥鳅,饱享着一春肥水的哺育,纷纷长成筷子般粗细,村外的肥水田里的烂泥,是它们的安乐窝。晌午,太阳吐着火舌朝地面直射,火辣辣的地面似乎要燃烧。漫步田间,可听到水稻拔节的声音,有些超早稻正在扬花,不久,沉甸甸的金珠一颗颗倒挂,如一个个含羞的村姑低垂着一头娇羞,在阵阵荷风中荡起延绵的金浪,四野稻香沁人心脾。
从五、六岁起,获悉四哥要去捉泥鳅,总会尾随其后如一跟屁虫。头顶一个黄铜打造的脸盆(听说是爷爷的遗产)满怀希望地来到水田处,不敢高声大语。懂事的四哥迫不及待地已迈进水田,泥水中响起一连串咕嘟咕嘟声,似在欢迎四哥的到来。随手捧起一把泥摊开于田埂上的四哥,展开灵巧的小手,在烂泥里翻弄几下,只见一两条泥鳅,在强烈的阳光下摇头晃尾,似想趁机溜走?遇到眼疾手快的四哥别想开溜。此时喜不自禁的我,慌忙从头上掀下家传古董——铜面盆,接住四哥新捕捉的泥鳅。一阵噼里啪啦传入耳鼓,咋一听还以为是邻家顽皮的小童,在敲打着他心爱的拔浪鼓。孰料,那是泥鳅接触到滚烫的铜洗脸盆之时,挣扎蹦跳的声响。随着盆里泥鳅的增多,平静逐渐恢复。只一会工夫,之前我用来遮阳的洗脸盆,挤满了泥鳅。

父亲见到周身带泥,满载而归的四哥,写满沧桑的脸上总荡起欣喜的笑。在那种物资并不富足年代的农村人心中,鲜活的泥鳅是一种极受青睐的乡村美味,无法抗拒。端午过后的乡村,田野绿油油的,各式时蔬在夏雨熏风的浇灌中逐渐成熟。母亲会到菜地摘取几个新熟的辣椒,一两条黄瓜回家,泥鳅洗净上油锅煎炸,伴入青椒、黄瓜爆炒,装盆上桌,满室飘香让人馋涎欲滴。几十年未曾品尝到了的这道乡野美味,犹在诱惑我这个羁留他乡的游子。
那些年里的新捕泥鳅,或煎或炸,或炒或炖,都不失为一道风味独特的佳肴。为家人生计总是忙个不停的父亲,最好这味烹煮的乡村野味。见到面露喜色的父亲,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和四哥去捉泥鳅的劲头更大了,寻野鲜、投父所好、皆大欢喜。
令我百思不其解的是。为什么当时故乡那肥田沃野之隅,溪水圳畔,会有如此之多的泥鳅和野生鱼类,取之不绝捕之不尽?而那时,会捕鱼却从不吃鱼的四哥是村中同龄人之中的捕鱼高手, 他驾轻就熟,总是手到擒来。捉泥鳅成了四哥与我收获乐趣,引以为豪的美差。
“近水识鱼性,近山知鸟声”受四哥耳濡目染,我慢慢也掌握了捉泥鳅诀窍。泥鳅喜欢在松软的烂泥中活动。捉泥鳅有两种方法,其一为点眼捉鱼顺藤摸瓜式,居于泥沼中的泥鳅,为了方便出入会钻出一个小洞,顺着这个小洞,把这一堆泥捧起来,藏在洞里的泥鳅只有束手就擒;其二为围堤成池,慢慢将小池中的水汲净,用手翻开烂泥,无处藏身的泥鳅成了你的战利品。乡村的夏日,阳光炽烈而灿烂,头顶烈日,泥浆溅到脸上,随着汗液滑动,使我变成了花脸猫,这些我不屑一顾,心中只有烂泥巴中做着美梦的小泥鳅。
人的一生总有些难以忘却的故事,在纷繁复杂的岁月里永不变更;她如一瓮陈年老酒历久弥香;譬如儿时的我,总会迷恋着烂泥巴里的小泥鳅……
(文棚是一个以散文为主的共享平台,面向全球华人开放,供作者、读者转发推送。其“写手”栏目向全国征集好稿,外地来稿不论公开发表与否,皆有可能采用。凡当月阅读量达6500次,编辑部打赏100元/篇。请一稿一投。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非签约作家请注明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全称、账号。)
◆中山日报报业集团新媒体中心
◆编辑:徐向东
◆二审:蓝运良
◆三审:魏礼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