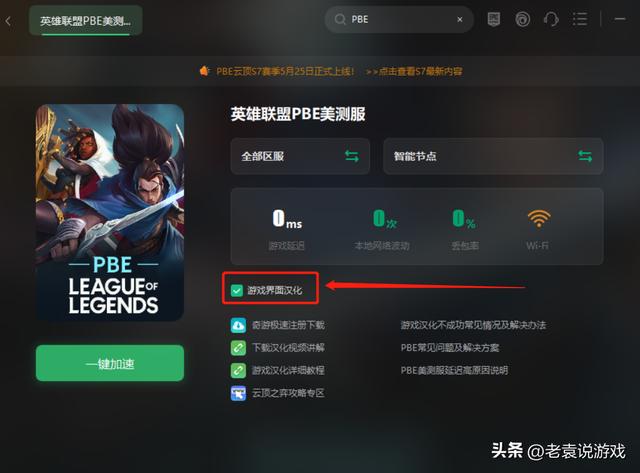《别叫我兄弟》是一部充满杂糅和融合特色的电视剧。他是在原创故事提供者乔长军和总制片人乔柏华“电视剧究竟应该偏文艺还是偏商业”的争议中完成的,也是南方编剧交来的稿子被导演和制片人推倒重写、加重了北方色彩之后开拍的。更重要的是,看完全剧之后就会发现,剧情在写实和虚构之间来来往往,年代质感由写实部分提供,而矛盾冲突由虚构部分负责。
“两兄弟,一辈子”,这是高满堂老师一贯的戏剧脉络,也是港剧编织故事的经典套路。如果把时代背景放在过去30年间,内地兄弟恩怨戏的创作是受到很大制约的。想翻起大的浪头,就要有成建制的坏人,一不小心就会成了“反腐剧”或者“涉案剧”,市场的出口一下就窄了。要不您就始终把双方冲突写成人民内部矛盾,斗法的本质是逗趣;要么您就另寻出路,到无法无天的外邦去寻求对立面,戏剧世界立刻就能天翻地覆。
演出开始的时间应该是七十年代末,或者八十年代初。
那个时候,或者再早些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查歌、打架、拍婆子,是北京社会青年的三大主业;冰场、老莫、天桥剧场,是他们出没的主要场所。
拍婆子和打架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雄性动物对雌性动物的争夺从来就伴随着战争。刚开场,我们的两个主人公:韩子辉和佟海涛就与刀子(余皑磊)的几十号人对峙,地点貌似在卢沟桥下。围绕着叶晓晓由谁来“带”的问题,他们话不投机,打在一起,转眼之间血肉横飞,有人中刀,有人中砖。警察同志不失时机地赶到,战士们一哄而散。
没错,这部剧总是让韩佟二位爷置身于双拳敌百手的境地,而且还不一定输。现实中也许有这般战斗力和勇气的人,但毕竟不常有。敢于这么在常情常理之外做文章,说明主创人员心里涌动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梦,要么像乔峰在聚贤庄里一样凭着绝世武功一人打败一百人,要么像杨子荣在威虎山一样凭着过人胆识一人镇住一群人。反正,两位好汉就是没有输。
这个血色开局的后果很严重:韩子辉锒铛入狱。这不仅终结了他们泡妞打架的好日子,也宣告了人生分岔的开始。没多久,佟海涛被“绑赴”香港,被迫成为商界精英,而韩子辉困守原地,开始创业之旅。创业是从“倒儿爷”开始的,先把“雪花膏”变“珍珠霜”,接着就南下倒腾家用电器,最后进军房地产界成为大亨。
韩子辉几落几起,终于发迹,这一段真实、耐看。它映照了改革年代中民营经济野蛮生长的态势,见证了一批富豪在创业过程中的顽韧和不堪。他们的商业嗅觉是敏锐的,同时也身负原罪,雪花膏毕竟不是珍珠霜。他们不追求绝对的诚信,但有自己的一套诚信守则,谁违反了就要遭到报偿。老张以“国产电视机雪花大”为由切走韩子辉的两万块钱,被他找机会以摔坏的冰箱为筹码进行了打击报复。
虽然做生意离不开请客吃饭,可做生意终究不是请客吃饭。所谓真实,就是不仅要给观众看孔雀五彩斑斓的屏,也要展示屏背后并不好看的杂毛和屁股。不仅要出示主人公的急公好义和情深意重,也要表现他的睚眦必报和价值迷失。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只见金光灿烂而不见阴影是不足为信的。
绿军装,蓝裤子,军用挎包。前门,后海,白塔寺。泡泡妞,打打架。这部剧是从《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出发的,甚至南下广州做生意的路径也相同。不同的是,《与》剧始终着墨于混沌、迷茫、血泪斑斑的青春,而《别》剧走进成人世界后流连忘返,专注于生意经和人心更变。《与》剧终其篇也没有走出青春的感伤,《别》的主人公完成了社会化成长(除了佟海涛),戏到终局的韩子辉是不可战胜的,人生观、世界观、爱情观无比成熟坚定。
韩子辉一路的风霜,虽然总是被戏剧化的情感戏和商战戏所扰动,但如果有一双穿透浮云的慧眼,还是能看到好多真东西,关于个人,关于时代,关于国家。
(2)情感的戏剧化

电视剧不是真人秀,一地生活搬上荧屏注定不解渴,电视剧不能没有戏剧冲突。从观众的角度看,冲突是他们要看的戏。从主创的角度看,冲突是商业卖点。
佛曰,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前四个跟生理周期有关,后四个则纯粹是感情因素作祟。
感情线是用来粘连剧情的,也是用来吸附观众的。如果不是因为叶晓晓(姜妍),韩子辉和佟海涛想必会是终生的好友,至少不会走向生死对决的猎场。如果不是因为罗雪娟(方安娜),韩子辉和叶晓晓想必早已缘定终生,王子和公主般快乐一世。再加上相对边缘的庄大力(周璞)和上官晴晴(程媛媛),六个人都为“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所苦,这才有了这许多泪眼婆娑和愁肠寸断的夜晚。

如果一定用逻辑来求证几条感情戏,不大顺的地方还是有。比如说,叶晓晓与佟海涛分手,是因为对方在关键时刻消失,导致母亲病重不治。可是佟海涛后来天天写信,一写就是三年,她愣是一眼不看,全部撕毁,稀里糊涂一直不给机会。后来叶晓晓与韩子辉分手,是因为罗雪娟挑拨离间,她又一次负气而去,仍然不给解释的机会。须知情侣之间,移情别恋是经常发生的,一旦发生就很难逆转,而所谓误会是最容易消除的,因为既为情侣便了解对方也疼惜对方,了解便不易发生误会,疼惜便会回头审视误会。这一审视,所有的谗言都会败露,所有的误会都会烟消云散。叶晓晓的行为方式只能用病态来解释,单亲家庭导致心理障碍。
庄大力这种无怨无悔的“中国好备胎”,现实中不乏其例。上官晴晴这种无限包容的贤妻范儿,在今日怕是难找了。在一台戏剧中,总得有功能性人物,他们或者是麻烦制造者,或者是垃圾承受者,他们像坚强的礁石一样耸立在戏剧海浪的必经之路上。如果,我说的是如果,他们能活得更性情一些,或者行为模式能更复杂一些,他们会变得更可爱。
(3)偏执的佟海涛

剧中最得我心的其实是上官伯儒对佟海涛的打磨。作为一个正在努力做家长的中年人,我除了经常向“中国狼爸”讨教之外,也老想从影视作品中学得一二。上官伯儒将一天到晚只知道打架、泡妞、讲义气的佟海涛“绑”到香港,既是为了不负老友之托,也是为自家培养上门女婿和接班人,所以他既是严厉而有爱的长辈,也是传业授道的恩师。
他采取了挫折教育和激励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法,他恩威并重、中西合璧地调教这匹狂野的小马驹,他舍得给机会也舍得剥夺机会,他放手任用他也重手敲打他。在我看来,他的教育理念相当先进,手法相当凌厉。可是他的教育完全失败了。在佟海涛差点被扔到海里喂王八的那天,他先痛骂又给钱,明明是为了挽救一个迷途少年,可是这个少年将这一切理解为羞辱和鄙视,在写给叶晓晓的信里发誓报复。
佟海涛看问题的角度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似乎也从这虚构的情节里看到了教育的有限性。有些狼崽子是养不熟的?有些奇葩是劝不转的?有些愚昧但顽固的价值观是不可战胜的?有些人的天性和命途是不可改变的?
情感波折多因叶晓晓的偏执起,商战风浪多因佟海涛的偏执起。

剧中的麦克(叶静)曾经问佟海涛:我们这是求财还是置气?这一问,的确问到了关键。正宗的商战剧要遵循商业的逻辑,是为了利益而殊死拼争。这部剧中的两次商战都是“伪商战”,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而是为了出气。第一次,富华牌收录机大战,佟海涛挖坑把韩子辉埋了。第二次,京城拿地大战,韩子辉突出了佟海涛的包围圈。
佟海涛和韩子辉没有本质上的价值冲突,所谓“抢走女朋友”很大程度上是个误会。一个人穷尽一生去报复一个误会,这事怎么看都有些滑稽。就算佟海涛一意要做人上人,他报复的对象也该是香港那帮人,而不应该是老哥们韩子辉。
在《无间道》的警匪站过的天台上,在《大时代》里丁家父子跳过的摩天楼上,韩子辉和佟海涛展开了最后的对话。佟海涛说了一句话,用以解释自己一生的行为:“我们这种人,脸比命重要!”他就是这样,善意和恶意不分,哥们和敌人不分,机会和黑洞不分,为了一种虚妄的信念,把自己玩了进去。
《别叫我兄弟》是“总分总”的结构,查架和倒爷部分写实,情感和商战部分想象。韩子辉身上能看到一个时代的影子,而佟海涛如同破空而来的传奇。韩子辉身上寄托了创作者的很多感情和理想价值,佟海涛则负有搅动戏剧的特殊使命。这实际上是把流行的都市情感剧和商战传奇剧合一了,这种虚实相生之法在当下的电视剧市场中独树一帜。
文/李星文
喜欢本文就点击右上角分享吧!
搜索微信号“dusheme”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影视独舌】
由资深媒体人、影视产业研究者李星文主编,提供深度的影视评论和产业报道。高冷、独立、有料,助大家涨姿势、补营养、览热点。涵盖微信、微博、博客、豆瓣和人人小站、网站五大载体。在今日头条、新浪、网易、腾讯、搜狐都有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