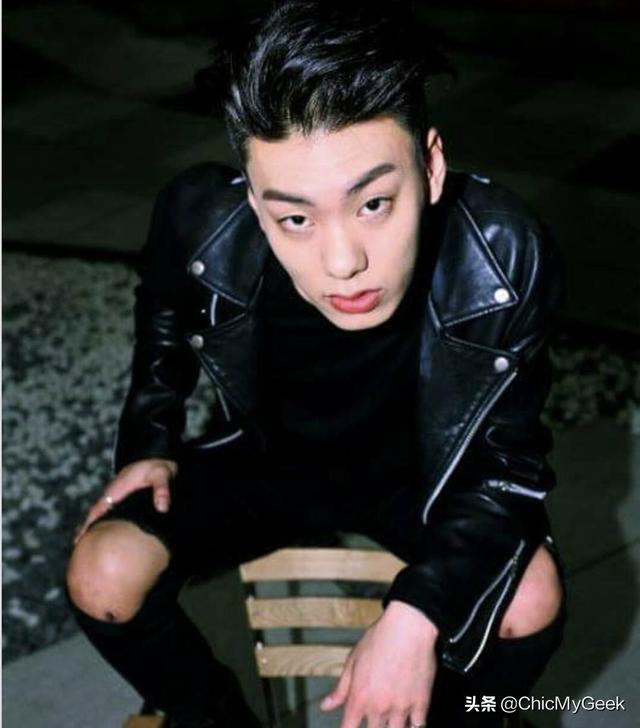第二章第二节 徒步上班,苦中有乐,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老爸一路走好天堂安息短句?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老爸一路走好天堂安息短句
第二章
第二节 徒步上班,苦中有乐
一九七四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清河门地区还是阜新市郊区人民公社,公社下设生产大队,大队下设若干生产队,后窑当时设一、二队,赵家窝堡是三队,西山村从村中间往两头分,村东头为四队,村西头为五队,我们家就属于第五生产队。
生产队的农活年年重复着,周而复始,一年干到头也挣不到钱。父亲到现在是看明白了,这样过日子实在不行,苦日子没个头,得想办法出去挣钱,不出去打工挣钱守在农村,就没有出路,不会过上好日子。
那时村里也有不少人都外出到黑龙江的漠河、黑河等地找工作挣钱,就是人们常说的“跑盲流”,有挣到钱的,也有挣不到钱的,后来就都因为没有公社介绍信,也就是没有身份证明被政府给遣送回来了。家里后院的王守义就曾去过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黑河、漠河等地,钱虽然是挣点,但也受了不少苦,最后还是因为没有介绍信被遣送回来了。
父亲可不想做“盲流”,要找个稳定的工作。于是就找当年在城里工作时的老工友,托工友在郊区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找到了工作。于是再托我表叔梁尚武在清河门公社开的介绍信,这才走出生产队到郊区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当了一名架子工。这才结束了还乡后的生产劳动,算是城里半个工人,按现在话讲就是进城当了一名农民工。
在那个年代,社员外出打工如果公社不允许,不给开介绍信,到外面是找不到工作的。而且技术再好,哪个单位也不敢要,所以能出来打工的人很少,不像现在这样凭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全国跑,哪都能去,那个年代没有介绍信就按“跑盲流”处理,送到收容所了,然后让户籍地生产队接回去进行教育管理,所以社会上流动的人口非常少,人口也好管理,谁家晚上来人了,第二天早晨公社的公安人员就知道了,那时公社就几名公安人员,一个清河门公社的公安人员还不如现在一个派出所多,可社会治安是相当平稳有序,这与当时讲“阶级斗争”有关,人们的思想禁锢保守,头顶被“政治氛围”笼罩着,谁还敢越雷池半步呢,家里来个外人马上就得向大队报告。
社员出外打工必须经生产队、大队同意后,再到公社开介绍信。那时政治气氛浓,管理得非常严,所以父亲想出去找工作,必须得有介绍信,先是找人说好话征得生产队同意,然后找大队同意,最后才能拿着介绍信去公社换介绍信。
拿到公社介绍信,这其中也费了不少周折,是一路求人找关系才开出来的。
记得当年五队队长是杨德成,他一直当了很多年队长。此人非常跋扈,说一不二,为人做事粗犷,看人下菜碟,很多村民都巴结着他,围着他转,生怕他在生产队里分工计分时给穿小鞋,如果那样,天天出工可就白干了。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还记得村里有不少被划分为“四类分子”的,那些“四类分子”就没少被他折磨,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时常让那些“四类分子”来我家前院南边空地跪着。有时候那些“四类分子”一跪就是半天,村上的广播里一通知啥时候来那些“四类分子”就得啥时候到,在地上跪着一动不动,不让起来谁都不敢起来,要是不听话,就得开会批斗,哪个敢不服啊。那个时代“四类分子”被批斗是常事,批斗现场就在五队原来加工厂院里的西厢房,就是现在巩德友家的院,我记得有几次是在吃过晚饭后开始批斗的,一批斗就是到半夜,给被批斗的“四类分子”戴上高帽,站到台上,让村民检举揭发,进行声讨,队长啥时候说批斗过关了啥时批斗会才结束。
爷爷当年也是被遣送到后窑生产大队接受广大社员监督改造的,但爷爷没有受到像西山“四类分子”那样的待遇,不过因为有成份问题的这顶帽子,子女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要受到牵连和岐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成份问题的决定》,为“四类分子”摘帽,并且其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待遇,不得岐视。所以后来哥哥参军和我考上警校时均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当年的生产队长,在村里是绝对的说了算,那真是耀武扬威,全村人都得听他的。村里累活脏活都少不了“四类分子”的身影,比如我们家前院就是原来生产队的骡马圈,圈里二十多间房的骡马粪尿常年由三位“四类分子”即河南沟王春林的老爹王润、曹云霄的老爹曹庭众和我家后院的王守礼老爹王平负责垫土起粪,三位老人家是起早贪晚,冬冷夏热,既脏又嗅,天天又苦又累,受尽折磨。所以这个生产队长在全村人心中威信也不高,普通社员的待遇也是不平等的,队里的农活由他分配,和他关系好的人就给分配点轻活,否则还不得把人累蒙圈了,还挣不多少工分。那时队长也不是全村人选举,而是公社任命的,公社也不听社员的呼声,很多社员对他是敢怒不敢言。
对我们家而言,父母在生产队上工时也是经常给找麻烦,现在又好长时间不放我父亲出去上班。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连说好话带找人说情他才勉强同意了,在生产队开出了介绍信。生产队同意了,再到后窑村找大队长,当年的后窑村大队长是崔风祥,这个人是老队长,和爷爷关系不错,有点交情,当年爷爷还乡时,虽然在个人成分划分时,爷爷被划分为“四类分子”,在村里开批斗会时也挨了不少打,遭了不少的罪,但也尽量找理由不让爷爷参加,并且知道爷爷腿脚不好,在生产大队对爷爷和家人也挺照顾,找到崔风祥大队长,很快就开出了介绍信。
村上大队的介绍信开出来了,最关键还是公社的介绍信不好开,不认识人根本开不出来,对人不对事。现在搞营商建设,政务公开,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搞公平公开,那时是看人办事,全是凭人际关系,没人真办不成。好在我表叔梁尚武当时在公社医院上班,是X光室的,拍X光片的业务权威,接触人多,也认识些公社里不少人,父亲找到了表叔,表叔和父亲关系不错,挺投脾气,平时也多有走动。表叔托关系就把这个介绍信开出来了。当年如果没有表叔帮忙开这个介绍信,父亲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西山生产队的,所以有了表叔的帮忙,既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
有了这张介绍信,父亲才来到了郊区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当上了一名架子工。这个工作比较累,属于高空作业,特殊工种,也很危险,身体不好也干不了。如果不是经济和家庭压力,父亲也不会再次从事这个行业,这也算重操旧业,因为当年在城里时就干过架子工。这次来到郊区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一干就是十几年。
父亲自从到郊区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当架子工以后,家里每月也见到零花钱了,经济条件也逐步有了好转。我们家在全村人眼中的地位也在一天天发生着变化,也越来越受到全村人的关注。
当年的郊区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就是细河区第一建筑公司前身,地址在细河区的四合镇,距离清河门大约有三十多公里。那时不像现在交通发达,火车、汽车都有,高速公路、阜锦公路都畅通无阻,那时仅有一条公路就是老阜锦公路,路面比现在窄多了,而且也没有汽车通行,都是驴车、马车走,道路坑洼不平。我记得小时候大人们赶马车去市内得三个多小时,要是办点事,去一趟市里得一天时间。
父亲当年从清河门去市里主要还是坐“小零客”,这列“小零客”运行区间是锦州和阜新之间,早晚来回往返运行,车头就挂三五节车厢,这列火车主要是运输市里去清河门煤矿上下班通勤工人的,还有一些零散的阜新和锦州两地的旅客。那个年代坐这列“小零客”列车,检查的也不太严,多数都是煤矿的通勤工人,工人们都办月票,父亲刚坐车时也办月票,后来有时候就不办了。因为在车上有时检票,有时也不检票,时间长了也都熟了,连火车门的钥匙都是自己配的,有查票的来了,父亲就躲到车内厕所去。工人们上车就玩朴克,消磨时间,一直玩到车到站,早晨上车就玩,晚上上车也玩,玩朴克是一天中这些跑通勤车工人最开心的时刻,尤其是晚上,大家坐在一起,玩会朴克,有说有笑,把一天的苦和累全忘了。既是娱乐,也是消磨了时间,更增进了工友们相互间的感情。
这列通勤车,早晨是七点三十五分从清河门站开,到市里是八点十五分左右,晚上六点三十五分从市里开,到清河门七点十五分左右。
清河门火车站当年在清河门煤矿东边一里多地处,是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修建的“人”字房的三等站,只可惜现在已经拆掉了,从现在保留下来的义县老火车站还能找到清河门当年老火车站的影子。
火车站距离我们家西山村约有十里路程,中间还得穿过老街里和清河套,再过后窑村。农村的土路也不好走,再加上那个年代经常下雨,清河水属山水汇集的,水深流急,河面也宽,河上只有一个简易的木桥,能走人,走不了车。夏天发大水,桥有时候就被洪水冲断了,那就过不去河了。
父亲每天是早晨天不亮就得从家出来去火车站,走一个小时路程,坐火车一个小时,到市里东阜新乘降所下车后,还得走半个小时,经过市中心解放广场向北走到头才能到公司,这样算下来,父亲一天往返的路程就将近三十里。
到公司有时还得立龙门架,上架子绑杆子。
所谓的龙门架,现在被塔吊取代了,当年没有塔吊这样先进的吊装设备,就是一边由三根(或四根)二碗粗钢管组合的“门”字形架子,形象地称为“龙门架”,把它立起来,顶端安上滑轮和钢丝绳,钢丝绳一端连接地面上的绞车,另一端连接贷架来用来装卸货物,这就是一个简易的龙门架升降机。
立完龙门架,盖楼时还得在楼外墙绑上施工的脚手架子,搭脚手杆,这就属于是高空作业,也算是特殊工种。四层五层高的楼都得一根杆一根杆自己带上去用铁丝绑上。绑好了,瓦工才上去干活。要是现在别说是干活了,走到单位就得累躺下,可见当年父亲吃的辛苦,现在是无法想象的。
正是因为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为了这个家能过上好日子,才激励着父亲每天超负荷运转,支撑起了一个家。
父亲到晚年腰疼驼背,体力不支,这与年轻时身体透支有直接关系。
那时人们生活水平很低,没有更多营养补充,我记得父亲每天早上带个饭盒,到火车站时买一块水豆腐,算是中午的菜,中午自己用饭盒煮一盒高粱米饭。偶尔开工资了能买点猪头肉或是猪尾巴,算是见荤腥了。
那些年,夏天还会有些青菜吃,冬天在家平时就是土豆、白菜,母亲一年也能买几次肉,但不要瘦肉,专要肥膘的,都得炼出油,把油放罐里存着,等炖菜时放一小勺。如果条件允许,在高粱米饭里伴上一汤匙猪油,再加上点酱油,那是特别香的,不亚于过年的生活,那个时候一年不断猪油就是好人家。
当年郊区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不单是承建楼房,也承水塔、烟囱、桥梁等建设任务,六十年代初阜新发电厂扩建时的大烟囱就是父亲在还乡前参与承建的。
承建的桥梁就多了,比如一九五八年修建的海州桥父亲就参与建过,不过在二○一九年的时候因为桥龄太久、桥面狭窄而进行重建了。还有七十年代修建的清河门通往义县稍户营子的细河堡大桥,这座桥也于今年年初进行了重建。另外八十年代初修建的清河门老爷庙大桥,父亲都参加过。
前几年遇到几个当年和父亲一起跑车的老工友,还问及父亲情况,他们说父亲当年真是有耐力,很了不起,多么辛苦啊,他们都很佩服父亲,无论是刮风下雨,父亲都是风雨无阻。走那么远的路去上班,下班还得往回走这么远,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可是父亲就是这样走下来了,走出了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到八十年代初,家里经济有些好转后,父亲才买一台二手自行车,开始骑自行车上下班,这样比走是轻松多了,但同样辛苦,因为这条路坑坑洼洼,上坡下梁,平时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现在想想,要是我肯定没有这样的毅力坚持下来,挣多少钱我都不会干。是父亲辛辛苦苦一路走下来,让我们家庭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当年,那些老工友和父亲一样,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奔波在市区两地的路途上,饱受了颠簸之苦。
在火车上他们围坐在一起,放松了心情,玩玩朴克,自娱自乐,缓解着劳累。
时至今日,他们那些工友仍然很怀旧,非常珍惜当年他们“跑车”时结下的友谊,这就是那个时代给他们留下的最难忘的时光记忆。
第三章 自强不息,勤俭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