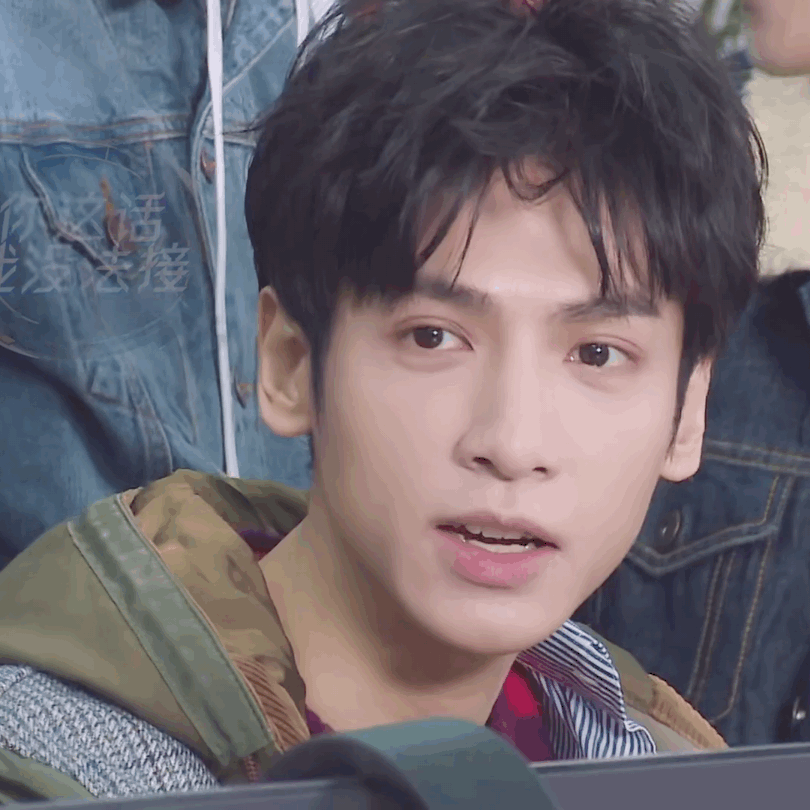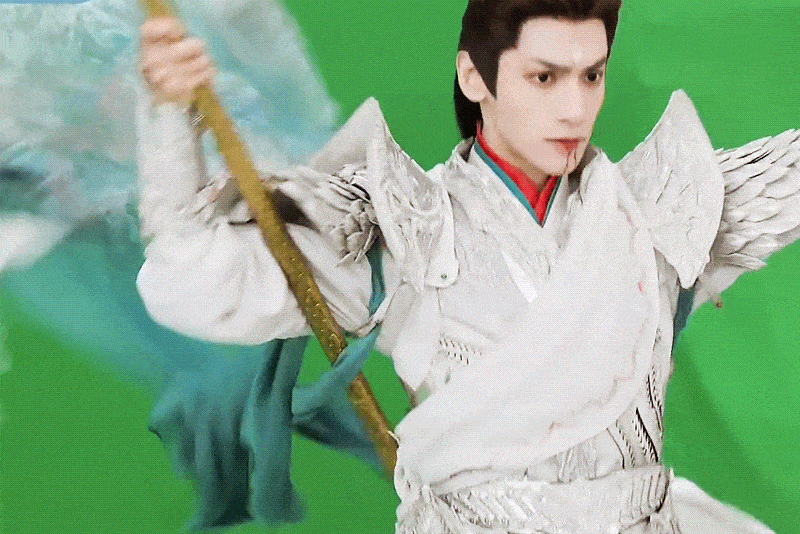2007年,一部以青春、爱和同性为主题的泰国清新电影《暹罗之恋》风靡圈内圈外,继之而起的泰国同性电影无出其右。而7年后的2014年,《我的兄弟情人》尽管依旧无法企及《暹罗》题材立意的广度和高度,却在心理学层面更合理、更细致地诠释了正处于青春转型期的少年心事。

且先从颜值来对比,就不难发现两部电影风格的差异:

当年凭《暹罗》一炮而红的Pchy以及《兄弟》中的Fluke,拍戏时都正值17岁将熟而未熟的青涩,但二者的气质在同样的忧郁中呈现了不同的魅力。Mew的忧郁中含着一种艺术的优雅、孤高的冷峻以及美学的灵气,而Bank的忧郁则有着更多的依赖性、黏合性和家庭的气质,换句话说,Mew是行走在艺术殿堂里孤独王子,而Bank则更拥有女性的气质,情感也更多依赖性。与Mew更多形而上的唯美色彩相比,Bank的居家更为接地气。
同为1的Tong和Golf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Tong更为温柔,Golf更霸道;Tong在面临选择时更为犹豫(直到结尾才真正选择自己心之所向),Golf则单刀直入;Tong和Mew之间没有第三者的介入,而Golf和Bank之间则横叉一个Tom,故事里唯一的女性也奇丑无比,不像《暹罗》中的女配都是高颜值。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两部电影风格的差异,我们可以说,《暹罗之恋》像铺展在星空下的唯美卷轴,一头行走着一个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另一头行走着一个不断寻找缺失的爱的感情完美主义者;《我的兄弟情人》像铺展在田间地头的绿茵,其上奔跑着两个更为直露、外方,也更为坦然的家庭寻觅者,使人生的缺憾在相互的情感补充里得到圆满。

若论唯美,《兄弟》显然不及《暹罗》,伤于其过于直露,情感线索过于迅速和单一,相对于《暹罗》所揭示的更多元的爱,包括父母姐弟的亲情、男女恋人的爱情、朋友之间离合的友情、同事之间合作的责任等等,《兄弟》对爱的描摹显然过于狭隘,也因此,Bank和Golf的同性之爱中也少了很多其他因素的干扰,使观众更容易陶醉在他们单纯的家庭之爱中,而不必思索过多感情的责任和负累。

实际上,就演技来讲,Fluke比当年的Pchy相去甚远,在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忧郁气质的彰显上,Pchy的大方洒脱更能表现一种天生的王子气,而Fluke则明显缺乏情感上的独立气质,在许多细微处的表现力度尚有欠缺。这也是为何在面对分别时,Mew能够表面上孤高冷傲而内心滴血到死也不露声色,Fluke则一味地将伤感流于形色,使离别的悲剧性大打折扣。
所以从悲剧性的角度来看,《暹罗》比《兄弟》更胜一筹,尽管结局没有人死去,没有人离开,但蕴藏在内心深处的崇高的贵族气质无疑要比《兄弟》的伤离死别更有吸引力。

《兄弟》仅有不多的足以称道的地方,是其对同性恋情发生的心理学原因有了相对合理的揭示。家庭之爱的缺失在两部戏中均有涉及,但《暹罗》中更为复杂,Mew缺乏的是整个家庭的关爱,所以在他身上的恋父、恋母情结并存,并在祖母去世之后得到器质性的固化,Tong则因姐姐的走失相继失去了姐弟之爱、父爱和母爱,几乎也是在感情阴影中度过了童年。二者的恋父恋母情结难以区分,所以其心理学层面的原因自然也难以揭示,很容易让人将其统归于孤独、寂寞之类。

而《兄弟》中,Golf因母亲早丧,是个明显缺乏母爱之人,而因父亲对其的冷落,则刚好将两种情感投射在既是男性、又兼有女性气质的Bank身上。同样,Bank是一个十分依赖母亲的人,女性性别的同化使得其恋父情结加深并最终投射在性格外向、外表强硬的Golf身上。二人在情感上的自然结合既是对家庭关系缺失一环的自然而然的弥补,也是二位少年反抗家庭的叛逆心理的体现。

在同性恋亚文化中,特别是在男同中,父爱的缺失是极为重要的因素,父亲角色的弱化导致男孩儿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类似Golf的极端叛逆,一种是类似Bank对母亲角色的过度同化,这种双向缺失往往只能在拥有同样情感缺失的同性中才能找到,而不是完全不同的异性。因此,《兄弟》对这一因素的展现较为明朗,并最终以Golf将肾脏移植给濒危的Bank使其重获新生为结局,将故事圆满地划上了句号,使观众得以释然。而《暹罗》直到最后也要给观众留一个悬念,一方面展示爱的主题的无限性,使人回味无穷,另一方面却也有失于过于朦胧,没有像《兄弟》一样升华出更高维度的身体和精神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