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是王旷的第二个儿子。永和十一年三月王羲之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无锡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他和许询、支遁等人,开始遍游剡地山水,直到他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

那么,王羲之因何壮年辞官?
几年前,笔者认为:是因为他的性格太过直率、高傲,身上的书卷气太重,很难适应官场的原因。可以说,这些想法均出自清朝的《越中杂识》,这部作品中有一句结论先入为主,直到最近,又读了一些历史资料,才对此事有了更深刻的见解。
说起与王羲之打交道的官场中人,就不得不提起王述了。以前笔者觉得让王羲之“耻居其下”的王述,肯定是个较圆滑的人,而让王述成为王羲之的上司,绝对是一种本末倒置,这才使王羲之心有不甘,最终,选择了告病还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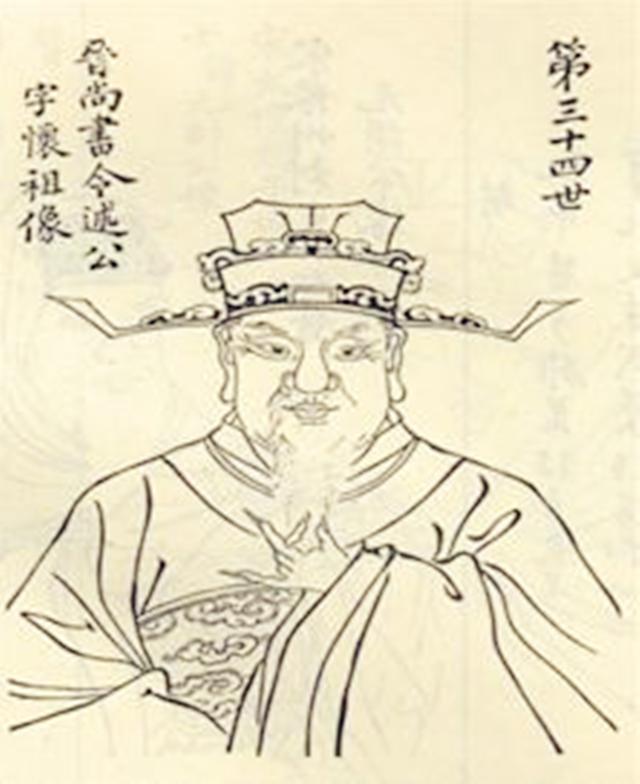
但是,事实却是,王述在当时有着与王羲之一样出名的贤才,其声名丝毫不逊于王羲之。王述母亲去世后,王述在故乡守孝多年,暂代王述作为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仅在王述的母亲发丧时前去拜访了一次,算是走走过场,其后再未造访过王述。
然而,王述却时常邀请王羲之做客,每次都洒扫庭院相候,只是王羲之每次都不赴约罢了,这才让王述对王羲之心怀芥蒂。后来,王述守孝期满,朝廷将其升迁为扬州刺史。会稽正是扬州的辖区,这时,王羲之又做了什么事呢?
他上奏朝廷请求将会稽划分给越州,就是害怕王述会对自己不利,这种“行人失辞”的行为难免会被官场同僚笑话。后来,王述履行公职,前往会稽视察,王羲之又避而不见,只叫下属应对。谁知,属下办事不力,很多接待工作都搞砸了。
王羲之面子上实在过意不去,这才“深感耻之,称病而去”。

所以,我们从这些细节来看,王羲之之所以辞官,并不是因为此人不懂得圆滑,而是根本就不通人情世故,对同僚太过于淡漠。之所以笔者会对王羲之辞官这事有了改观,其实,还是因为两种“认识偏差”的存在。

在这里,识人论事切莫不可像笔者这样,有这样两种“认识偏差”:
其一、容易先入为主,根据《晋书》所载,王述并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圆滑小人。早年王述的上司王导官运亨通,他的属下均对其大拍马屁,只要王导发表言论,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只有王述却面色如常地向王导提出建议,并说:“人非圣贤,怎会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呢?”
为此,王导还夸奖了王述一番。
而且,王述是个颇有能力的官员,关于他的办事能力,《晋书》中仅有短短一句:“莅政清肃,终日无事”。为何说“终日无事”的王述能力出众呢?注意,之所以王述每天无所事事,完全是因为他所在的环境就是莅政清肃,并不能说明他游手好闲。只能说工作相对轻松罢了。
然而,就是因为王羲之做官勤勉的印象在先,所以,难免会错误地认为王述游手好闲。有王羲之“耻居其下”在先,更让人不由得想王述的性格缺陷。

其二、就是不可望文生义,前几年在《越中杂识》中看到的那段记载为:“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上疏争之,多见从纳。尝遗书殷浩,止其北伐;上书谢安,谏其清淡。众皆韪之。后王述为扬州刺吏,羲之耻居其下,谢病归。”
看过《晋书》的朋友都知道,其实,这段完全照搬了王羲之的本传,只是稍有缩减罢了。正因为篇幅被修改,所以,很多关键的细节被省略了,以至于,这段记载的每句话都显得突兀,最终,使读者望文生义,将王羲之的辞官归咎于王述,或王羲之不懂得圆滑的性格。
其实,客观来讲,笔者并没有贬低王羲之的意思,他为民请命敢于直言的性子,的确是廉洁奉公的典型,但是,不通人情世故不懂交流也是他最大的弱点。不圆滑与褊狭有时就是一码事,因不圆滑而不懂变通,因不懂变通而不宽容,因不宽容而褊狭,二者之间有逐级递进的关系。

王羲之与王述虽同朝为官,但是,两人却势同水火。王述之所以会恨王羲之,完全是因为此人不通人情世故,自己好意抛出橄榄枝,却被王羲之当作野草对待。而王羲之之所以“耻居其下”,则是单纯地因为他的“褊狭”罢了。
其实,这两人只要各让一步,例如:王述守孝期间,王羲之抽时间登门拜访,两人促膝长谈一番;或王述走马上任扬州,路过会稽时探望一下这个直脾气的小老弟,或许,这两人则会冰释前嫌。然而,历史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终其二人一生,始终心怀芥蒂,无法释怀。
参考资料:
【《晋书》、《世说新语·赏誉》、《越中杂识》】
,




